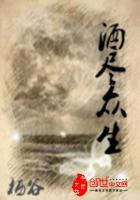“噗嗤”一声,火柴点燃烟斗,顽老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烟圈。
桌上的蜡烛已经烧尽了,蜡水顺着烛台流淌下来,凝固成泪珠。
房间昏暗,竹河颤巍着抬起手臂,声音扑朔:“天……亮了?”
钟岚心捧起竹河的手,轻声回答:“亮了。”
“开窗……”竹河的眼睛追着雕花的窗格、米白的窗纸。
“竹河,风凉。”岚心一眨眼睛,两行泪水滚滚而下。
竹河气若游丝,用全身的力气抽出手,抚摸着妻子的脸颊,努力笑出来:“我想看看天……。”
钟岚心看向顽老,顽老闷头抽烟,没有阻拦。于是,琅歌走到床边,推开窗扇。
明亮的日光顷刻洒进来,竹河好容易才适应了光线,勉强睁开眼睛。
“什么时辰了?”竹河问。
钟岚心颤抖着声音回答:“午时了。”
竹河一点点扭头,看向旁边。草籽紧握着竹笛,歪坐在床榻边,睡着了,浓密的眼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
“他知道了?”
钟岚心默默点头。
竹河没有再说话,只是发出了很长的叹息。
草籽肩膀一动,醒了过来,他“嗖”地转过身,往床榻上看,可是竹河已经再度睡去。草籽有些失望,钟岚心揽过他的肩膀,说:“刚刚你父亲醒了一会儿,还问了你。”
草籽掖掖被角,道:“他累了。”
“是啊。”
“他会好起来吗?”草籽转头,仰起脸看着钟岚心。
这一次,钟岚心没能回答。
于是,草籽再次低下头,不再追问。
小小的手,一次又一次地平整着被角。
看着草籽无助的背影,在明晃晃的日光下,愈发单薄,像一株金秋寒风里的芦苇,摇晃着,不安着。
罗骁与钟长野交换眼神,扭过脸去各自叹息。
顽老手边的桌面上,堆积着从柳畔送回来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只是为绝望添了一笔浓墨而已。
顽老已经不知道自己抽到第几管烟了,开着窗,屋里还是弥漫着刺鼻的烟味。
一夜之间,他仿佛衰老了很多,不得不说,钟老庄主和竹河对他的自信与权威,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玄渊和熹月回来了,死寂的屋子,空气令人窒息。
顽老见人到齐了,敲敲烟杆,艰难地开口,说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个人的命啊,总量总归就那么多,要么求长,要么求宽,柳自如给他的药,激发了他残余的体力,换言之,是预支了他的生命。如果他一直保持着之前的状态,或许还能活上十年二十年,而今……大限已到。”
没有人质问。现在他们唯一还能做到的,就是静静守在竹河身旁,陪他走过生命最后一程。
但是,多么心有不甘。
就这么,窗外的太阳西沉,一轮圆月升起。
屋里的人,或坐或靠,却没人离开。
“今夜之月,亮于昨夜。”有人感叹道。
“是,”是草籽的回答,“爹爹。”
这下,众人骤然惊醒,竹河醒了。
竹河看到满屋子的人,忽然笑了:“这是何必呢?”他干枯的手指抚摸在草籽的脸上,目光落在窗外:“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果然……呢。”
明月圆满,但是,过满则亏。
“孩子,到底,是父亲亏欠于你。”竹河笑着,眼角滑落一滴浑浊的泪。
草籽的手指接住了那滴泪:“我……”
竹河没能听到草籽含糊的回答,他害怕听到那个他不愿听到的答案。
“琅歌。”竹河轻唤。
琅歌凑过来,他的听力极佳,但他还是极力靠近竹河,生怕错过一个字。
竹河注视着草籽,眼睛里是说不出的郑重:“孩子,你记住,我是元家人,你也是元家人。琅歌,他不仅是你的长兄,更是这个家族的族长。”竹河又看向琅歌,“草籽的名字,由你来定。”
“小叔叔?”琅歌大惊。
“你是族长,在元家你的话,最有分量。由你来命名,是吾孩儿之大幸!”竹河越说越激动,半个身子都仰了起来。
琅歌稍一思索,再次环视满屋子的人,视线落定在草籽身上,一字一顿道:“元珝歌。王羽之珝。”
竹河的身子骤然一松,落在床榻上,神情复杂地笑起来:“哈,哈,羽者之王,琅歌啊,你对我的孩儿,给予了如此之大的希望吗?”
“他值得。”琅歌道,“而且,我要你亲眼看到他那一天。”
“你替我,看,好吗?”竹河的询问没有得到琅歌的答案。
而一直跪在床榻之侧的草籽,如今是元珝歌的孩子,他严肃地朝着琅歌一拜,说:“元珝歌,谢族长赐名。”
明朗的声音,崭新的声音,清澈的声音。简单的几个音,在场之人,无不动容。钟岚心伏在竹河身上,泣不成声。
琅歌压制住内心的哀恸,扬手一甩衣袖,从身后抽出他的长箫,横在面前,对竹河道:“元氏琅歌,在此起誓,我必定护佑元珝歌长大成人,为世间清风。”
元家传世之宝在前,琅歌的誓言有多重,不必言说。
竹河因为激动而大口地呼吸着,好容易平稳了情绪,咳着说:“多……谢你……”
在此后的三天,竹河一直陷入昏迷之中,偶尔的苏醒,也无太多意识。
乘风人只是偶尔的小憩,钟岚心和琅歌,一直寸步不离。
逼近的时间点,折磨着所有的人。
夜半,突袭暴风雨。雷暴霹雳,伴着刺耳的爆裂声,一道紫色的闪电直劈而下,犹如暴怒的神龙。狂风肆虐,雨珠比豆大,不问冷暖,只重重砸向人间。
突然,竹河睁开双眼,直直瞪向窗外。
钟岚心条件反射地将珝歌搂在怀里,心中是怎样的震惊:“不,不会。”
竹河颤巍巍地站起来,微驼着背,手臂不自然地垂着,嘴角向后扯动。他曾说的疯狂,难道会在这个时间,来找他吗?
玄渊跃步上前,张开双臂,将所有人挡在身后。
忽然,竹河神色异样,不等满屋子人有所反应,他纵身一跃,破窗而出,消失在了暴雨之中。
瞬间,玄渊也飞身而出,追了出去。
看到竹河的方向,钟长野叫一声不好:“那里是明玕的迷宫!玄兄当心!”
说罢,钟长野一个呼啸,叫来明玕大弟子,追着玄渊的脚步跑去。
“碧虚郎,什么迷宫?”罗骁吼着。
暴风雨里,声音很难传递,钟长野也吼着回应:“我明玕四周尽是迷宫,有暗道有机关,只有大弟子以上的人才知晓出路,这样的天气,连我都不敢贸然闯入!”
“管不得那么多了!”琅歌道。
追了一会儿,玄渊的痕迹不见了,前方出现了好几个方向,钟长野朝大弟子下令道:“这里启动机关了,我们要快!”
“对面是哪里?”熹月问道。
钟长野一怔,张了张嘴:“这一带,都是沼泽。”
“什么?”
钟岚心说:“难道,他还有残存的意识,他不愿伤害我们……”听到这句话,珝歌猛地抬头。
“事不宜迟,我们先找到他!”熹月道。
“少庄主,找到了,从这里走!”钟佳抹一把脸上的雨水,指着一条路。
钟长野扬手:“带路!”
暴雨使地面愈发泥泞,湿滑得厉害,雨帘如瀑,阻隔了视线与声音。在视觉、听觉和行动力都被封闭的情况下找人,谈何容易。
“竹河!玄渊!”众人呼喊着,暴风雨吞没了声音,闪电乍明,雷声滚滚,人类的声音如此微弱。
琅歌捕捉到耳边的异动,钟长野和罗骁迅速挡在最前面。窸窣声越来越近,突然,一只白色的猛兽扑上来。
“是竹河!”琅歌的叫声,打断了罗骁的进攻,罗骁急转身,让他从自己的侧方冲过去。
竹河回头,恰巧一道闪电从他的上方劈过,白光之下,竹河披头散发,头发凝结在脸上、脖颈上,他的衣袍撕破了,挂在身上。半个身子的疤痕,使他真真正正地像个怪物。
“不要刺激他!”后方传来了玄渊的声音。
熹月回头:“玄渊,你没事吧。”
玄渊没有回答他,只盯住竹河:“他还有意识,他只是失去了控制力。”
罗骁问:“顽老,用昊离村那个方法行吗?”
“暗器?”熹月也看向顽老,“可以吗?”
顽老摇摇头:“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在自主行动,不受七经八脉干扰,恐怕不妥。”
“那要怎么办?”罗骁吼。
玄渊问钟岚心:“以前是怎么解决的?”
“以前都是柳先生,柳先生将他带到没有人的地方,任他自行缓解……”
玄渊对明玕弟子道:“围阵,他的行动没有思想控制,将他困在阵法中,先看他能否自愈。”
钟长野随即吼道:“钟佳!列阵!”
“是!”
数名大弟子齐齐列阵,将竹河围困在内。
“需要多久?”玄渊又问。
钟岚心摇头:“没有规律。”
明玕剑阵很难突破,那是因为逃脱需要以命相搏,但是,在竹河硬闯的关头,大弟子们却不敢轻举妄动,于是行动十分受阻,竹河疯狂攻击之下,大弟子渐渐承受不住,血水混在泥水中,散开血腥的味道。钟长野见状,亲自出手,他的加入,为剑阵上了一道重锁。但是,竹河仿佛被着血腥味刺激到了,他俯下身,嘴角发出嘶吼声。
突然,钟悟和钟冰之间,露出了破绽。竹河从此突破而出。
原来,大名鼎鼎的明玕剑阵,也有守不住的时候。
竹河的武艺早已全废,若十二名大弟子拼力而为,不是做不到,只是因为,阵内的人,不是敌人。这才是固若金汤的明玕剑阵之软肋。
钟长野眉头一拧,调转方向去追,却在他之前,钟岚心冲到了竹河面前,张开双臂,挡在他的面前,迅速有两个弟子站到了钟岚心的两侧。
竹河明显地停顿了下来,不安地左右错步,试图绕开钟岚心,而一左一右,玄渊和罗骁已经就位。
钟岚心看着竹河毫无感情的双目,雨水冲刷不去刺鼻的味道,白衣而来的大弟子血染衣衫、伤痕累累,乘风人小心翼翼、刀不出鞘。
不应该是这样子。
这是钟岚心的第一个念头。
“杀了他!”
钟岚心突然喊出了这三个字。
竹河微微侧头,仿佛听到了钟岚心的声音一般。
玄渊注意到,钟岚心十分沉着,异常冷静。她是认真的。
但是,仍旧没人移动。
“长姐!”钟长野吼了一声。
就在竹河脸色微变的瞬间,钟岚心夺下一弟子的剑。
“不要——”琅歌爆发了,他的声音震慑了天空的雷暴,就要冲上去,罗骁一把抱住了他。
锋利的剑锋,直直刺进竹河的心口。
雨水凝固在了半空,时间停止。
竹河晃了晃,缓缓扑倒,钟岚心顺势托住他的身子,跪倒下来。
竹河的眼睛闪过一丝笑意,转而,黯淡下去。
在道观里,暴雨之中,柳自如仰着脸,注视着枝头的血红色树叶脱离枝干,在风雨中飘落,他微微张口,吸了一口气,忽然向后仰起头,哈哈大笑,又笑到俯身,头发黏在脸颊上,再次抬起头的时候,脸上的雨水,完美地掩盖了泪水。竹河琴从柳自如细长苍白的手里滑落,“嘭”地砸在地上,那么短的距离,坚固的竹河琴却碎成片,木屑与断弦迸溅开来,余音消散,尾声沉寂在浑浊的泥水之中。
琴弦剐蹭到了柳自如的手指,鲜红的液体滴滴答答地落下,落在断琴上,渗进木材的纹理中。
“世上,再也没有了。”柳自如喃喃而语。
过了很久,空荡荡的道观里,传来了很长、很失落的叹息。
沼泽边缘,钟岚心抱着渐渐失去温度的躯干,将脸颊埋在竹河冷去的肩膀上,瘦弱的后背剧烈抖动着,空中响彻着钟岚心不加丝毫压抑的撕心裂肺的恸哭声。
琅歌呆呆地挂在罗骁的臂弯,眼中原本的明媚色彩,如同被抽离出去一般,瑰丽的紫色暗自神伤。
钟长野身子一垮,瘫坐在地上。
熹月不知如何应对眼前的狼狈,她捂住颤抖的肩膀,慢慢蹲下身子,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大弟子们互相搀扶着,勉强站起来,顽老给他们处理伤口,他的手一贯的稳当,但是未免太过稳当了。
玄渊握在刀柄上的手,缓缓挪开,张开手指的时候,骨结发出清脆的响声。
忽然,珝歌走到母亲身边,保留在三步远的距离,竹河的血水流到他的脚边,他默默地看着眼前的景象,仿佛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天空忽然明亮起来,云开雨霁,日光灿然。明亮的光柱投射下来,天际呈现一道漂亮的虹桥。
两日后,一座朴素的新坟,出现在竹林河畔。
在入葬前,琅歌把自己从天宝斋找回的玉佛坠给竹河带走了。这是竹河唯一的陪葬。
玄渊轻轻问钟岚心:“你其实,不必自己动手。”
“我知道,”钟岚心已经很平静,但却十分憔悴地说,“但是,如果是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我都会恨他的。”
“竹河最不希望的,就是你恨自己。”玄渊道。
身边的女人露出一抹苦笑。
突然,不远处发生骚动,玄渊走过去,看到熹月和罗骁搀扶着半坐在地上的琅歌,琅歌垂着头,金色的发丝散乱着,挡住他的眼睛。顽老蹲在他面前,看到玄渊走过来,看着他的眼睛,严肃地说了几个字:“琅歌失声了。”
玄渊眉梢一抖,僵着身子问:“伤到了?”
顽老站起来,摇摇头:“只怕是心病。”
玄渊脸色一黑,没有再问,直接离开了。
其实,那天黎明,从迷宫回来的时候,琅歌与玄渊发生了争吵,或者说,是琅歌单方面的发脾气。
琅歌留在队伍的最后,四下无人之际,他低着头,道:“就算岚心不出手,你也会出手的吧。”
“是。”玄渊没有回避。
“你没有隐瞒,没关系,反正我也听到你了,”琅歌的声音阴沉得不像他,“为什么会这样。”
玄渊仍旧没有转身,只说:“天意难违。”
“你怎么可以放弃?你不是去找柳自如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我刚一找到小叔叔,他就死去了?我的祖父、父亲、叔叔,到底是因何而死的?玄渊!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琅歌突然爆发了,像头暴怒的小兽。
玄渊并不意外琅歌失控的情绪,但是他只能说:“抱歉。”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平阳又是为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元家做错了什么?”琅歌抓住玄渊的衣襟,眼里冒着火焰。
两个人的争执声引起了众人注意,熹月和罗骁连忙将他们分开。
“琅歌,柳自如的事情,我已经全部告诉你毫无隐瞒,你,你不要责怪他好吗?”熹月不敢看他的眼睛。
“不好!”琅歌怒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我的家族是为何失去了三条人命都不知道!不好!”
玄渊的衣领被琅歌抓扯了,但他毫不在意,只留下了两个字:“抱歉。”
“我不接受!”琅歌冲着玄渊的背影吼。
山林披霞,秋水微涟,北风瑟瑟。远方的山斑斓色彩,层层叠叠,格外美丽。果然,是最美丽也是最残酷的季节。
黄昏时分,有人出现在坟茔前。
“有竹有河,你很满意了吧。”
“只可惜,再也没有你喜欢的声音了。”
“你都不回来了,留在它,给谁听呢?”
“我也要走了。”
宽大的月色白袍,拖曳至地的长发,那个人蹲在碑前,尚未结痂的手指划过碑上那悲伤的字。
在那晚的谈话中,熹月就已经知道,耿介信中,那个百夫长记忆里的世外高人,并非阆风六士的后人元昱笑竹河,而是琴声飞扬、来去自由的柳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