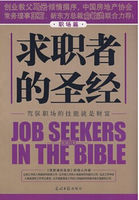从大湖回来,玄渊的精神很明显地渐渐好了起来,虽然他更多的时候还是静坐和发呆,也没什么话,但是那双浑黑不见底的眸子,已经能够映出一些画面了。
再深的水,也会在石子的激荡下,引起涟漪。即便是细微之处的震颤,也可以成为巨变的开始。
熹月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便是一步一个脚印,学东西向来扎扎实实,经过晓行云的指点,她的箭法得到了很大进步,晓行云随意往空中抛起的草靶子,移动起来有快有慢、有高有低,而熹月的命中率,仍旧已经不容小看。
进入伏天以后,尽管是绿林山水,中午的时候还是酷热难耐,晚晴变着花样地做些清凉的食物,来缓和暑气。说起暑热,龙兴寺的禅房更甚,于是乘风人们时常能见到一个摇着蒲扇的胖和尚,晃晃悠悠地过来蹭饭。
又是一日上午,微风带来几分舒爽,槐树的树荫里,琅歌和罗骁坐在矮凳上,叽叽咕咕地研究着什么,而玄渊则靠在树旁的石头上,默默看着。
来人踮着脚,小心翼翼探头探脑,玄渊刚要坐起身,那人便做了个禁声的手势,于是玄渊欲言又止,复又靠回去。
“古尊大师,你来看看我做的怎么样!”琅歌头也不回,好像早就察觉到来人了似的,声音清朗而愉悦。
古尊浑身一松,瞬间明白了玄渊想说什么,有点失落地说:“唉,你这对小耳朵也忒好使了吧,得,我瞅瞅,你俩这是做啥呢?”
琅歌放下手里的小刻刀,捧着一朵绚丽张扬的月季,放在古尊宽厚的大手里。
月季花儿朵儿娇嗔嗔,轻盈润凉,花瓣精薄,光滑而富有弹性,颜色呈现为柔和的月白色,晶莹剔透,恰到好处地绽放,既不羞涩,也不必担心花落之憾。
古尊顺势蹲下来,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嗅了嗅,“哎呦”了一声:“呵,还是芦菔[芦菔:汉代人称白萝卜为“芦菔”“罗服”等。《后汉书·刘盆子传》中有宫女“掘庭中芦菔根”吃的情形。]味儿的。”
琅歌喜滋滋地笑,顺手把小刻刀擦干净,边说:“罗大哥问起我家传的手艺,眼下也找不到材料,我看晚晴在做午饭,就问她借了根芦菔来。”
“这可以呀,虽不及你爷爷的手艺精确,但这样子,啧啧,比你爷爷有想法。”古尊说完,看见罗骁藏着掖着的,道,“行啦,我都看见啦。”
罗骁傻笑着,把自己的芦菔露出来,古尊瞥了一眼,犀利地评价:“哟,帮晚晴切片儿呢?”
罗骁是靠着一双手生活的,刚起家时无不躬亲,做起活儿来,自然是好手,可就算是好手,要他盖栋房子出来都没问题,偏就搞不定一朵小花儿。
这时候,晚晴举着勺子走出来,问这两个人:“你们不是说帮我切菜吗?菜呢?”
琅歌指指古尊的手心,晚晴也眼睛一亮,好生赞赏了一番,又看向案板上七零八落的芦菔片,不由好气又好笑。
玄渊顺手捏起一片儿来,送到鼻子下,轻轻嗅着那股清香味儿。
过了午后,听晚晴煮了酸梅汤,古尊更是不走了,从厨房顺出了两根芦菔,叫琅歌再雕刻点儿别的花样儿。
“哎呀,大师,你这是跟顽老学的吧?”罗骁打趣儿道,话还没说完,就被古尊和顽老一人拍了一巴掌。
琅歌埋着头,小刀微微颤抖着,不大会儿,就雕出了一只透亮的蝉,栩栩如生。
熹月和晓行云错过了上午的月季花儿,虽早就知晓元家手艺超凡脱俗,却还是捧着芦菔蝉惊讶不已。
玄渊再次看了看一脸玩心的古尊,叹了口气,摆弄着手里的斜尖刻刀,说:“大师,关于智前辈的事情,您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古尊伸出来的胖手一顿,缩回袖子里,呼呼哒哒地扇着蒲扇,歪过头去不说话。
这言一出,连晓行云都一愣,更不用说其余乘风人了。
“玄渊,你这是何出此言呐,智前辈早就失踪了,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晓行云道。
琅歌忽闪着充满疑问的大眼睛,看向罗骁,罗骁耸耸肩,表示不清楚。
玄渊的话从不会无缘无故,熹月更是通过古尊的表情猜出一二,清澈的眼睛看得古尊很不自在,熹月想了想,说:“大师,您将此事隐瞒,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她看了看玄渊,又道:“大师不愿讲,晚辈也不敢强求。只是,把事情调查清楚,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吗?”
其实,关于这些个陈年往事,古尊原本是打算烂在肚子里的。古尊之所以日日来这小院,除了蹭吃蹭喝之外,也确实是担心玄渊,还有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一层,就是他确实想把关于智的事情告诉玄渊,可是,每次都是话到嘴边上了,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熟料,不知先前在哪里露出马脚,竟叫玄渊猜出个七七八八。看样子,玄渊是在等自己主动说,又估摸着自己来了多少回,都没有说出的意思,八成是有心隐瞒,才不得不主动挑明的。玄渊虽然少言,但总是能说到点子上,这回若是混过去也不是办不到,更何况,谎圆不成了,还可以犟嘴不说,估计玄渊也不会逼问。左不过,古尊琢磨着,玄渊这孩子也不容易,若是因为自己的面子,让这娃娃再多走不知道多少冤枉路,只怕佛祖也不会原谅,更对不起平阳和南岸。罢了,罢了,不就那点破事嘛,他们知道就知道吧,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还是红尘之外的和尚,怕啥。
不过,也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是说不出来呢?
每次返回龙兴寺的途中,古尊都会拍着自己光滑的脑袋,使劲琢磨。
即便是说,也是打算找机会,把这点儿事单独告诉玄渊的,谁能想,千算万算,古尊怎么也没想到,要洗耳恭听自己那些事儿的,竟然老老小小坐了一院子,好像自己是个说书的。饶他是古尊,也有些不好张口了。
持有“智”之名的,是古尊的师姐,名叫蒹葭。
算起来,最先入门时年三十多岁的元老前辈,十年之后年轻儒生唐文拜师,又过了近十载,先后收留了十四五岁的蒹葭和古尊,镖师晓之凤是后两年才来的,故而他虽比古尊年长,按辈分却在之后。
虽说蒹葭是师姐,却只比古尊早入门半个月,何况论起年纪,还是古尊年长半岁。当时,元老前辈回家继任族长,唐文已前往青州办学,平阳虽与他们年龄相仿,却恰好不在周关,去了一处独峰修习,与他们熟识是后来的事。总而言之,在周关最初的大半年,山上的年轻人,只有这两位了。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论是外貌还是心理,女孩子往往会比男孩子显得成熟些。
蒹葭原是船家的女儿,和适真居士还有远亲的关系,而古尊是流浪的小乞丐,瘦弱矮小,是蒹葭在集市上看到他为了一口饭,甘心被一群乞丐打,一时气不过,替他赶走了大乞丐,又不忍他再继续流浪,从而捡回来的。蒹葭自持师姐的身份,对年轻又单纯的古尊很照顾。每天练功辛苦,古尊粗枝大叶也不觉得难受,只是明显地涨了饭量,看着他整日脏兮兮的,却渐渐结实起来,蒹葭很高兴。而古尊呢,看到这个小师姐,也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欢喜和亲近。
不知不觉间,古尊发现,蒹葭不是那么爱笑了。
在武艺上,古尊起步晚却进步飞快,实打实的拳脚,虎虎生风,遒劲有力,成长起来的不止是饭量,个子也一齐猛长,从背影看竟然那么雄武,有那么几分顶天立地的意味了。
蒹葭明白自己身体素质不是习武之才,在武艺上不会有太大造诣,可她偏是性子好强,不肯服输,过于辛苦反而生了场急病。
这场病急坏了古尊,功也不练了,书也不读了,他就整日趴在蒹葭的廊外听动静。
蒹葭自然知道古尊的小动作,又急又气又伤心。
一日早晨,古尊笑嘻嘻地给她送来早膳,看着他这幅天真的样子,蒹葭径直把早膳丢出去了。
“师姐,馒头你不要吃,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古尊好脾气地说。
蒹葭一跺脚,泪珠子掉下来,赌气地说:“我要吃独崖峰上的果子,你能采得来么。”
独崖峰距离周关不算远,屹立在大河中央,一柱擎天,不要说路了,连攀爬都无有地方。独崖峰上缠绕着一种独特藤蔓,结的果子十分稀罕,又埋藏在叶子里,不一点点拨开是找不到的。
蒹葭的目的就是难为古尊,果然,等她抬起头时,古尊已经不在了,院子里的饭食也被打扫过了。
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子夜时分,蒹葭听到有人在叩门,点了烛火出来一看,原来是古尊。
就算是不拘小节、邋邋遢遢,古尊也从未这般狼狈过,这让蒹葭一下子想到了当年的小乞丐,内心深处忽然一软。
“师姐,你要的果子!”古尊捧着两个青涩的小果子,笑得灿烂,露出一对小虎牙。
蒹葭眼眶瞬间就红了。
“傻子!你就是个傻子!”
独崖峰四壁陡峭,古尊就靠着手臂的力量攀上去的,不知滑下过几次,身上那么多擦伤,而且,这般辛苦,居然还采了未成熟的果子。
深夜里,两个人就坐在廊下吃果子。
“师姐,你真觉得这果子好吃吗?”古尊被酸得龇牙咧嘴。
蒹葭仔细地咬着,慢慢地点头。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古尊瞪着亮晶晶的眼睛,瞅瞅蒹葭,再瞅瞅果子,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蒹葭喜欢吃怎么酸的东西。
而适真居士,就在不远处,静静看着他们。
第二天,蒹葭举着笤帚把古尊赶到练功的院子里去了,自己则去了适真居士的书库。
蒹葭是个聪明人,天文地里、经商算法……凡是需要用脑的地方,蒹葭无所不精。闲来无事的时候,她就和古尊讲述那些奇异的地方。
当平阳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两个人,一下子就笑了。
适真居士也笑了。后来,等他们到了合适的年岁,替他们主了婚。
那天晚上,周关难得的喜庆繁华,乘风人来了许多,祝福这对璧人。
古尊潇洒挺拔,器宇轩昂;蒹葭红妆披霞,英姿飒爽。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古尊说过的,最有文采的句子。
八个字,字字,千金。
刻骨铭心。
婚后的古尊和蒹葭,移居到了洞庭郡,创造了大江最大的船帮。夫妻二人,一武一文,琴瑟和谐,和鸣铿锵。
直到一天,冬雪漫漫的黄昏。
“师姐,在读什么?”古尊走进屋来,关上门,掸去肩上的残雪。
蒹葭抬起头,回答:“蓬莱。”
“什么?”
蒹葭把书的封面推给古尊看,是《东海诸岛志》。
古尊迅速扫了一眼,转身挂上披风,道:“那蓬莱不是传说里的地方吗?”
“可是我在古书上真的有提到这个地方,或许它真的存在呢。”蒹葭托着腮,充满相望地说。
看着蒹葭这幅样子,古尊忍不住从身后揽住蒹葭,仍旧是好脾气的话:“既然你喜欢,我带你去。”
“骗我。”蒹葭噘着嘴。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古尊扳过蒹葭的肩膀,蹲下来仰视着妻子,笑着说,“独崖峰我都去了不是吗?”
蒹葭羞涩一笑,锤着古尊胸口,道:“不许提独崖峰!”
自独崖峰之行后,古尊才发现自己力量惊人,倒时常跑哪里去练功,自然也发现了那果子的真味。
蓬莱,是一个承诺,一个未来得及兑现的承诺。
对他们来说,也是天崩地裂的距离。
事发的那天,古尊带领船队西行,而蒹葭还留在洞庭郡。混乱之中,两人失去了联系。
古尊在匆忙间,躲到深山的一座破旧寺庙中,僧人善良,尽管知道他的身份,却还是收留了他。
不出几日,追兵到了。
方丈年迈,白眉长须,凛然伫立在门口,坚称庙内只有僧人。
追兵要求进庙搜查。
四方围截,插翅难飞。
古尊深知自己被捕不要紧,连累了这里的僧人才是大罪,于是,他请僧人为自己剃去了头发,着一身僧袍,俨然普通武僧,站在众僧之列。
追兵没有认出古尊,匆忙离去了。
世间的偏差往往很巧,只隔了一个时辰,蒹葭就找到了这座寺庙。
看到古尊,蒹葭柳眉倒竖,双唇颤抖无法言语。她难以想象,自己的夫君为了逃命,竟然不惜放弃乘风人的身份,不惜抛却妻子,出家做了和尚。
古尊震撼,却不知如何解释。
蒹葭声音无力地问了方丈古尊的法号,转身离开了。
直到离开,蒹葭衣袂飘飘,她依旧是那个好强、潇洒的不凡女子。
故事讲到这里,说者不再唏嘘,听者震惊不已。
罗骁咋舌:“等会儿,智前辈,是一位女侠?”
琅歌合不上嘴巴:“阆风六士,每个人的故事,都那么精彩么?”
晓行云仍旧是难以相信,勉强笑着问道:“不过,你们看古尊大师现在的样子,能和他讲的这些联系起来吗?”
“能!”玄渊和熹月异口同声,说完这个字,他们两个也相互对视了一下,显然没有料到对方也会这么肯定。不过,在这两个心思细敏的人眼里,古尊的隐瞒,破绽实在太多了。
古尊看了这群人的反应,倒觉得不出所料,该有的反应都有了,反倒放松下来,摇着蒲扇道:“后来,我去找过她,她已经不在洞庭郡了,我用了很多时间,才知道,她就在渔阳郡,洞庭上游不远,听闻,她重组了船帮。所以我说,你们沿大江[大江:长江。]逆流而上,是不会错过她的。”
“您有这样的苦衷,为什么不去找她,为什么不告诉她呢?”熹月痛心地问。
要怎样说呢,为了保住一寺性命是真,难道剃发出家就是假了吗?
危难之际,古尊确实没有考虑到蒹葭,所以这种话,即便蒹葭相信,他是古尊,他说不出口。
恐怕这才是蒹葭伤心的真正理由。
离开蒹葭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古尊成了名副其实的酒肉和尚,寻花问柳,在自我放纵中麻痹自己。
少年练功的时候,古尊用过很多木质傀儡,也就是人偶,在最失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行尸走肉。人鬼为傀,他自觉和那些无笑无泪的冰冷傀儡没什么差别了。
后来,晓之凤找到了他,把这个几乎认不出来原貌的胖和尚接到了龙兴寺。
“依着她的脾气,我估计她应该查到了不少东西。现在,渔阳郡有个鬼市,你们去那里能找到她。”古尊淡淡留下这句话,甩着袖子离开了。
胖胖的身子,影子却那么单薄,被残阳拉扯得那么长。
“大师,您不觉得,智前辈住在离洞庭那么近的地方,是在等您回去找她吗?”熹月冲着夕照里模糊不清的身影喊道。
玄渊按住急欲追去的熹月,微微摇了摇头。
他夫妻二人的结局,就由时间,和他自己,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