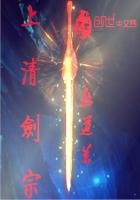正当宁小川横空出世、一刀斩杀了一名同境界修行者之时,在大离中州离都城内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同样激烈却没有硝烟的“战斗”。
离都城外廓浑圆,占地超八十平方公里,人口近二十万户;内城和外城皆是被隔划成八块扇形区域,相对应的城墙处同样开着八座城门,城中大小道路完全参照了八卦图中的精妙规划并建造,据说可容百万人马同时通行而不会拥堵,可鉴当初这座雄城的设计者是何等的独具匠心。
有外城正南方向所开的离门一路向北十八里后到达内城丁午门,以这十八里路画出一根轴线,便是离宫御道,此刻御道上彩旗招展,两旁甲士林立,显得威严气派而又不乏隆重。进了丁午门后,便是最靠近离宫南门的承乾殿。离宫离宫,共分有三宫六殿,分别为正中上清正殿、正北未央殿、正南承乾殿、正西上福宫、正东永安殿、西北文华殿、西南关雎宫、东北汶水殿和东南麟趾宫,合意九尊至顶。此刻除上清正殿以外的另八个宫殿皆是人头浮动,不停有甲士和身穿官服、手捧托盘的人进进出出,最后再交由两列身着绛红色甲胄的禁军统一送去离宫中央的上清正殿。
殿内即将举办一场晚宴。
夕YX光正沿着这座恢弘大殿的黄顶红墙及两翼琉璃瓦顶渐渐下落、渐渐转淡,直到映上了殿中央大门上那块刻着‘上清正明’字样的巨型白玉牌匾后方才如龙抬头,照出丁午门,照上了那根十八里轴线。
大殿北有一露台,中央设国主龙椅,殿前摆有龟蛇、龙、凤、麒麟四象铜塑,下设三列共十八级台阶,两侧按级分别摆放了十八尊铜鼎。最下方的台阶口左右两侧陈列着两排共八张长桌,其后的庙堂中央才是整整齐齐又一排排不下百张长桌。座无虚席。临近露台的八张长桌上却只有五人落座。
左首一个中年黑胖子,大手大耳圆脸小眼,一身大紫色朝服已被洗至发白,似是名廉臣。一旁隔开一张空桌,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高瘦男子低头不语,自顾把玩着一块挂于腰间的玉佩。碧眼男子身旁是一耄耋老者,佝偻着身子,即使是身上那套华贵朝服也丝毫衬不出其半分雍容官气,倒是不经意透出了几分知天命后的随意豁达。右侧一排头两桌也是空缺,第三桌上的那位,是一身着黄金甲胄、貂领披风,身材修长才半甲子的武将,这位壮年将军此刻一副正襟危坐模样,双眼却在直视着正上方的龙椅发呆。旁边桌那位五十上下,圆脸方颌魁梧壮硕,一身浩然正气,虽未披甲带胄却也着了身胸前补了块绣有唐猊飞鹤图的武将补服。朝堂站列分为左文右武,堂下百官依此一目了然。
两侧八桌之下,百官均已落座。手捧托盘的禁军甲士鱼贯入殿上酒上菜,终于给今日这异常沉闷的朝堂上带来了些微新鲜空气。
黑胖子率先打开话匣,转头对金发碧眼的高个男子说道,“碧眼儿,听说前些日子你们唐州府屡出大手笔招兵买马,更是连同墨家,撒出大量灵器晶石作饵,吸引了好几个修行门派世家和不少散修加入,看来你们志向不小啊!”
金发碧眼的男子呵呵一笑,并不急于反驳。身为西域人的他幼年经历过战乱逃难、一路乞讨直至大离西南隅的唐州后才终于得以安身,他在唐州做过小贩,当过跑船,经受过无数人异样的目光和白眼,也终于熬出了头,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不到而立的岁数便成了一个大富商。至于他后来又是如何弃商从政,一步步从地方小吏做起终成就了堂堂封疆大吏、富甲天下的唐州州牧大人,却是无人知晓其中原委了。
然后他回道:“刘大人取笑了。我们唐州有钱是没错,墨拒城墨家强盛依旧也是不假,但如果刘大人硬是借暗示州府和墨家联手便是想觊觎什么的话……”
碧眼男子敛起笑容,“哥舒翰虽然不才,却总还是比某些脚踏两条船、所谓光明磊落的人士来得可靠些。别以为我不知道,申州去年一年的粮食产量达三千万石,其中有两千万分头分批拨给了镇北军、镇南军、征西军以及转进了国库,申州往年民用及军需一年耗粮约两百六十万石,照惯例入州府的库粮也就两百万石左右,那么,剩余的五百四十万石粮食去了哪里?”
胖子一张黑脸霎时转白,然而不及他辩解,碧眼男子又道,“上月我们大楚军在泰州樊篱、卢州金昌一带剿除地方叛军时均是吃了败仗,可根据情报说泰卢二州的叛军本应断粮超过两个月了,而这两个州府更是早已被东夷神圣军给彻底摧毁了,叛军不可能也没有渠道弄到足够多能保证军队战力的军粮。除非……”
碧眼男子哥舒翰斜望着身为申州牧的黑胖子不再言语,眼神玩味。
黑胖子暴怒起身,白脸又转红,大声斥责道,“碧眼儿,你少给我血口喷人!”
身旁方才还佝偻着身子似在打盹的耄耋老者突然醒来,连拉带拽地让黑胖子又坐了下来。
“哎呀,我说两位州牧大人呀,你们这是干嘛,两位都是未来朝廷仰仗的股弘,庙堂之上的百官表率,可不能这样拌嘴吵闹啊,这让百姓武夫们瞧去了,少不得又要被添油加醋修饰一番对外转述,成何体统呐!”
这番话明显意有所指,碧眼和胖子皆是偷偷打量了对座两位曾在大离军方位及人臣的上将军一眼,见对方果然面有喜色又在努力憋住不笑,于是再不争吵。
耄耋老者起身来到二人中间分别牵起碧眼和胖子一手,“二位大人齐心协力,才是我大楚国之大幸,天下百姓之大幸也。”
言罢他同时牵举起四手,堂下顿时喝起一片叫好声。
“吴老祭酒英明!”
“哥舒大人英明!”
“刘大人英明!”
“大楚国万岁!”
……
离都外城西侧靠近兑门的城墙上,有两队巡防士兵完成了交替。一个四五十多岁的老兵拖住了另一个明显年轻许多的士兵一起来到了城墙一处无人注意的拐角,蹲下身直到看见最后一名同伴也下了城楼后,老兵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瓷罐交给年轻士兵。
“和他们一起回营房也就是摸牌九说浑话,我这罐购自光明邨值二十个大钱的上等照烧可不够这么多人分呐。”
年轻士兵一听是好酒,急忙启开酒封,凑近闻了闻,咧嘴一笑,小心地咪了一口。
这年轻士兵是老兵的妹夫,也是一个刚入军伍的新兵蛋子。大离国战乱不断,目前做什么行业也比不上入伍从戎来得牢靠,何况有自家大哥这么个老兵油子罩着,当得又是最安全的巡城守军,一周三日白班三夜晚班又放假一天,月饷八两晶票足足八百个大钱呐,多好的差事!
新兵感激地望了眼老兵,把酒罐又塞回给他。
“大哥,听说离宫今日设宴群臣,到底是谁做的东,又请了哪些大官呢?”
老兵瞥了眼城墙上那些熟悉地不能再熟悉的旗杆上正迎风飘舞着的一面面陌生旗帜,叹了口气,心想自己这个巡了二十年城墙的兵痞子,如今到底是在替谁把守城池呢?
“不管是谁作东,今日晚宴过后,离宫都应该要改名了……”
“是啊,听说国号将改为大楚,国主的龙椅应该是那宣威将军王培龄来坐吧。”
“嘘!”老兵作了个噤声的手势,再环顾了一下四周,道,“别议论这种事情,小心惹祸上身。”
新兵有些不解,疑惑道,“可是在营房里大家都在说这事,没人避嫌啊。”
“愚蠢!君侯国主的名晦也是我们这些小小士兵能随便呼喊的吗?一旦这话被有心人传了出去再让上边知晓了,指不定那就是……”老兵顺势作了个单掌抹颈的动作。
新兵深吸一口气,继而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无法忍住不问。
“大哥,你说如果最后坐上这龙椅的是另有他人,那我们也不能报出那宣威将军的名字么?”
老兵有些窘迫地抓了抓脑袋,看着自己面前这位连襟,心想怎么就和他说不明白呢?
“如果国主真的另由他人来当,冲你刚才那席话,那就是诛九族的大罪了!”
“自从那个腥风血雨的早朝过后,离宫中能保住项上头颅和头颅上那顶官帽的哪位不是未来大楚朝廷的股弘大臣?有申州出粮,唐州出钱,霸秦二州出兵马,新朝廷本就已立于不败;武有原本大离国七位上将军中的四位:禁军中的宣威将军,向晚原上的那位统领帝国骑兵的大都督,还有镇北将军,征西将军作为中流砥柱。大离文官虽然在宫变中折戟了大半,但也不能尽说文人多迂腐,这不谁也想不到曾侍奉过三代国主、立誓做一辈子道门圣宗仆人的祭酒司吴老祭酒就头一个站出来说愿意侍奉新主,这才保全了更多原本就立场不坚的文臣性命,甘愿尊其为首辅、政坛执牛耳者。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在背后唾弃吴老祭酒,说他老而不忠是为贼,可是我却觉得他是能屈能伸方为真豪杰!说来说去都是围绕着那张龙椅宝座在博弈,所以说说错了国主是谁就等同于站错了队列,这是最犯忌的大罪!”
新兵一脸崇拜的表情望着老兵。
“大哥!我真是第一次发觉你原来这么有才!真是说得太对了!”
“嗨,这有什么?等你也和我一样熬成了老兵痞子,对这些上层世界的游戏,都能看通透!”
老兵嘴上说得轻巧,心里却难免被夸的有些得意,仰脖灌了一大口照烧,回味叹道:“我们虽说穿着这身卒服却仍旧脱不开普通百姓行列。其实不管这天下是姓姬还是姓王,我只求日子过得安稳些、能吃得上热乎的、家里老娘多活几年,你待我妹子好些,其他也就别无所求了。就拿这巡城守卫的工作来说吧,看似危险,但我守了足足二十年城,见过夺权兵变见过封城戒严,但说到离都被外敌侵犯需要我们用命来守城的次数有过么?一次都没有。”
话音刚落,但见西方距城墙百丈之外突然尘烟滚滚,虽然自己身在高处却仍能感受到一阵急促不安的震动正伴随尘烟席卷而来,愈来愈强烈,令人心悸不已。
新兵疑惑愁眉道,“是地震吗?还是起了尘暴?”
老兵不语,但他心中已经确定了这是什么状况,这种感受他曾在位于秦霸两州中央的向晚原牧场上体会过——正是亲见万马奔腾的壮观景象后带给内心的那种无以言复的震撼!
他手上那罐美酒轰然坠地、砸成了粉碎;却毫不在意。转过头,用尽了可能是平生最响亮的嗓音喊道:
“有、敌、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