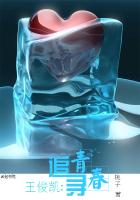亲爱的卡尔,很抱歉现在才回复你最近寄给我的公文。地缘政治已经成为我们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哥哥和我整日忙着建立战后组织。我认为把耶路撒冷还给犹太人是一个合理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无论如何它还是要影响到相关的条款。我们仍然坚持高姿态,当然这样总是有利。
苏联将采取一切措施反对统一欧洲,我确信我们最终会胜利,只是外交和战争问题。
更艰难的工作是这一目标直接涉及集体无意识宣传《秘经》中描述的原型,建犹太教是一回事——它是,或者将是像其他国家一样的国家。但我们建一个这样的世界:
牲畜被屠杀在田间,在疯狂的构思中图案自己加密,天空被幻象照亮。
看来像是苛求但我认为可以实现。我们发明了一种新技术(希望你把这个任务留给我)。
艾伦
邓菲又读了第二遍再读第三遍:牲畜被屠杀在田间——他们这么做,邓菲记起吉恩·布罗丁说的话:“我快要退伍时,我们开始谋划……代理把这些称为纵的沟纹图……”图案自己加密……还有其他的什么事,一些关于光电技术的事,“他们在默主哥耶、罗斯韦尔、特伦顿、格尔夫布里兹镇也用同样的手段。”
这么说邓菲是对的——20世纪是光的展台,一个特技伪装的大熔炉。这些首先是现实,接着被作为历史。所有这些都被几个持特殊想法的掌权者操纵着。为什么?他充满了疑惑朝亚洲方向的山脉望去。为什么这么做呢?
6月1号他们乘飞机抵达伦敦。他们用马克斯在布拉格给的证件。邓菲泰然自若,因为他外出时经常用假身份证,但克莱姆——可没做过什么违法的事——很紧张。入境的人很多,排了长队。他们足足等了十五分钟,轮到他们时克莱姆因为紧张加之焦急的等待,热得拿着身份证当扇子扇起来。
“八号,小姐。”
一个上了年纪的印度锡克教徒似的移民官伸手指指其中的一个平台。一个年轻人坐在那儿忙着盖章。克莱姆朝那个人走过去,那人态度的转变之快让邓菲感到诧异。他正笑着给克莱姆的护照盖章。邓菲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只需看着就明白,他们在几秒钟里就成了好朋友,他面露喜色,克莱姆则一直咯咯地笑着——不住地眨眼,不一会儿她就乘电梯到了海关边境的行李传送带旁边。现在轮到邓菲了。
邓菲来到一个瘦瘦的年轻移民官面前。移民官长着蓝色眼睛,黑色的连鬓胡子,嘴周围的胡子呈盾形。他很不耐烦地看了一眼邓菲尚未痊愈的鼻子,迅速翻阅邓菲的护照,寻找没有盖章的地方。
“皮特先生。”他读这个名字时仿佛在射精。
“是的。”
“你从哪儿来?”
“特内里费。”邓菲回答说。
“度假还是公干?”
“两者兼有。”
“什么职业?”
邓菲想这个移民官真是无趣。“会计师。”
移民官抬头看看邓菲,怀疑地问:“只有你自己吗?”
邓菲点头说:“我现在要见一个在伦敦的朋友。”
“明白。”移民官皱皱眉,指着邓菲的鼻子问,“打架吗?”
邓菲不安地挪动脚,说:“不是,我被人袭击了。”
移民官苦笑着问:“拉丁美洲人吗?”
邓菲点头。这似乎正是移民官所期望的结果。
移民官摇摇头,小声说:“西班牙混蛋。”随后给邓菲的护照上盖了章,交还给他时笑着说,“皮特先生,欢迎你来不列颠群岛!”
他们没费太大周折就找到了范·沃登。从录音带上的拨号音判断,希德洛夫打的是本地电话。这样一来邓菲和克莱姆就很容易找到范·沃登了。他们找到一家斯特兰德区的网吧,开始在网上找范·沃登。最后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教授就住在切尔西的夏纳步道。他跑步时曾不下一百次从这里经过。
“你和我一起去吗?”邓菲问。
“当然,”克莱姆说,“我们去之前打电话吗?”
“不用打了。”
“为什么不打?”
为什么不打?邓菲无法确定希德洛夫是否见过范·沃登,但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邓菲一打电话范·沃登肯定会知道教授已经死了,并且知道见陌生人时要小心谨慎。“我们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吧。”邓菲对她说。
他们发现范·沃登单独一人住在奎恩,一艘生锈的游艇停泊在巴特里布里奇特牧场。不确定为什么船会停在市中心,但又不能冲着远处喊“喂”,来招呼陌生人。所以邓菲就拉着克莱姆走到船的踏板上,接着走到一扇门前。他试探性地敲敲门,等着有人应门。等了会儿没人应门,他又开始敲门——这一次用力敲。
“等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气质高贵的人给他们开了门,这个人手里拿着一瓶红酒和一包香烟。“有什么事吗?”他问道,先看看邓菲然后又看看克莱姆,接着又看看邓菲。
“我找范·沃登,他在吗?”
“找他有什么事?”
“我叫杰克·邓菲,”他说,“你是……”
“我是,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哦,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范·沃登上下打量他们一番,说:“你们是不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会员?”
克莱姆咯咯地笑了。
“我们不是,”邓菲回答说,“我们和见证会没关联,我们是希德洛夫教授的朋友。”
范·沃登眨眨眼,喝了口红酒说:“这家伙已经死了。”
“是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调查他以前的一项研究。”
范·沃登点点头。他不像是冲着邓菲或者克莱姆点头,倒像是在暗自想着什么自顾自地点头。“我恐怕帮不上你们什么忙。”他说着开始关门。
“事实上,”邓菲说着,用脚顶着门下面,接着说,“我认为你能帮得上忙,希德洛夫也这么认为。”
范·沃登一脸痛苦地瞥了一眼邓菲的脚说:“我确实不愿介入此事。”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
“无论怎样都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为什么这么说?”邓菲问道。
“我只跟他通过一次话,从未谋面。”
“我知道。”
范·沃登似乎向后退了一步,问道:“你知道?你怎么知道?”
邓菲仔细想想,告诉了他实情,“我在他的电话上装了窃听器。”
范·沃登深吸了口烟,然后又把烟从鼻孔喷出来。随后喝了口酒说:“但你不是警察。”
“我不是警察,”邓菲回答说,“我们都不是。”
范·沃登点点头,很欣赏邓菲的坦率。然后皱着眉头说:“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要跟你谈话。”
邓菲开动脑筋思考,却不知该说些什么。最后,克莱姆走到门前,温和地看着他说:“如果你好心跟我们谈谈的话,我们会非常感激你。”
范·沃登清清嗓子说:“好吧。”打开门让他们进去。
他们跟着范·沃登来到一个狭长的走廊,走廊里挂着中世纪一些大大小小的教堂的黑白照片。经过厨房时有一股烤面包的味道。他们接着走到一个类似客厅的地方,里面堆满了书,然后他们又穿过客厅来到甲板上。甲板上的熟铁桌子上覆盖着一张玻璃板,周围有很多椅子。
“喝点波尔图葡萄酒好吗?”
“谢谢,我来一点。”邓菲说。
“很不错,这是我这儿最好的了。”范·沃登说着给他们各倒了一杯后指着旁边的一盘奶酪说,“上乘的斯蒂尔顿奶酪,吃一点吧。”
克莱姆倚着横杆,看着上游的巴特里布里奇特。一艘船经过时掀起波浪拍打着船体,她由衷地感叹道:“这地方太好了。”
“想买下来吗?”
邓菲笑着说:“我们不是真的在做交易吧。”
“我给你个好价钱。”
“抱歉。”
范·沃登耸耸肩说:“我不怪你,在这儿真是件麻烦事。”
“这么说……你不喜欢待在这里?”克莱姆问道。
“是啊。”
“为什么呢?”
“噢,首先,我觉得每个周末都出去喝点才有意义。”
“那么……你为什么要买下来呢?”
“因为艾伯特·霍夫曼。”范·沃登回答说。
邓菲笑起来,克莱姆迅速转了一下头皱起眉。
“这家伙发明了差速器,”范·沃登解释说。然后又问邓菲,“你知道燃料发动机吗?”
“不知道。”邓菲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待在原处。”说完范·沃登坐在一张石灰色的阿迪朗达克椅子上,招手让邓菲和克莱姆也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邓菲不确定应该向他透露多少实情,所以就直奔主题,先发问:“如希德洛夫所说,我对抹大拉修会不是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哦,首先,我们不清楚那是不是以前的事。”
范·沃登咕哝着说:“你的猜测没错,那不是以前的事。”
他的回答出人意料,邓菲困惑地皱起眉头,努力回想录音带上的谈话内容。“你和希德洛夫通话时,当他暗示说抹大拉修会至今还存在着时,你似乎感到吃惊。”
“我的确很吃惊。”
“但现在你却很平静。”
范·沃登摇头说:“在希德洛夫死之前,我一直认为这是谣传。”
“他的死使你改变了观点?”
“当然!”
“为什么?”克莱姆问道。
“因为他死的方式。”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邓菲问。
范·沃登挪挪椅子想要转换话题,“你们对抹大拉修会有多少了解?”
“了解得不多。”邓菲回答说。
“但肯定知道些什么。”
“是的。”
“那么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也显示出你的诚意。”范·沃登强调说。
“那算不上什么秘密。”
“在三四十年代,舵手是埃兹拉·庞德。”
范·沃登被惊得目瞪口呆,“那个诗人?”
邓菲点头。
“上帝啊!”范·沃登感叹说,他又接着回想着说,“就是那个庞德,他……”
邓菲点头说:“他进了精神病院?是的,就是他。但这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影响。他在精神病院理事——见他要见的人,做他要做的事。”
“真的吗?哦,这也不奇怪,”范·沃登发表意见说,“有许多郇山隐修会地下组织的大师都是诗人,也是疯子。”
范·沃登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便接着告诉他们,他在给诺斯替主义文学作品选集写序言时开始对位于拯救之山的洛奇族(这是抹大拉修会的前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稍等,我很快回来。”他说着站起来走进客厅,不一会儿拿了一本诺斯替派的书。这本书足有邓菲的前臂那么厚。“这是一些很有趣的文献,”范·沃登解释说,“是关于圣经的伪仿作品(所写的虽是圣经中的人物但不是圣典的正经)。
其中最有趣的是《抹大拉秘经》。”
邓菲听得一头雾水便问道:“你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词?”
“哪个词?”范·沃登问道。
“伪——什么?”
“伪圣经作品?”范·沃登问。
邓菲点头。
“说的是一本福音书,据推测是某个信教的人写的,”教授说,“这本书很有争议——《抹大拉秘经》——它是一千年前在爱尔兰一个修道院里找到的。”他把书翻到其中一页递给邓菲让他看。
邓菲看了几行抬起头问:“原作是玛利亚·抹大拉写的吗?”
“据说是。”范·沃登继续解释说此书的叙述中有很多分歧。“《秘经》是日记又是预言历书。作为日记,传说它记录了耶稣基督和玛利亚·抹大拉秘密进行的婚礼。”
邓菲表示怀疑。
“它没有听起来那么怪异,”范·沃登坚持说,“福音书里说基督是个犹太学者或者是教师——碰巧说了很多基督的婚姻状况。”
“我想他应该是个木匠。”邓菲说。
范·沃登摇头说:“大家都误解了。通常用于描述他的那个词应该是学者的意思。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人——一个犹太学者。这样才对。众所周知耶稣基督是个犹太人,他向众人传福音。但很少人知道米什奈伊克法律规定犹太学者必须有妻子——因为未婚男子不能当教师,所以才有耶稣基督结婚的说法——作为一个丈夫,他就会有自己的孩子——就不像听起来那样有争议。”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呢?”克莱姆问,“如果他有妻子的话,圣经上为什么没提到呢?”
范·沃登摇着头说“:如果有人宣称他没有结婚的话,就是造谣了——我们确有耳闻。否则人们也不会提到这个话题。毕竟我们是在谈论两千年前中东的事。妻子没有社会地位和公众角色。我们也从未听人提到那些使徒们的妻子,不是吗?但我们不能说他们都没有结婚——不是吗?”
之前邓菲并没有考虑他说的话,但现在却开始考虑了。
范·沃登接着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抹大拉已经怀了基督的孩子。
抹大拉被人放逐到海上,乘着一艘没有帆的船,“据说——有很多种说法——马大、拉撒路、约瑟陪着她。他们在海上遇到了一场风暴。风暴喻指天使和追赶抹大拉的魔鬼们战斗。最后他们在马赛着陆,并在那儿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墨洛维。”范·沃登微笑着重新把他们的杯子斟满酒,“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吗?”
克莱姆好奇地瞪大眼睛问:“接下来呢?”
“哦,接下来是很多预言——如果你看过《秘经》的话,你就明白我说的那些事。”
“墨洛维怎么样呢?他遇到些什么事呀?”克莱姆追问。
“他很了不起,建立了墨洛温王朝。”范·沃登弯曲食指呈引号的形状,并接着说,“长发王朝。”
“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克莱姆问。
“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从来不剪头发。”
“为什么不剪头发?”邓菲疑惑地问。
“因为他们的头发有魔力——他们的头发、呼吸、血液都有魔力。”范·沃登停了会儿,又说,“瞧,我们在谈论传说。有亚瑟时代……圣杯时代(传说中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过的),决定你谈话对象的是杯子——或者世系。”
“你所说的世系指什么?”邓菲问。
“刚才我说的:世系。特定的世系。基督的世系。从墨洛温王朝的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从国人到国王个个都是魔法师,有魔力的人。”
“有什么样的魔力?”克莱姆问。
范·沃登微笑着点了支烟说:“据说他们只要用手抚摸患者的伤口,伤口就会愈合。他们亲吻死者,死者就会复活。他们会和鸟类对话,他们能像蜜蜂一样飞行,他们可以与狼和熊为伴追捕猎物。他们操控天气变化,还有——噢,有人说过,那是个神秘的时代。”范·沃登停顿片刻又接着说,“有人说那是蓄意的神秘时代。”
“此话怎讲?”邓菲问。
范·沃登似乎有些不安,“噢……有些——我不该称他们为历史学家——确实有人感觉到所谓的黑色时代(欧洲中世纪)并不存在。他们说那个时代应该是黄金时代,今天我们之所以说它黑暗是因为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视野。那个时代变得黯然失色是因为……某些机构期望这样的结果。”
邓菲想起他在看《阿契尔斯》时,曾看到过这种说法,就问:“你指谁?”
“罗马。罗马引领整个西方历史。神父记录并保存当时发生的事件——他们会依他们的设想涂抹掉历史。”
克莱姆盯着他问:“你是说……像苏联那样?把人从照片中消除掉?”
范·沃登耸耸肩。
“你是说教会中断了欧洲三百年的历史?”邓菲问道。
范·沃登摇头说:“这是阴谋理论,仅此而已。我跟你说的不过是转述他人的话,不必大惊小怪,看看耶稣会对玛雅历史做了些什么。”
“玛雅历史?”邓菲问。
“我正要说。”
“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做?”克莱姆问。
“依据理论?”
“没错。”
“肮脏的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他们无法隐瞒罪行只好涂抹掉黄金时代的记录。”范·沃登看到邓菲不解的样子就开始详述,“墨洛温王朝的人持异端邪说。他们声称自己是神的孩子——照字面看是神的子女——他们放弃了所有其他的王位以及长期以来不合理的统治权。如果神自己的孩子(或者孙子)在巴黎称王的话,罗马还需要一个教皇吗?这是历史上最危险的异端邪说。正是因为这些,墨洛温王朝的人被绑架,被暗杀,被出卖,直到最后他们所有的统治痕迹都被涂抹掉,他们便就此从历史上消失了。”
“直到《秘经》浮出水面。”邓菲说。
“正是。当这些异端邪说因《秘经》的出现,得以重见天日时,就必然会遭到镇压——也确实被查禁了。信徒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最后他们只能作为一个秘密团体,一个被通缉的阴谋团体存在着。
“他们密谋做什么?”邓菲问。
“光复至福一千年,”范·沃登回答,“还有什么疑惑?”
“他们打算怎么做?”邓菲问。
“一旦预言应验,那就是既成事实了。”
“这些预言——”
“——在《秘经》里写着。”范·沃登回答说。
“你是说加密和天空——”邓菲说。
“你知道这些!”范·沃登惊叹。
邓菲耸肩说,“我曾看过一些相关的材料。”
“当然,不是所有的预言都这么……诗意、浪漫。有些很特别。”
“比如说……”
范·沃登耸肩说:“所有的土地将会统一。”
“这很特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