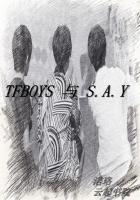帝国的骑兵到来的时候,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偌大的庭院,横七数八地躺满了人,仅有还站着的,便只剩月凛和阿篱而已。
将场间的情形与中队长交接妥当之后,阿篱对月凛提出了一同回到大营的邀请。
自然是没有拒绝。
回营地后,首要的事情便是将阿篱送去就医,军医说没什么大碍,只是内腑有轻微的震伤,给她开了一些固本培元的方子。
阿篱听得这诊断,心想:那白狼将自己用半中击落的一下,力道极强,若是没有月凛,自己恐怕已经没有命回来,可那小子不但接住了自己,还将身上的劲力化去了十之八九,让自己只受了这点轻伤。
越是细想,越觉得这个叫月凛的少年,深不可测。
……
换了一身单薄凉爽的单衣之后,月凛独自一人躺在宽敞的帐篷里,想想接下来要做的事,一下子困意全无。
睡不着的时候豁达一点,起来散散步最好了。
月凛走进了阿篱的帐篷。帐篷的烛光已灭,少女已入睡,少年走向床边,静静地坐在病榻旁的椅子上。
少女的黑发自然地披散着,显得十分柔顺,洁白的月光洒在汐微微苍白的美丽脸庞上,神圣而温柔。
突然,少女睁开了眼,然后她看到了呆呆看着她的他,看到了他漆黑深邃的眸子。
……
夜色正浓,一对年轻男女四目相对,本是极妙。可问题是,虽然这里不是闺房而是营房,少女睡的不是绣床而是病榻,但一个男子未经允许就走了进来甚至在床边坐下,仍是大大地有违礼数。
所以二人的对视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便双双于慌忙中收回目光。
沉默。
月凛侧过身去不敢抬头看阿篱,但神色中似乎只有羞而没有愧。
山里来的野孩子哪懂得什么礼数,他只是像初遇时一样不敢与她对视而已。
但是阿篱懂,只是想到醒来的那一刹看到的眸子,竟忘记了指责,而是说了另一句话打破了沉默:“夜这么深也不睡觉,你是谁家养的夜猫子。”
“白天昏倒时就睡了许久。”
阿篱没想到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回答,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笑起来就像昙花一样美。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
“你真的,是从雪山下来的?”打破沉默的依然是阿篱。
“恩,我是来找姐姐的。她在我十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算算已经九年了。”
阿篱心道,这个小子原来跟我同年,只是你姐姐已经离开了近十年,又如何找得到。但又不敢说破,于是问道:“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姐姐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没了?”
“恩,没了。”
阿篱心中大呼无奈,不过她对这个少女确实有许多的好奇,于是不断地盘问起他来。月凛也不再似方才那般害羞,慢慢打开了话匣子。阿篱听得也格外入神,讲到雪山上的平静生活时,便带着一脸微笑;讲到姐姐离开时,也跟着一脸沉重;讲到下雪山时碰到的野兽雪崩之类的种种险境时,就似身临其境般,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少年十岁时,姐姐离开后,便独自在那荒无人烟的雪山上生活到如今,也算是孤苦。而阿篱也在那一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母亲,说起来两人倒算是同命相怜。于是闲话也就越拉越长,不觉间,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
天蒙蒙亮时便有鸣号,镇西将军许庸来了。
许将军来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审问昨夜被擒住的人犯,也不是集合营部训话,而且径直走进了阿篱的营帐。
这位身材魁梧,面庞刚毅的中年男人走进营帐的第一件事,便是指着阿篱的鼻子大骂:“你胆子也太大了吧,难道以为自己是大将军,能像他一样勇猛无匹?那铁掌帮没有知根知底,你就算修为再好,也没有必要一个人去吧!多亏了这位月公子,不然我们只能去给你收尸罢!”
骂完一阵,许庸复又叹一口气,道:“你这丫头,若是出了事,我如何向你父……你师父交待啊。”
阿篱知道将军的严厉实质是关切她,便也只好低头认个错:“许叔叔,是阿篱不对,阿篱以后不会这样了。”
阿篱只是天畔营部的监察,主管着数个细作而已,却能得一方将军如此的关切,换作是旁人,肯定是吃惊不已,但月凛不谙世事,也并未觉得如何奇怪。
许庸知道阿篱脾性,料是就算她这么说也不见得真的能这么做,于是说道:“罢了罢了,不提此事了,那帮反贼的事处理地如何了?”
“我昨夜去探听时,听到那帮主成世离说,‘有位大人,不久后将要来到台前,成为帝国新主’。”
许将军的眉毛皱成了倒八字:“果真胆大包天,只是不知他口中的那位大人是谁。”
“营部长已经连夜派人审问,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报!——”突然,营帐门被掀开,传令官奔了进来:“禀将军,那铁掌帮主成世离自杀了。”
“什么!”阿篱惊地坐了起来,却不小心牵动内伤,猛地咳了起来。
许庸摇了摇头,好言劝慰阿篱躺下。
少女重新躺在病榻之上,皱眉说道,“成世离此人貌似从容,实则胆小如鼠,凛在击败蛮三狼后,他连反抗都未做,第一时间便是想逃跑,这样贪生怕死的人怎么可能会自杀。”
既然不是自杀,必然是他杀,能在军中大牢杀人的,必然是军中的人。
许庸虽然名庸,但也并不是平庸无能之辈,当即明白了她的意思。他立刻压低声音:“若反贼的势力已经渗进了军中,那将会是极轰动的大案子。甚至会牵扯到大人物。”
“我要查。”
“说得简单,眼下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要从何查起?”
“这事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回京找师父帮忙,以他的人脉,肯定已经有这方面的线索了。”
“你想找大将军相助确实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事倘若跟大将军有关呢!你也知道最近的流言,若此事的幕后主使真的是他,你岂不是羊狼虎口。”
“许叔叔莫急,阿篱昨夜也冒出过这个念头,不过细想后便知道不可能。师父的为人我再清楚不过了,四方平乱后,为了稳定皇权,他主动交出军权,一直闲居在京中,早已不过问天下事。若他真的有这分心思,当年他手握军权之时,便可以直捣黄龙,帝国也不会有今日。”
许庸捋了捋胡子,点头应道:“如此确是有理,然而现下并不太平,我镇西军地处荒僻,都能发生这样的案件,若是回到中土,更不知有怎样的风浪。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
阿篱狡黠一笑:“这个嘛,我想就不用您担心了,我已经想到了合适的人选陪我同去。”
说罢,少女努了努嘴,指向了站在一旁似木头桩子似的月凛。
“我?”方才两人一番对话,月凛早已是听得云里雾里,此刻阿篱突然指向他,一时间他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错,许叔叔,这位公子的武道修为阿篱可是见识过的,他要是真的想,就算拔光您的胡子,您也没有办法碰到他的衣角,”话到一半,少女又转向少年,说道,“你陪我回京都,我帮你找姐姐,如何?”
“啊?!”两声惊呼同时响起,一声发自有些羞怒的许将军,另一声则是惊中带点喜,这声音的主人自然是这位木头桩子月凛了。
阿篱对着许将军吐了吐舌头,再转过头来对月凛说道:“我师父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我请他帮忙,一定能有你姐姐的消息。”
原来凌晨时与月凛的一番长谈,让阿篱对月凛大有同命相怜之情,现在又打算查这桩造反的案子,眼珠一转,便想出这么一桩两全齐美的法子来。
“好,我答应你。”说完这句话,凛再也绷不住自己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有些羞涩地笑了起来。
见着月凛的笑容,阿篱心中暗道:这个小子笑起来倒还挺好看的,只可惜是个木头,现在心里只记得姐姐,不然我介绍两个京中的好姐妹给他,说不定能促成一段姻缘。
许庸细想之下,也认为这是良策,不过他依然担心阿篱的安危:“月公子武艺超群,这事倒也是可期,不过想要我答应,还需月公子再答应我几件事,月公子请随我来。”
说罢,便将月凛请出帐外,单独说话去了。留在帐内的阿篱,坐在病榻之上,鼓起双颊,自语道:“许叔叔肯定又说些有的没的,他要是敢将我的身份说出去,我今天就要将他的胡子全部揪下来!”
……
“月公子,你与阿篱这丫头素不相识,却能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救她,这样的大恩,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公子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只要是许某能办到的,绝不推脱!”
月凛第一次与许庸交谈,很是拘谨,说话的声音也是如蚋蚊般小:“姐,姐姐说过,知恩图报。阿篱姑娘先救过我一次,如今她有难,我自然是要出手的,报酬什么的可不要再提了。”
许庸为人豪爽,听得此言,大笑三声:“好,好,好。公子如此年纪便有这样的修为和人品,日后必定大有作为。不过我现在邀你出来,却是另外有事相求。”
“将军请讲。”
“阿篱这个丫头,身份有些特别,这回京的路途遥远,护她周全自是不用说。我想说的是回京之后,切不可让他师父师母,也就是大将军和将军夫人之外的第三人,知道你们二人的行踪。”
“她究竟是什么身份?”
许庸故作深沉地笑了三声:“嘿嘿嘿,这个嘛,就不便与你细说了。”
……
这是一个宽敞昏暗的房间,四面无窗,屋内仅有一方长桌,长桌的两头各有一把长椅,长椅上各坐着一人,一支红烛摆放在长桌正中央。被烛光映照的两个身影,一个年轻挺拔俊秀,一个略显苍老伛偻。
“虽然我接活不问原由,不过你让我杀一个年轻姑娘,倒是挺不合我胃口的。”年轻的身影说道。
“墨之佣兵团做事向来不问原由,只凭好恶。此事我确有耳闻,不过老夫倒也知道天问先生好的是什么,”苍老的声音从长桌对面传来,他从兜中取出一个布袋,抛向对面,说道,“这些天问公子可还喜欢?”
被称为“天问”的年轻身影轻轻接住布袋,打开一瞧,袋里尽是翡翠宝石,少说也值得上十万两白银,天问有些压制不住自己的喜色,抱拳道:“老先生就是爽快!我去召集弟兄,明日动身。”
苍老的身影微微点了点头,那叫天问的男子便离开了密室。
屋内只剩一个略显苍老的身影,他的眼神好像苍鹰一般,似要看透人的灵魂;他的周身,隐隐有一圈强烈的气场在流动,密室内的空气都变得有些粘稠。
“我终究是个凡人,这肉身也有腐朽的一天。”
苍老的身影似乎在自言自语。
“所以我要在老到变成朽木之前,让这件事先我一步下地狱去。”
“九年了,我终于又嗅到了这股熟悉的味道。”
……
数日后,阿篱的伤势已经好了一大半,月凛雇了一名车夫,买了一些干粮草药,将阿篱扶上了马车。
马车离开小镇的时候,月凛回过头去,望了一眼白雪皑皑的月见山脉。
帝国历一百二十七年八月初,一名叫月凛的十九岁少年终于离开月见山畔,驶向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