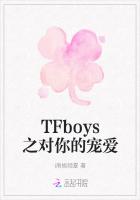突然,沈佩佩灵机一动,自己倒是想到一个绝佳的去处,安全保险,一般人绝对想不到。她踮脚走到门口,轻轻推开阁楼门,像小偷一样,鬼头鬼脑地探出房外,发现四下无人,琢磨着等一会儿顾班长一定会来催促她,到时候人多眼杂,戏班开唱,自己根本就没有时间另找藏处,便下定了决心,正欲出门的时候,“等下。”那青年顿了一口气,正正经经地说“沈姑娘,我好像忘了一个东西。”可沈佩佩觉得机会只有一个,拉着他的衣角就往下面走,那青年也只得无奈地摇摇头,觉得沈佩佩做事实在是冲动欠考虑。这阁楼与普通的房间不一样,为了方便通行,一共修了两条楼梯,右边这条通向戏院后台,而另一条则通向后院的小花园。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正当他们走到靠近花园的楼梯口时,后面冷不防地响起一个声音,不用回头都听出了这是谁,果然是顾班长来了,亏得沈佩佩平日唱戏,天生机灵,转身一推,将那青年藏到转角处,自己顺势靠在了朱漆门框上,恰巧挡住他的视线。
顾班长张着脖子,瞧沈佩佩已梳妆完毕,只缺几件戏服,心想这不过是片刻的事情,觉得这小姑娘调皮归调皮,大事终归是不误,便决定不追究她上午的事情,眯眼笑道:“佩佩,还不快过去,都这个节骨眼了,还在这里干嘛呢?”
“我瞧这花园的玉兰花开了,挺美的,便跑下来看看,只可惜今年天色不好,这花可得趁这几日晴天多开开。”沈佩佩故意提高了音量,望向那棵玉兰,意味深长地朝那青年使了个眼色。
“这丫头,又发什么疯呢,什么玉兰不玉兰的!还不快赶紧上来,迟到了我可不许你慧姐姐煲汤给你喝哟!”顾班长笑道,知道她们两姐妹感情深,沈佩佩又尤其喜欢她煲的莲子汤,便作势比了一个得意的样子,假装生气了。
“好馁,那,我就来了。”沈佩佩靠着栏杆往上走,像腻歪的小夫妻分别似的,恨不得一步三回头,但又怕顾班长发现,活生生地忍住了,只在转角的一瞬间偷偷瞥了一眼,那人站在楼下,望着自己,竟然咧开了嘴,笑得十分灿烂。不知道他听懂了自己的意思没有,也亏得他心宽还笑得出来,沈佩佩心想:算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自己也只能帮他到这个地步了,心下一横,便想跟着顾班长走,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沈佩佩突然觉得这种感觉似曾相识,走了几步,又回头望向楼下,但那里空空如也,那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怎么了?佩佩。”顾班长见沈佩佩突然停下,以为她哪里不舒服。
“没事,没事。”沈佩佩却什么也不说,继续往前走了。顾班长摇了摇头,这丫头从小就有些古怪,不敢一个人睡,硬是说半夜听到鬼说话的声音,还经常莫名其妙地说后面有人,一开始顾班长挺注意的,还专门请过道士驱邪,但时间久了,也就不当回事了。那段时间沈佩佩的母亲去世了,她把自己关在阁楼,整整呆了两天,滴水未进,顾班长实在是担心,心一紧,莫不是那丫头如此想不开,寻了短见不成,便派人撬开那门,只见窗户大开,沈佩佩安安稳稳地趴在外面那棵玉兰树上,闭着眼睛睡觉。自此以后,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整天嘻嘻哈哈地,再也没有提过这些事了。
话说,回到戏院,约莫半个时辰后,顾班长到是回来了,安然无恙地,毫发未损,沈佩佩扶着顾夫人,能明显感觉到身旁紧绷的身体放松了起来,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只是顾班长身旁跟着一个高大的年轻军官,身着军绿色制服,手戴黑皮手套,看起来雍容华贵,长得也是眉清目秀,奈何戾气太重,冷峻的脸庞上没有任何表情。要说来“碎锦”看戏的人不少,包场的阔老爷,有钱的士绅,掌权的官员,普通老百姓,街头小混混,沈佩佩自诩“阅人无数”,可有句话说“老马失蹄”,说的就是他这块“绊脚石”吧,看他一副不得了的样子,恐怕不是那么好对付,心里隐隐地为顾班长感到担忧。不止沈佩佩,顾班长心里也直犯嘀咕,算起来,他顾新芫在七里山唐街的地位,无人出其右;因推广自家班底,自然少不了交际应酬,靠着沈佩佩唱戏打下的名声,酒桌上觥筹交错,几番吹嘘拍马屁,加之逢年过节亲自登门“聊表心意”,也算是结交了不少大人物,其中自然不乏政界高官,军队也算是稍有染指。这个华筵,此般年纪就当上新军统领,真是闻所未闻,而且态度就像臭水沟里面的石头,“又臭又硬”,刚才在外面与他纠缠了半个时辰,竟半步都不退,还是硬生生闯了进来。底下到底是有见过世面的人,对身旁人耳语到:此人乃近年来新晋新军悍将华筵。说起这个华筵,可是大有来头,和四十五标标统刘之洁关系十分密切,而这个刘之洁直属江苏巡抚程德全,此次华筵亲自出动,或许是为程德全办事,声势如此浩大,无论如何,事情绝对不简单。而且关于这个华筵,民间传说他是华老爷的私生子,8岁之前一直流落在外,后来华老爷膝下一直无子,记起自己好像还有这么一个儿子,便派人到处寻找,后来接回了华家,委以重任,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
两排持枪官兵有条不紊小跑进来,风尘仆仆,两条军绿立刻呈现包围之势,封锁了整个戏院,随即一长脸官兵朝戏院内大声喊道“谁也不许动,新军华长官抓捕犯人徐踵羽。举报奖大洋三十块,若有知情者不报,一律按窝藏罪处分。”顿时,整个戏院鸦雀无声,人们面面相觑,留意周围是否有陌生面孔,以免到时牵连自己,可是到底是怎么样的犯人,悬赏如此之高?沈佩佩顿时心里一沉,知道自己已经惹祸上身,可是事情已经发生,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小子胆大包天犯下死刑,自己若将他交出去,不仅他小命不保,自己手上也间接地沾上了血;若硬挺着不交,恐怕到时候被发现了,又会落得个一事两命,自己大好年华,二八岁月,活生生成了那小子垫背的了!两难之际,沈佩佩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只能祈祷阿弥陀佛,祈求佛祖保佑那个小子不要他们被发现了。可话说回来,当时竟然没来得及问他名字,沈佩佩至此才知晓他叫徐踵羽。
顾班长心忧夫人,生怪自己平日杂事繁忙,无暇顾及三餐饮食,自己到不甚注意,只是每次腹痛难忍,巧慧心疼自己的身体,每日定时给自己送一碗西红柿蛋花面条,这面又烫又香,自从周巧慧嫁给他以来,顾班长都吃习惯了,可今日却不偏不巧,赶上这么个烂摊子,关键是她还怀着孩子,平时都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上的公主,哪里经得起一点刺激,心中十分后悔,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要巧慧给自己送饭。顾班长顾忌此事,变得唯唯诺诺,十分配合这群士兵,只希望尽快解决这里的事情,好早点带巧慧回家,安心备孕。
突然,一个人影从戏院外“飞”过,守门士兵拉开枪栓,朝大街放了几枪,便追了过去。那长脸士兵立即询问华筵,是否增派人手,华筵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淡,右手举起,示意他不用。沈佩佩一直留心,远远地观察着华筵,满心盼望他能撤兵出去,但没想到他如此聪明,一眼便识破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如果那人还在后台藏得好好的,刚刚那影子便很有可能是他的同伴,只要徐踵羽没有脱离危险,那么谁也走不远,到时候只要设下一个埋伏,就能一箭双雕,沈佩佩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人如此聪明,恐怕今日《痴梦》都还唱不完,自己便魂归西天,再劫难逃了!
正胡思乱想之际,顾夫人突然挣脱沈佩佩的手掌,紧紧抓住她的手臂,脸色如白纸一般苍白,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脸上显现出异常痛苦的表情。“羊水,好像破掉了!”周巧慧感觉肚子里面一阵一阵地酸痛,眼看就站不住了,沈佩佩赶忙将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左手紧紧环绕不让她倒下,右手摸了摸顾她裤子,黏黏糊糊的,发现已经完全湿掉了,一定是刚刚的那几声枪响,惊动了腹中的胎儿!于是大声向顾班长求救,顾班长心急如焚,直冲向戏台,长脸士兵欲阻拦,华筵招手示意放他过去。
可巧的是,底下看戏的有个张老太太,头发花白,满脸褶子,家住乐桥桥头,她年轻的时候是这一带有名的稳婆。提起来起来也怪,这一带流传一个说法,经这张老太太接生的,十有八九都是男孩,谁家有小孩出生都巴巴地派人过去请,她也因此摆起了架子,接生需要提前两三个月知会她一声,带上定金亲自接她上门,除了检查身体外,还要查看孕妇的面相,她说一句“好”,全家自然喜不胜喜,这等于判定这个孕妇将来会生一个儿子,不论放在谁家,这种意义自然不言而喻,不但喜糖喜酒少不了,张老太的酬金也是水涨船高,翻了几番不止。但老太太皱眉摇头的人家,被拒绝了心里就不是滋味了,横眉冷对,几番求教无门,希望好声好气地求她老人家再多看几眼,怕是搞错了,张老太一律不识相地都拒绝了,并且声明自己绝对不会搞错,无法,只得派家丁把张老太送到大门口,愤愤地,嘭的一声关掉大门,自此两不来往,所以她的口碑一直都是是两极分化。但无论怎么样,这老太婆子的本行是稳婆,好歹接生是她的分内之事,俗话说救人如救火,眼见顾夫人情况危急,她自告奋勇,挤出一条路,气喘吁吁地,爬上戏台救人。
“让她躺下来,屁股抬高一点。”张老太镇定自若地指挥到,沈佩佩站在旁边,急倒是急,忙得团团转,但实际上人小经验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人家生孩子,什么也不懂,紧张得只能握住慧姐姐的手。
“我估计是要生了,胎儿在里面动。赶紧把她抱到房间里面去。”张老太看顾班长这里急得跟沈佩佩似的,手忙脚乱也不知道做什么,便瞪了他一眼,吩咐他把夫人抱到里头房间去,总不可能在这么多人面前接生。顾班长看了看门口的华筵,感觉自己现在顾不了戏班了,只吩咐杨管家处理事情,把周巧慧的手搭在自己肩上,横抱着转头就往后台走。恰巧周嫂年纪大,自己又生过三个孩子,好多事情也都知道,便与张老太配合默契,看她照顾孕妇,不用知会就跑去厨房烧开水。
话说这一边,那长脸士兵是个不近人情家伙,心里面恨的牙痒痒,几次意欲阻止,但都忌惮华筵的权威,不敢出面。华筵不动,看戏的群众也没人敢动,他像一墩大佛一般凝视着他们,直到顾班长一行人将顾夫人抱到后台。他突然想起,在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夜,寒风凌冽,他的母亲在后院打水,天黑没注意,一不小心踩到了路上的冰,加上又穿着那种脚底很滑的棉鞋,整个人都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水桶里面的水撒的满身都是。那时候,她怀着华筵已经八九个月了,只觉得肚子非常痛,想叫人来帮忙,可是使了全身的力气都喊不出来,便硬生生地爬到了院子里面的牛棚里面,独自一个人生下了华筵。说来也巧,那母牛不久前才产下一窝小牛,也许是母亲之间的心心相惜,也许是见这个女人太可怜,蜷缩在那里瑟瑟发抖,便走了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牛棚的开口,不让风吹进来。她没有奶水,也是挤的那牛的奶,华筵的母亲哭着,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候,她没想到是一头牛救了他们母子俩的命。回想起往事,华筵的眼角有些湿润,他是军人,要执行父亲给他的命令,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对一个母亲下手。
“张副官,你负责这里,我一个人过去。”说着,一个带军衔的人走了过来,表情刚毅,额头上带着一条伤疤。
“好,三爷。”那张副官回答道,他自参军以来就跟着华筵,一起出生入死了好几年,也为他档过子弹,有着过命的交情。
华筵本就高大潇洒,加上穿着一身军大衣,配着披着貂绒衣领,走起路来飒飒生风,人群立马让开一条路。管家心想,顾夫人现在已经临盆,顾班长如此怜爱她,肯定不愿他人打扰,但无奈华筵去了后庭,便立马派他儿子去通知顾班长,另一方面又派了一个人给华筵带路,但没想到被华筵一脸冷酷地拒绝了。管家有些为难,但人家是好歹将军,便不敢多说一句,只得由他去。
阁楼里面传来周巧慧的哀嚎声,自古有句话:生孩子就好比走一趟鬼门关。顾班长把周巧慧抱进房间后,看到夫人这么遭罪,他自然也是想在房间里面,握着她的手陪着她,但张老太宣称妇女生小孩之时,男子不得入内,顾班长死磨硬泡,还是硬生生地被赶了出来。顾班长站在门外,觉得在夫人如此痛苦的时刻,自己却连陪都不能陪,只能在外面干瞪眼,实在是不配做她丈夫,想着想着便骂了声娘,正巧此时,管家那儿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顾大叔,我爹叫我过来告诉你,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官哥哥来咱们后台了。”
“什么官哥哥,管他娘的,我现在自己都管不过来了。”顾班长扒着窗户缝隙往里面看,可是什么也看不到,不耐烦地丢下这么一句。
“我去吧。”沈佩佩自告奋勇道。虽然她也想守着慧姐姐,看着她平平安安地生下孩子,可是比起来,现在慧姐姐更需要她丈夫,现在自己在这里什么作用都起不到。再加上徐踵羽还藏在楼下的小花园,如果被华筵发现了,他们俩有事倒无所谓,要是连累了他人,牵连整个戏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喂,佩佩啊,他爱去哪去哪,不要拦他,这个祖宗咱们可伺候不起。”顾班长心里一暖,很感激沈佩佩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但又担心她年纪轻做事不周到,便转头嘱咐了沈佩佩一句。
“恩,我会注意分寸的。”说罢,沈佩佩拉着管家儿子的手就往外面走。
穿过了几个房间,在院子的转角处,沈佩佩瞧四下无人,便蹲下来,摸了摸小孩的头,温柔地对他说:“现在没事了,你回去吧。姐姐现在就去找那个官兵哥哥。”管家儿子在戏院最喜欢的便是这个姐姐,长得十分好看,尤其是喜欢看她笑,嘴角有两个甜甜地梨涡,而且人也温柔,平时对他也极好,每次犯了错他爹要打他,都跑到沈姐姐这里来,这个姐姐总是帮他说好话,让他少挨了不少的打,所以非常听她的话,点点头便高高兴兴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