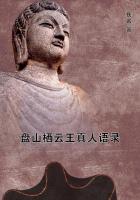“小米,进来吧。这马上要拆迁了,帮我看看还有啥东西要拿的,不然过几天推土机一推就啥也没了。”三跨进了屋。
“嗯,是得赶紧找找,别屋子里埋得金元宝被人给挖了去。”我再一次跨进了屋。
三突然转过身,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你可别不相信,我爸翻房子那年,从地下还真挖出一罐袁大头来,那银元铮光发亮,吹着还带响呢。”
嚯,我啥时候这么灵了。“你爷爷奶奶都不知道吗?”
“问了,不清楚。反正这是我家祖宅,要有也是我家老祖宗留下的。哦,还挖了好几罐什么大清光绪、中华民国的铜板。”
三拉着我往里屋去,“你跟我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这不就是汤婆子嘛!”我看着眼前黄澄澄的一个铜罐子,铜身上打磨的亮亮的。
“这就是那些铜板打的。”三打开盖子,“看见没。”只见塞子地下还垫着一枚铜板,已经锈蚀的看不出纹理了。
“浪费啊!那么多铜板不比这铜罐子强。这玩意冬天捂脚还得包好了,不然把皮都给烫了。”
三悻悻道:“当年谁在乎铜板啊,还是这个实惠。”
我点点头,说的也是,当年我还拿着一个乾隆的小钱挂在钥匙扣上,这丢了也是丢了。
进了里屋一看,东西摊了一地,柜子橱子里的抽屉都给翻了出来,床上扔着一大堆的衣服,这场景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遭了贼呢!
“三,你这干的和当年的鬼子差不多啊!”乱物堆里我一眼就看见了只黑色的皮革包。
这可是好东西啊!当年拎着这可不亚于现在的LV包包之类的。看,这包上印的楼房,这上面的SH两字,那就是身份,档次,品牌。
那时候SH亲戚到我家来,就是拎的这样的包,手上戴着宝石花手表,一身中山装,胸前插只钢笔,看着既潇洒又有派头,从包里一掏就是大把的大白兔奶糖。
我把它从杂物堆里拎了出来,包上的拉链还是好的,就是这皮革有些皲裂了。“三,快来,你家的宝贝。”
“送你了,你看上什么自己拿。”三头也不抬的坐在地上,正看的津津有味。
我凑过去一瞧,原来是本武侠书《黄金瞳》,这纸张都有些发黄了,我说这家伙咋爱看书了。
我们小时候可不像这会对着手机,电脑拼命,那时候男生看武侠,女生看言情,厚厚的一本书一捧就是大半天,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
翻翻杂物堆真是挺有意思的,感觉像是找寻过去的记忆。这条裤子,顺着摸挺滑,倒着摸起绒,就是常州灯芯绒厂生产荷花灯舞牌的灯芯绒裤子。我拎起一件的确良的白衬衫,领口有些泛黄了。这的确良的衣服当年可算是人手一件了,现在看着挺亲切。
一只塑料袋里装着些邮票,看样子是从旧信封上撕下来的,上面还盖着印戳。邮票我也曾收集过,只是后来没多少人写信了,这集邮才慢慢给放下了。最多每年到邮政局买些现成的年册,不过感觉不再是因为兴趣,因为这一张张簇新的邮票对我而言失去了记忆,更多的只是对过去集邮的不舍,再之后,我干脆就不理会了,邮册堆成了灰也不再看,没有情感寄托的东西实在勾不起我的热情。以至于后来曾把热情转移到烟标上一段时间,像雪峰、大前门、老刀,牡丹、红塔山、红梅阁、良友等等。
“三,这件线衫不错,留给你孩子穿。”我拎起衣服给三样了样,就是小点,看着还挺时髦。
三回头看了眼:“这是我妈织给我爸的,不错吧。”
这件黄色的马海毛线衫上面还织着铜钱花的图案,看着真是漂亮。不是有人说过嘛,衣服收起来放个几十年,再拿出来就又成了最时髦的款。
“三,你家可以开个常州工业博览馆了!”三家的老古董居然都还在。这方方正正的是常州电视机厂产的17寸幸福牌黑白电视机。旁边还有台常州产的熊猫彩电,只是贴的南京的牌子。
这是飞牌的洗衣机?居然壳子还没烂掉,不会还能用吧!这个应该没坏,双喜牌的台钟,发条紧紧就能走了。
这是星球牌收录机,这是南极牌电风扇,这地上还扔着包国营常州床单厂的双叶牌床单。
“三,这些都扔了怪可惜的。”我看看这些曾经红火一时的地方名牌叹息道。
“可惜啥,都老掉牙了,这些厂子都早没了。”三伸了伸腿,脚碰到了桌子。
“哎,你当心,别把青花瓷给摔了。”我冲过去把桌上的瓷瓶给抱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