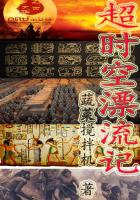要找当然得找正主。
这天一大早,酒楼还没开门,胡玉儿就来到了店里。四下里随意看了看,就拖着我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高俅还在蒙头大睡。
也不知道是胡玉儿今天是心情不好还是心情太好的缘故,看到高俅还在睡觉,胡玉儿走到床前,一脚踹在高俅身上,嘴里呵斥道:“你这比猪还能睡的高二,还不给老娘起来!”
高俅翻身而起,刚准备发作,一看是胡玉儿,便将一腔的怒气生生地咽下去了几分,嘴里却依然怒道:“牙婆,我高某人想吃便吃,想睡便睡,就算当猪,那也是我高某人愿意,与你有何干系?”
胡玉儿柳眉倒竖,两手一叉纤纤细腰,呵斥道:“你高二在别的地方当猪,姑奶奶我管不着,不过你想在这里当猪,还得先问问姑奶奶我答不答应。”
“我草,你当你是谁,大老爷们的事,凭什么要你一个妇道人家答应,你是我老娘还是我娘子?”高俅一脸轻蔑道。
“就凭我是这酒楼的股东……”刚说到这里,胡玉儿猛地一顿,随即大怒,“你这腌臜货,敢占老娘便宜,老娘今天不打得你满脸桃花开,这胡字老娘就倒过来写!”
说着,顺手操起高俅放在床头边的那根齐眉哨棍,劈头盖脸向床上的高俅打去。
“牙婆,你今天要敢动我一下,我高某人这辈子就和你没完。”
高俅怒吼着,手下却一点也不含糊,两手抓起被子,整个人往被子里一缩,四下一拢,紧紧地在床上团成了一团,速度之快,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胡玉儿下手也够狠,那棍子忽地一下就飞了上去,之后,棍子就化做了棍雨,往被子上劈劈啪啪地落了下去。
“我是你老娘”“我是你娘子”“打死你这不知孝顺的畜生”“打死你这不知廉耻的腌臜货”……
胡玉儿的嘴里不见半分停歇。
我没有去劝。
说实话,我老早就想揍高俅这厮一顿,就怕他还手,到时候我鼻青脸肿不说,就连他对一个先生应有的最起码的尊敬只怕也没有了——就算有,也被打上了折扣,和没有也没多少区别。
现在,胡玉儿将高俅一阵痛扁,我看着当然开心,暗自高兴。
不过看着看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起初的时候,那团被子还在床上不停地挣扎,被子下还能听到阵阵的嘶吼,但是现在,被子下不但没有了嘶吼声,就连被子也停止了挣扎,没有一点动静。
“坏了!”我心头一惊,“难道高俅被打死了?”
赶紧上前,架住了胡玉儿的手,嘴里急忙道:“胡大姐,你不能再打了,要出人命的!”
“这泼皮捱得住,还请先生让开,莫要拦着我。”胡玉儿一边挣扎,一边说道。
眼见拦不住,我怒吼一声,“你还打,没见他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吗?”
听我这样一说,胡玉儿也停了下来,一脸的疑惑。
“我觉得我还没怎么打,怎么就……这不会闹出什么人命来吧?”胡玉儿看着我问道。
“只怕已经闹出人命来了!”我心头发紧,嘴里更是涩得发苦。
难道历史就这样被改变了?
看着床上那团静静不动的被子,感觉自己整个人就像是落入了冰窖之中。
历史会不会被改变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不是我操心得过来的事情,更何况我也操心不了。我担心的是,高俅要这样死了,我的未来不全都没有了——五大名瓷,苏黄米蔡,清明上河图……这一切的一切,我该找谁要去?
我怎能不心痛!
不错,高俅死了,赵佶——也就是未来的宋徽宗还在,可赵佶或者宋徽宗哪有高俅好使。
先不说我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就算赵佶成了宋徽宗,念及我和他的那一点点交情,把我变成他的臣下,把本应由高俅坐的殿帅府太尉的位置交给我来坐,可我也不能天天跑进皇宫,涎着脸对宋徽宗说,“官家,你这件汝窑笔洗不错,可否赐予臣下”、“官家,你这只定窑的画缸臣下看着实在喜欢,臣下能否将它搬回家”……
一次两大概没什么问题,三五次或许也有可能,可要再来,别说是皇帝,就算是我——谁要敢从我家搬东西,我不弄死他那是因为我不在家。
这就和蹭饭是一个道理。
当然还有别的法子,譬如说收点孝敬或者接受点贿赂什么的。可一想到那样的一副吃相,我又觉得恶心,真要做了,先不说会不会在回去的时候被那道闪电给劈死,只怕我自己都会被自己给恶心死。
再说了,收了别人的东西总得给别人办事不是。可真要把那些装满了一脑袋猪油的家伙弄在了关键的位置上,大宋朝因此而灭亡,我的罪可就大了去了——倒不是说坏了名声,在我看来,名声就是个屁!
关键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无数的小老百姓被金人像牲口一样宰掉或者真变成牲口吧?尽管北宋以及之后南宋的结局就是这样。
不是我做的,又没有经过我的手,我就能问心无愧!
但是现在,高俅死了!我的银行就这样破产了,我的印钞机就这样从我眼前不见了踪影,我未来世界里的富贵就这样消失了……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小镇上的那个老头是何等的一种幸运,至少他还为他的四条儿每人挣下了一栋小洋楼,可我呢,这座酒楼我能背回我的那个未来世界吗?
对了,我还有两幅字……该死的,我竟然忘了去催高俅,把黄大师的那幅“一家人酸汤鱼”的印鉴给补上!
还好,还有赵佶的那幅字在,就是尺寸有点小,才八个字……不知道能卖几个钱?
这唯一的安慰,支撑着我没有瘫倒在地。
大概是看到了我难看的脸色,胡玉儿的脸色也有些不太好看,犹豫着,胡玉儿问道:“要不……揭开看看,说不定……说不定只是……只是晕了过去……”
瞪着胡玉儿,我一言不发。
咬了咬牙,胡玉儿放下手里的哨棒,然后走到床前,伸手揭开了被子。
被子下,高俅一动不动,裸露的肌肤上呈现出道道淤青。
胡玉儿一脸阴霾,嘴里喃喃道:“难道……这高二真的就这样挂了……不应该呀!”
“呼”地一口长气,我和胡玉儿顿时愣住了,不等我俩反应过来,高俅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嘴里嚷嚷道:“可把我给憋死了!”
“好你个高二!”胡玉儿见状,一脸胀红,怒喝道,“你敢给老娘诈死,老娘今天不给你摆出个十八般模样,老娘就跟你姓。”
说着胡玉儿俯身拾起了地上的哨棒。
我赶紧上前拦住。
“先生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给够了她面子,她要再这样,我可真的还手了。”
高俅嘴里说得凶狠,行动却一点也不慢,抱起床头的衣服,纵身下了床,趿上鞋,一溜烟地就逃了出去。
我和胡玉儿目瞪口呆地看着门外,都有些想不明白,捱了这么多下,高俅竟然还能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泼皮,就是欠揍!”胡玉儿把手里的哨棍使劲往地上一扔,转身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盯着门外,一脸的恨意。
看了眼胡玉儿,又想到刚才的情形,这似乎不像我认识的那个高俅,“莫非……莫非高俅这厮喜欢上了胡玉儿?”我暗道。
见胡玉儿还是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我赶紧岔开话题,问道:“胡大姐莫不是找我有事?”
胡玉儿长长地呼了口气,等到整个人完全平静下来之后,这才点点头,“是有点事。”胡玉儿说道。
我没有开口询问,而是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等着胡玉儿的下文。
捋了捋额前稍有些凌乱的秀发,胡玉儿开口道:“先生有没有听说过康平坊的四海酒楼?”
虽说我对东京城不怎么熟悉,不过既然干上了饮食这一行,对东京城里那些有名的酒楼多少还是知道,只是这“四海酒楼”,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摇了摇头。
胡玉儿看着我道:“四海酒楼虽然不出名,不过只要到了康平坊,随便找个人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胡大姐一大早过来,就是告诉我这个?”我问道。
“当然不是。”胡玉儿笑了笑,“我不过是听说,前段时间在酒楼闹事的那四位公子,今日正午要在那里宴请重要的客人,我想先生肯定有兴趣,所以特地赶过来告诉先生一声。”
“谢谢胡大姐!”我道了一声。
“谢什么谢,要谢那就见外了。”
胡玉儿摆了摆手,“别忘了这酒楼可还有我的三成份子,来这酒楼闹事,也是在砸我的饭碗……要是可以,我恨不得将那四个家伙亲自手刃掉。”
胡玉儿叹息一声。
我丝毫不怀疑胡玉儿的话,也相信她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胡玉儿早就一声不吭地让这四个家伙去见了阎王。
但胡玉儿却不能够这样去做。
我没有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