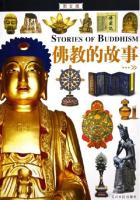索氏说:对与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时赚了多少,错时赔了多少。更要紧的是,当你认为对时,就要大胆去赌一把。过分小心谨慎,往往会失掉良机。再说了,富在险中求。为此就不能不兵行险道,剑走偏锋。何况这次是有惊无险呢,你赶快去调动100亿资金吧。
9月16日,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三”。但对索罗斯而言,却是一片春光明媚,艳阳高照。当他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杜肯米勒的电话来了。他对索罗斯说:乔治,你刚赚了9.58亿美元。
事后最终盘点,在这次狙击英格兰行的战斗中,索氏净赚了整整20亿美元。除10亿英磅之外,另外10亿来自意大利和东京的股票市场。
据此5年之后,索罗斯在东南亚又打了一场更漂亮的金融之战。
当人们正在为亚洲神奇的繁荣而欢呼时,索罗斯却敏感到这种用“泡沫经济”鼓吹起来的虚假繁荣,就像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一样,必然会土崩瓦解。但对索罗斯来说,这无疑又是一次发财的大好时机。他说:
我不能相信现在的繁荣不会紧随破灭。
索氏用他“荣枯相生”的走势标尺,率先牢牢地卡在早已被“泡沫经济”鼓胀起来的“泰国虎”的脖子上。
一天晚上,杜肯米勒又打电话给索罗斯,说:“乔治,你又有机会发笔大财了。”
索罗斯在电话中问他:“目标是不是东亚那只泰国虎?”显然,索罗斯早已胸有成竹。
他说:“不错,泰铢肯定快完蛋了。”
索罗斯问他:“整个仓位建多少?”
他想了想,大胆地报了一个数字。索罗斯毕竟财大气粗,一听他只报了区区几十亿美元,便冲着他说:“你总是胆小怕事,在对市场做出正确判断后,舍不得投入大本钱。”
杜氏说:“风险太大……”
索氏说:“只有高风险才会有高利润,在你知道你对时,就要全力投入,正像桶里捉鱼一样,只要桶子还在,就要不停地去抓。”
杜氏问他:“那准备投入多少?”
索氏毫不犹豫地说:“可以把整个仓位建在150亿美元左右,大赌一把。”
就这样,一锤定音,地动山摇。
朱利安·罗伯逊等大炒家,也闻风而动,说:“有钱大家赚,我们联手扑杀泰国虎。
于是,炒家们暗中调动资金,全力以赴,向泰国金融界发动了攻击。
就这样,一场金融大战便在泰国率先打响了。
说起来很复杂,其实做起来却很简单。
索罗斯等炒家们,主要采取以下办法:
第一,借入泰铢;第二,抛泰铢,买美元;第三,抛美元,买泰铢;第四,再抛泰铢买美元;第五,放弃盯住汇率,泰铢贬值;第六,低价购入泰铢;第七,偿还泰铢、获利。
泰国为了保卫泰铢,除了固定汇率和提高利率外,就是禁止传媒发出对泰国经济不利的消息,企图把它锁在“黑箱里”。
殊不知,愈是想让人们看不见,人们愈是想看,到底黑箱里卖的是什么药?
国际炒家们正好利用了这一点,趁机散布消息,说泰国已黔驴技穷了。又说:
泰国金融不稳!
泰铢要贬值!
结果,便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应该赶快卖掉泰国股票,抛出泰铢买美元……”
不久,美国一些行也大登广告,招揽汇款到外国去做生意。为防泰铢贬值,进口商家也提前结账。于是,很快形成一种抛泰铢、买美元的风潮。
就在这种波动中,炒家们大量买入预期泰铢汇率下跌的泰铢/美元的期货合同。
这样做,当然有两种可能。
如果泰铢升值,那么卖家就赚钱;如果泰铢贬值,那么买家就赚钱。
双方都有可能成为输家,双方都有可能成为赢家。
但毕竟只有一个结果,不是输家,就是赢家。二者必居其一,总有一输一赢。
炒家们是瞄准了泰铢非贬值不可的,所以才大量买入泰铢/美元的期货合同,而且十拿九稳地等着“泡沫”的破裂。他们也深信,五彩的“泡沫”一旦被引爆之后,会给他们带来高额的回报。
果然,事情比炒家们预计的还要顺利。他们买多少,泰国行就卖多少,似乎备货充足,保证供应。这倒把炒家搞糊涂了,一时不免有些犹豫起来,不能不考虑太顺利了反而会不顺利,还有可能造成判断上的失误。
偏在这时,又从泰国行传来一句恶言:说“不怕死的就只管来”!
但炒家们再一分析,泰国的外汇储备就那么区区300多亿美元,外债却高达1000多亿美元,还有烂账400亿美元,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这分明是以进为退,以攻为守,说穿了还是在玩“数字游戏”,同样是“泡沫”。于是又张口吃进。
泰国行,见期权合同的需求量大增,始以为奇,但又觉得这种增加对自己有利,所以便毫无顾忌地只管卖。稍后发现对方胃口太大,尽管有所警觉,发现苗头不对,但素来“打肿脸充胖子”的泰国人,从来讲究的是“输人不输阵”,虎死也不倒威,所以仍然硬着头皮卖。
一方只管“买”,一方只管“卖”。
双方都咬上劲了,正如侠客比武交手一样,奇招迭出,险象环生,直斗得难解难分。这时,谁先让手,谁就是输家。
这是“力”的交锋,也是“心”的较量。
这场买卖,双方交手的武器不是刀枪,而是“货币”,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到了1997年5月份,泰国行一看,有8至9成的远期合同,差不多都落在炒家们的手中。若再“玩”下去的话,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于是,这才不得不停止合同的发售。
但可惜的是,为时晚矣!
等泰行刚刚回过神来时,一个抛售泰铢的汹涌浪潮,已扑面而来,势不可挡。
政府为了保住泰铢,立即向邻邦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紧急求援。在短短几天内,就耗去100多亿美元,花掉了全部外汇储备的1/3。
但这100多亿美元投放出去,就像一盆水泼在干枯已久的地上一样,根本于事无补。泰铢仍然被大庄家们源源不断地掷了出来,并很快引起了连锁反应。汇市股市皆应声直线下跌,抢购黄金的风潮也汹涌而来,接着又引发了政治危机。
1997年7月2日,这一天对泰国来说是个“在劫难逃”的“厄”日。
泰国再也受不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泰铢迅速贬值。
7月1日,1美元可兑25.9泰铢;到了10月,1美元则可兑到40.6泰铢。而且,泰铢还在狂泻暴滑,直至贬值50.21%。
这就是说,如按此结算下来的话,那泰国所欠的外债已翻了一倍多,而国民财富50%已顷刻付诸东流了。
炒家们成了大赢家。
泰国则成了大输家。
接下来是兵锋南下,直指马来西亚群岛诸国,再横扫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是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读,也是对索罗斯的重新评估。
索氏“投机取巧”的最大成功秘诀,就是他掌控了“天下禅机”的神秘支点,所以才撬动了“地球”。也就是说,他的直觉与胆识的“情商”
(EQ),占了80%;而理智意志的“智商”(IQ、AQ),仅占20%。
人们常说:“天助我矣!”
实际上是:“机助我矣!”
将二者合起来,就是“天机”。
“天机不可泄露”,也不可多得。
谁得了“天机”,谁就得了“天下”。
索罗斯就是这样一位靠“天机”而得“天下”的异端人物。他的最终目的是想营造一个金融帝国的一代王朝,成为一个普度芸芸众生的如来佛祖。
(三)
索氏在他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说:“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存有相当强烈的救世主的幻想。”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把自己想象成某种上帝,或者是像凯恩斯那样的经济改革家,或者更好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我对现实有十足的认识,所以知道那样的期望太过分了,因此像犯罪一样把我的这一念头藏在心底。
在我成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相当不快乐的一个源头。但当踏进这个世界后,现实和我的幻想拉得很近,又使我敢于承认自己的秘密,至少对自己坦承。不用说,这使我快乐许多。
由此可见,索氏从骨子里就想当一个开明而开放的政治家。他说:
当你觉得自己是上帝,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的时候,那是一种病。但因为我熬了过来,所以又觉得很自在。
是我的成功使我重拾起儿时无所不能的幻想。
幻想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索氏便想将这笔财富投放到一种“开放”
的社会之中。这是他从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写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受到的启迪。他说:“我同意他的观念,也就是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了解本质上是不完整的。这种本质上的不完整,我归因于我们只是世界的一部分。”
索氏在他的《意识的负担》一书里也说过,人不一定更注重拥有物质,而不重视拥有精神、艺术和道德的价值,但所有的价值都可以简化为货币条件。他相信市场机能的原则可以延伸至极为广泛的领域,如艺术、政治、社会生活、性和宗教。
经济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索罗斯十分清楚,经济家虽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拥有呼风唤雨、操纵一切的大权,但却可以通过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实现政治的目的。
他想以货币为条件,以市场机制为原则,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建构起一座彩虹桥,然后实现他拯救全人类的理想。
因此,索氏拼命赚钱,而且已赚了许多许多的钱。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他上了《福布斯》的全球富豪榜。在全球400个富豪中,他名列第27位,拥有35亿美元。
他说:“当我的成就不容置疑之后”,他就“必须开始享受、利用这些成果”了。他说:“就算毁了能生金子的鹅,也在所不惜。”
其实,他早在1979年就创立了他的第一个“基金会”。迄今为止,他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里设立了50多个基金会,雇员有1500余人。
他说:
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
索氏将自己的“情妇”,慷慨地送到世界各个地方,与政治家打得火热。资料显示: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便以每年捐助300万美元的规模,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而索氏选用担任该基金会的总裁瓦萨赫利,正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人物。
80年代后期,索氏用1亿美元建立了国际科学基金会来向俄罗斯科学家提供帮助,使3万多科学家每人拿到500美元的救助。1996年,他又为俄罗斯捐助了约580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之中,他向10个东欧及中欧国家一共捐赠了1.5亿美元的援助。他对匈牙利等3个国家的资助,竟超过了美国政府对那些国家的援助。
富豪们拼命积累财富的目的,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光宗耀祖,改变家族的命运,借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人生境界。
一种是不仅想改变自己个人的命运,也不满足于自我实现的人生快乐,而且更想改变他人的命运,使天下人人都生活快乐。也就是说他想改变当今“不完整”的现实世界,而重塑一个新的世界。一句话,他要改写历史,真的要把地球举起来。
显而易见,索罗斯是属于后者。
他说他建立基金会的唯一目的不是别的,而是比基金会本身更为重要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比现在开放社会还更为“开放的社会”。
他说: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自然包括美国在内)正濒临崩溃(《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15日)。
即使像美国这样开放的国家也很不理想,到处都是吸毒、犯罪。为此,他花了100万美元来救助吸毒者,还准备在5年之内为一个毒品政策研究小组提供1500万美元的经费;其他还用2500万美元来资助一个“死亡研究”中心,又用5000万美元来帮助移民能够获得美国国籍……
但作为犹太人的索罗斯,对以色列却从未提供过任何援助。他说要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要花得更有意义。他也建立了慈善基金会,但不是去救援自己的亲人和民族,也不是随便去救一些“穷人”,而是首先花在有利于开创“开放社会”的那些方面。即使是搞些慈善活动,也只不过是将此作为一个平台而取得话语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一个超民族、超国籍和超自我的全球领袖,就像拯救世人的上帝一样,这就是他——索罗斯。
他自己是这样看,其他许多人也如此看,正如西欧一位高官说的:“索罗斯是阿尔卑斯山脉以东未经选举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即使是曾经吃过索罗斯苦头的英国人也认为:“索罗斯真行,如果他因为我们的政府的愚蠢而赚了10亿美元,那他一定很聪明能干。”更有不少的英国人,称他是“传奇中的英雄”。
从某种意义上看,索罗斯的确不是金融家,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家,一个近乎于传奇中的英雄——一代天之骄子。
然而,政治家们似乎都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更有人恨之入骨,百般辱骂他。
(四)
20世纪80年代后期,索罗斯想与美国总统布什谈一谈应对苏联的新策略,但布什对他不置可否。索氏想见一见戈尔巴乔夫,也未能如愿。
不久,索氏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商讨一项援助苏联的计划,也迟迟不能实现。直到对方下台之后,这位“铁娘子”才与索氏打来电话,说了声“稍锐”(对不起)。
这还算是客气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不如此客气了。他骂索罗斯是“疯子”,是“罪犯”,咒他“不得好死”,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马来西亚人竟在广场上焚烧了他的模拟像,尽情地发泄对他的愤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平息之后,不论是胜者还是败者,都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向世人作个交待。
索罗斯向世人坦承交待说:
我被马哈蒂尔谴责为万恶不赦的坏人,他把我当做替罪羊以掩饰个人的失败,他在欺骗本国的民众。马哈蒂尔选中我的原因是他需要一只替罪羊,而我正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也有其他的一些缘故,他提供了某一类观点,亚洲的重要性,与我所支持的开放社会相矛盾。我能看到这其中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在索罗斯潜意识的理念中,也许含有正如马哈蒂尔说的那些因素,即“西方国家现在企图利用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新殖民化政策,以便重新奴役我们”;他们“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就进行了不道德的破坏。”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也失之偏颇。
索氏认为东亚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的惨败,“各国政府要对此负责”。意思是罪不在我,而在你们自身。我非旦无罪,而且有功。不是想奴役你们,而是想解救你们。
明人不做暗事。索罗斯事前就曾多次发出警告,一再向世人提醒。
他说:
吟市场中留有投机的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
吟市场不能留下被校正的错误。
吟市场上没有均衡这样的事情。
吟不能相信现在的繁荣不会紧随破灭。
吟市场的不稳定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混乱。
吟在兴盛时期,资本从中心流向外围,但当信心下跌时,就具有从外围回流的倾向。
吟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它的特征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除此之外,还有思想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吟我只能一再对盲目信任市场的魔力发出警告。
既然提醒无用,警告无效,那就用事实来证明谁对谁错。获胜者索罗斯指点江山,无非是向世人表白,他这次横扫东南亚,是要给东亚人一点教训,别再干蠢事了。这次损失全当是你们交的学费吧。这不是什么“奴役”,也不是什么“不道德的破坏”,而是一种“帮助”。
若用某种价值观来衡量的话,那这无疑是一种强盗逻辑,是一种“不道德的破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