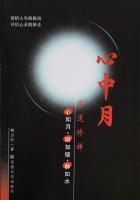但若用禅师们的理念来看,似乎又另当别论了。有个病人向一位名叫曹山的禅师求医,他说我浑身是病,求大师医治。
曹山禅师说:“不为你治病。”
病人说:“为什么?”
曹山禅师说:“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病人说:“你不是常说大慈大悲吗?”
曹山禅师说:“我这样做,正是大慈大悲。”
禅师们都是一些不讲逻辑、不讲理性的“疯子”,说的都是一些“疯话”,世俗之人是很难参悟的。然而,一旦参透之后,你才明白他们往往是不医则是为了更好的医,不情是为了更大的情,不德是为了更高的德。这叫杀中有救,救中有杀。
也许索罗斯根本就不会也不屑于参禅悟道,但在冥冥中他似乎又深谙此“道”。
索氏横扫东南亚,显然与当年日本侵占东南亚是为了“帮助”东南亚建立“共荣圈”的目的与手段不太相同。
索氏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建立“开放社会”的政治目的,尽管他知道这与他向往的“开放社会相矛盾”,也从中看到“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他还是掀起了这场金融风暴。而且从中大捞了一把,获利多多。但也正像当年他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捞了12.5英磅一样,他“没有一丝良心上的苛责”,也不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因为,索氏始终将自己看成是对人类富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超级领袖。正如怀有“悲壮的人文理想”的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同索氏一样,都认为当今的世界是“不完美”的,都认为“封闭社会”不好,应当全面“开放”。因此他以他的“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的理念和权力魔杖,率先对苏联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然后又推向国外。他不仅要把苏联这只“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而且也要为“全人类利益”而努力奋斗。他还提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自己的幸福不能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全人类的利益,应当高于一切。他为此而努力的结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最终苏联解体了,他自己也被时代无情地抛弃了。当香港凤凰台的记者去采访他时,看到这位曾经权倾四野,指点江山的风云人物,而今却成为一个被历史尘埃封存了的“匆匆过客”。这只曾为万人景仰的金凤凰,而今已成为一只脱尽金毛的落汤鸡。
唐代诗人,也是最大的孤独者陈子昂曾慨叹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戈氏也像当年中国的陈子昂一样,见有人居然还来采访他,一时怆然泪下。他说别人都把我忘了,连电话都不打一个,你们倒找上门来了。
记者问他,你后悔了吗?
戈氏说“不”,从他眼里突然射出一股冷光。他说那时我对病入膏肓的社会痼症开刀问斩,敢于对“特权者”下手,这本身并没有错,我一点也不后悔。
这也正是中国禅师们说的:杀中有救,救中有杀。杀一魔障,救一梵天。
就此而言,戈氏也许正是一位空前绝后的人文主义者,一位难能可贵的思想家。
因此,索罗斯对戈氏佩服得五体投地,巴巴地渴望能与他见上一面。因为他们神交久也,双方的心灵是相通的。只是缘悭一面,终归未能如愿以偿。
如今戈尔巴乔夫已成了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但索罗斯的金融帝国却还稳如泰山,仍旧迎风屹立。而且,现在他的“基金会”的触须又伸向了东亚诸国,还伸向了神州大地,已在海南岛登陆。
如此说来,是否就认定戈尔巴乔夫是失败者、索罗斯是成功者呢?
倒不完全是这样的。
戈氏的失败,错不在他的理想。时至今日,不论怎样看,他的那些理想都是美好的,依然是人们永远都值得去追求而努力实践的。但理想并不等于现实,现实也不等于理想。值得人们努力实践的既不是美好的理想,也不是不完美的现实,而唯一可行的是要找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那个神秘“支点”、“契机”。只有这样,才能撬动地球,把地球举起来。
戈氏的最大失败,就是他还没有选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那个“支点”、“契机”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按动了杠杆。结果是非但没有撬动地球,反而被地球打翻在地,永无出头之日了。
因此,戈氏不是一个成熟而成功的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出色的思想家,一个值得人们怀念的悲壮英雄。
索罗斯呢,看去现在还没有丢盔卸甲,但他的理想,也同样不能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因为,尽管索氏还没有具体地描绘出他理想中的“开放世界”的蓝图美景,但看样子和戈氏描绘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开放社会”
也差不了多少。
事实上,这样的理想蓝图,早就有人提出了。中国晋代的陶渊明描绘的“桃花园”,可以说是这种蓝图美景的雏形。佛家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和道家描绘的“仙山琼阁”,也大抵如此。
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描绘的“五层人格金字塔”,大体上也是“开放社会”的缩影。但这些都只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已,是实现不了的。
实际上,戈氏也好,索氏也好,他们向人们抛出的只是一个参不透的“悖论”、打不破的“禅关”,一个连他们自己也找不到答案的“难题”。
他们的可爱与可敬之处,就在于许多人都只满足于现状而无心去过问的情况下,他们敢于去尝试、实践。而且也悟到了天下禅机的不少诀窍,为他人提供了难得的经验教训。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这正是一种佛家似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人们说戈氏索氏是傻子、疯子、狂人。
其实,他们都是很正常的人,都是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勇者。如果要说他们是狂人的话,那也是一个最清醒、最理智的狂人,但绝不是没有头脑的傻瓜、笨蛋。
索罗斯并不糊涂,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单靠“思想”和“经济”的推动是不行的,还必须借助“政治”的权杖才行。所以他一直都想方设法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以及其他有影响的政治明星联手合作,共同打造出一个比现在更加开放的“社会”。
戈尔巴乔夫也不糊涂,他比索罗斯更有条件和实力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他已拥有一国之富和呼风唤雨、点豆成兵的政治魔杖。
他更懂得利用手中的这根超级魔杖来创造自己和人类的历史。
然而,戈尔巴乔夫偏偏陷进了“滑铁卢”,最后以无可挽回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索罗斯虽然还在硬挺着,但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这并不是他们缺乏才能智慧和发疯发狂,而是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的: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戈氏与索氏恰好就输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关口上,他们忽略了自己所处的险象环生、陷阱密布的“生态环境”,不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生存情结”,而一味地仅凭自己选定的条件而随心所欲地进行“创造”。结果自然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非但没有“成龙上天”,反而“成蛇钻草”,变成一条“大鳄鱼”。
不过,苏格拉底说过:
让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首先改变自己吧。
索罗斯一心想要改变现有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尽管未必能通过自己的金钱来换取一个他理想的世界,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不断挑战自我,与自己较劲,与现有的秩序较劲,企图做一个现代文明的颠覆者。尽管他追求的那个世界未必就是人们理想的世界,他自己也感到有些“测不准”,更感到希望有些渺茫,但他仍然执着地去追求,非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改变世界不可。
就此而言,索罗斯仍不失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江湖好汉,一条可爱的大鳄鱼。
故不妨以雪窦禅师一偈作为评参:
一拽石,二搬土,发机须是千钧弩。
象骨老师曾辊球,怎似禾山解打鼓。
报君知,莫莽卤,甜者甜兮苦者苦。
最后要说的是,索戈二位虽然失败和失机了,但李光耀在区区禅丸之地的新加坡,却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并获得了最大的突破与成功。
请看李光耀创建的“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创建“新加坡模式”的“三三”之谜
救一个不如救一群。李光耀想创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他终于成功了。
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他找到了平衡“一党制”、“一言堂”和“一把抓”的“支点”,所以把新加坡这个小“地球”举起来了。
家家有路透长安,条条大路通罗马。
诠释了李光耀就诠释了新加坡这个新型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尽管李光耀开创的这个新型模式从开始到现在还不到半个世纪,人们对李光耀及其创建的新加坡模式的评价也还褒贬不一,但正像李光耀本人的名字一样,他依然是一个璀璨夺目、光耀环宇的“政治明星”。尽管他已不再担任新加坡的总理而成了内阁资政,但他依然是新加坡万人景仰的“国父”和媒体追踪的神秘“焦点”。
李氏操盘的“一党制”、“一言堂”和“一把抓”,在东方的许多国家为此掌控多年都以失败而纷纷解体,或者难见成效,不得不改弦易辙。
但李光耀为什么又将此玩得炉火纯青、大放光彩呢?
(一)
新加坡曾一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他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从1946至1950年,他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留学四年之久。
他还为自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哈瑞”。因此,英国人称他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他自己也坦承地说,我的确从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法制精神、社会主义理想和自由市场制度等,更使他受益良多。然而,他又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是一个钟情于儒家思想、富有亚洲价值观的炎黄子孙。
有位资深撰稿人问他:对你性格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开始才确立你的人生志向,并最终决定走上政坛大展宏图的?
李光耀说:
母亲一生都致力于抚养子女,让我们接受良好教育。日本入侵所带来的惨痛经历,也锤炼了我这一代人。我们看到了日军是何等暴虐无道,只要你还有自尊,必定会很有感触,觉得日后一定要挺身做些什么,再也不依靠英国人或其他人。(《海外星云》2002年3月上旬号,下同)
李氏究竟想这一生应当“做些什么”呢?
他说:“我以前曾和太太、弟弟一同从事法律工作。我想,我们原本可以发展成大型法律事务所,生意兴隆,我可以赚很多钱。”
但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一下便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他说:
从1946~1950年我在英国留学4年,我的政治理念就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英国曾饱受轰炸,当时满目疮痍,却仍透出一种傲气,人人克己奉公,礼数周到。
我第一次走出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地下火车站时,看到有张矮桌子上摆放着各种报纸和一个硬币盒,旁边无人看守。你要买报纸,只须取起一份你想要的,再放下硬币就行了。我当时的惊讶,至今仍然记得。我深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这是个文明的民族!”那是200年来治国有方、管理良好所致。
从事法律工作,当一名律师,虽然也是一种很不错的行当,而且还可赚很多的钱。但这种仅为个体和少数人化解纠纷,伸张正义的工作,比起拯救和造就一个民族的文明来,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正如李光耀说的:“这样一来,又有谁来为新加坡创造机会发展呢?”
记得有个叫马祖的中国禅师,有一天他碰到一个猎人正在追杀一只梅花鹿。马祖忙拦住他说:“你一箭能射几只鹿?”
猎人说:“我一箭能百发百中地射中一只鹿。”
马祖说:“那你还不是一个打猎的高手。”
猎人说:“请问大师,你能射多少呢?”
马祖说:“我一箭至少能射中两只,这叫一箭双雕。射一个不如射一双……”说着,一下夺过猎人手中的弓箭,直端端地对准猎人。
猎人大惊失色,忙说:“大师,你怎么射我呢?这样的话,我就不能活了,会死的。”
马祖说:“你怕死求生,那鹿呢?你爱惜生命,难道鹿就活该死在你的箭下不成?“一语点醒了猎人,他不禁翻然大悟,忙拜倒在马祖的脚下,表示从此皈依佛门。马祖身边的弟子说:“师父,你又救了一个。”马祖说:
射一只不如射一双,救一个不如救一群。
我虽然不能断定李光耀是否参禅礼佛,但却可以断定他的人生远大志向,不是为个别少数人谋求幸福,而是正如他自己说的:
我曾希望建立一个多种族的马来西亚……也就是说,想建立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多民族的国家,这才是他的政治理想。李光耀常说: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而最能发挥他的潜能、最适合他扮演的角色的,不是什么小小的律师,而是大大的国家元首。也就是说,李氏终于找到了他的人生轨迹中那个能撬动地球的“支点”,他终于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他说:
我的战略是在一个第三世界地区创造一个第一世界的绿洲。新加坡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比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更强大、更有组织性、更有效率。如果我们和我们的邻国一样好,那就没有理由把生意都吸引到这里来。(《参考消息》)
但有了“支点”并不等于就能撬动“地球”。有了“战略”并不等于就能实现自己的意图。
当40多年前李氏找到了这个支点、战略的时候,实际上新加坡并不存在,还是一个空中楼阁。当时,它还只不过是隶属于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小岛。李光耀说,他想建立的“也许是不会有的新加坡。1965年我们是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独立的,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可以生存”。
因为这个区区弹丸之地的小岛,无腹地,无心脏,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出口原材料,农业上要依赖进口,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320美元,政府形同虚设,要什么没什么,有的只是贫困。
但只要找到了“战略决策”和“支点”,就可以走上正轨,把理想变成现实,就可以将“丑小鸭”变成“金凤凰”。如今的新加坡,正像一位西方记者描绘的:
街上没有纸屑,甚至在拐角处有秩序地等待过马路的几百人中也是找不到哪怕一个小小的烟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人们都在说英语,没有乞丐,连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看不到。欧洲人和亚洲人、印度人和穆斯林都毫无芥蒂地生活在一起。着名的奥查德大街上汇集着全球最豪华的商店和最高级的品牌,新加坡人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到这里购物。
在千变万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多元化民族希望建设与众不同的国家的决心。这个决心到现在为止是成功的,在选择了这条道路40多年后的今天,新加坡人在收获,他们创造了一个奇迹。但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变革自身的历史,它要作出艰难的、有时是充满争议的政策,唯一的目标是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最适合居住、没有冲突的地方。凭借开放的经济、世界第三大港口、可与世界最佳相媲美的金融中心、在亚洲仅次于文莱和日本的高生活品质以及一个有力有效的政府,新加坡已经成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毫无疑问,李光耀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那么,他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二)
李光耀及其新加坡的成功之路,看起来复杂而难解,但说起来却非常简单明白,无非是如禅师们说的“前三三后三三”。
有学人问志勤禅师:“这是什么意思?”
志勤禅师说:“水中鱼,空中鸟。”
学人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