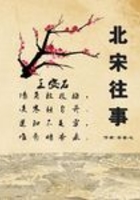俗家僧兵本来力量就超过普通人一倍以上,加上坚持训练,按月发粮,集结时三餐供应充足,还时不时有打来的猎物补充油水,所以,在寒冬的河里游到汽船那里,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三个斥候加上韩青,一问之下四个人有点傻眼,韩青会游水,三个斥候里只有一个会那么点狗刨,另外两个直接是旱鸭子,上午过河还是踩着木板绑成的筏子,战战兢兢过来的。
可以拆卸的爬犁,不但能当帐篷的骨架,过河也能利用上,要么说汉人的工匠手艺,那是没的说,就看能不能被发现了。
从岸边算起,这距离汽船不到三十米的距离,简直成了一个大坑了,韩青就是这么认为的,王队官根本就不想给他手枪。
“呼呼、呼,”河边的寒风愈加凄厉,扫在脸上犹如刀刮,如果再晚点,哪怕是身强体壮的僧兵,估计下到河里很快就冻僵了,用不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贸然行事不但会白死人,惊跑了汽船,那就白费劲了,对于韩青想一个人上船的主意,三个青壮僧兵果断地拒绝了,看神色他胆敢妄动,立马就会被绑起来。
躲在灌木从里,四个人商量无果,只能走两个去找王猛,汇报老毛子的情况,谁也想不到,老毛子的船过夜也不靠岸。
另外两个斥候带着韩青,监视着河上的动静。
一个小时后,王猛带着人马回到了河岸边的矮树林里,天色彻底黑了下来。几个蒙着白布的手电,小心地亮起来,光线背对着河道,僧兵们将爬犁再次拆开,组合成了一个双层的宽大筏子,趁着暮色抬到了河边。
“韩小子,来来,说说情况,”王猛拉着韩青,把他带走了,接下来的事情,已经不是韩青能接触的了,他的年纪太小。
早有斥候将看到的俄国人船上的动静,报给了他,汽船上应该有不少于十个持枪老毛子,加上木船里的人,总共不会超过二十个,里面没有看到穿俄军军服的士兵,这让王猛轻松了不少。
那三个木船上,斥候只看到了不多的人影,估计每条船上,至多有三四个人。
河岸边,十几个人忙着将筏子推进了河里,岸边一米多宽的薄冰,咔吧几声碎响,七人先后爬上去筏子,操起手里的长杆,顶着筏子往木船方向飘去,其他人拉着长长的绳子,守候在岸边。
筏子上系了绳索,为的是以防万一,还能把筏子给拉回来,但是真要有事的话,上面的人就危险了;夜里掉进河里的人,能生还的几率绝对不到一半。
刘二柱带着六个身手最好的斥候,每人带着刺刀、尖刀,腰里插着一把手枪,怀里还有一皮袋的烈酒,脱去了臃肿的皮袄大衣、厚皮裤,脚上的长皮靴子脱掉了。
幸好冬季河水水位低,三米多长的木杆,插到河底正好能推着筏子维持方向,缓缓向下游飘去的筏子,一点一点地接近了大木船。
三艘大木船首尾相连,最靠近汽船的,也通过缆绳,和汽船保持着十来米的距离,加上木船上的人不多,刘二柱他们当然先捡软柿子捏;最起码,抢了三艘木船也是好事啊。
筏子靠近了大木船,在距离汽船最远的木船旁,刘二柱他们爬上了船甲板,一个僧兵打开手电,冲着岸边晃动了一圈后,灭掉了灯光。
河岸边,等待的十来个僧兵,齐齐动手,将那个筏子拉了回来,防止以后被俄国人找到,顺藤摸瓜追到牛头寨就糟了。
黑漆漆的甲板上,弥漫着淡淡的鱼腥味,船舱舱门的缝隙里,露出丝丝晕黄的光线,正好照在刘二柱的身上。
一挥手,两个斥候从左右两侧摸了上去,防止从船两边的窄舷道上有人过来,剩下的四个人里,两人殿后拿出了手枪,两人来到了舱门外。
拿出锋利的刺刀,刘二柱顺着门缝插进去,慢慢去找阻拦的门栓,“哗,”舱门突然打开了。
一个络腮胡满嘴酒气的老毛子,和刘二柱脸对脸地愣了一下,嘴里还没来得及叫喊出来,刘二柱的刺刀,咔,凶狠地插进了他的大嘴里。
“咔,”刀尖从老毛子的脑后冒了出来,满脸诧异的俄国人,眼神猛然黯淡下去,身子僵硬。
柱子的手劲很大,刺刀直接就扎透了老毛子的后脑,毁掉了他的脑神经。
推着老毛子倒退,两人踉跄进了船舱,夹杂着酒味、汗臭味的浑浊空气,扑面而来,差点就让刘二柱给吐了。
借着舱内蜡烛的灯光,他一眼就看见里面的吊床上,还躺着一个呼呼大睡的家伙,盖着厚厚的毯子,手里还拿着一个闪亮的酒壶,滴滴答答的酒水,掉落在舱底。
空荡荡的船舱里,阴冷潮湿,比外面仅仅暖和一些,舱壁上挂着两杆步枪,还有子弹带、带鞘的刺刀,两个布袋子,里面估计装的是干粮。
“扑通,”把已经没了动静的老毛子扔到一边,顺势拔出刺刀,刘二柱对这种细长的刺刀很是不屑,容易断裂,唯一的优势就是比尖刀长罢了,刀口容易刺入而已。
不过,没有放血槽的刺刀,很容易被夹死在肌肉中,力气不大的人不好拔出来,更别说在肌肉中翻转搅动了。
来到这个醉汉跟前,柱子在同伴佩服的眼神下,将刺刀横咬在嘴上,上去按住了老毛子的脑袋,“喀嚓”,给调转了大方向,扭断了他的脖子,就像杀鸡时的手法。
刘二柱的枪法一般,在山林里寻找猎物的手段也是一般,辨识药材的手段还不如其他的斥候,他要想在斥候队里强出头,只能比别人更大胆更卖力。
他必须这么做,要用最狠辣的手段,告诉其他人,自己不是凭着妹妹的关系,才当上的这个斥候军校官。
吊床上的老毛子,很快不再抽搐了,一股子尿屎位弥漫开来,两个跟在后面的斥候,赶忙把脸扭了过去,只有刘二柱不动声色地拿出手电。
手电光亮,在船舱里看了看,他没找到其他的战利品,只能先带人走出后舱门,开始向前面的木船摸去。
木船之间几乎是船挨船,不用费力他们就摸到了第二艘船上。
第二艘、第三艘,刘二柱越来越老道的杀人手法,身上却是没有粘上几滴血渍,让斥候们不得不暗暗竖起大拇指,看向他的目光里,浮现出一丝丝的敬重。
越是实力强大的人,士兵们才会越佩服,跟着干也踏实,起码活命的机会就大了很多。
顺着粗大的缆绳,六个斥候终于爬上了汽船的甲板,“彭,”突然出现在船头的俄国人,走到船舷边还没脱下裤子撒尿,被刘二柱一枪打倒,惨叫着一头栽进了河里。
“上”,刘二柱大声喝道,其他几个斥候同时举枪,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枪口对着前方,沿着船两侧的通道,冲进了驾驶舱和侧面的舱室铁门。
“彭彭、彭彭,”左轮手枪沉闷的射击声,在河面上响起,清晰地传到了王猛的耳朵里。
啪啪,岸边上三个手电筒,同时点亮,直直照向了汽船,手持步枪的僧兵们,在岸边枪口齐举,虎视眈眈地盯着船上的动静。
只要有人再出现在甲板上,僧兵们见影子就会马上开火,无差别地射击,这是王猛和刘二柱说好的。
和大木船上的船员不同,汽船上的俄国人很是彪悍,面对冲进来的斥候们,哪怕是醉酒熏熏的人,也毫不犹豫地拿着任何能摸到的武器,长刀、木凳、酒瓶甚至餐刀,与僧兵们疯狂地搏斗起来。
“彭彭、彭彭,”两个军官模样的老毛子,举着手枪和僧兵们近距离对射,硝烟中选择了同归于尽。
几个试图逃跑的老毛子,刚刚跑到甲板上,河岸边顿时一阵排枪,将他们打翻在船上,也有身影掉入河水中,噗通溅起水花就没了踪影。
当两个浑身油污的船员,被从船尾机器舱里逼出来时,汽船上的枪声停了,六个前来夺船的斥候,死亡两个,受伤四个,刘二柱的左耳朵被子弹打掉了一半。
要是子弹再偏那么一点点,他就成了第三个死亡的斥候。
几乎没有夺船经验,甚至是第一次登上汽船的斥候们,凭着勇气和血性,生生完成了任务。
汽船上,驾驶室里有人,透过溅血的玻璃,用手电光对着岸边晃了几圈后,守在岸边被冻得浑身僵硬的王猛,终于长吐了口雾气。
汽船上携带的小船,在岸边人们的低低欢呼声中,划向岸边,船头上挺身站着刘二柱,光线下憨厚的脸上带着笑意。
他身后划船的,只有两个斥候,一人手臂上包扎的带子上,殷红显眼。
脑袋上包着一圈布带的刘二柱,站在了王猛面前,身上还带着淡淡的硝烟味,“报告队官,斥候队夺船完成,老毛子抓了两个,其他全部干掉了,伤亡六人,缴令,”
去夺船的七个斥候,死了四个,囫囵回来的,只有一个殿后的,他和另一个同伴伤势不轻,老毛子火拼太玩命了。
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熟悉汽船上的环境,被老毛子反偷袭得手就死了两个。
“去休息吧,弟兄们辛苦了,伤者包裹伤口上船,死者放到后面木船上,咱们要带他们回去,”
“是,”
很快,一艘大木船收了石锚,在韩青大呼小叫声中,僧兵们拉绳子的拉绳子,撑杆的撑杆,拉推着木船好容易到了岸边,开始装运爬犁和帐篷物资,这时候,王猛才发觉,韩青的作用真是太大了。
木船靠岸都要找好地方,装运物资也不能太多,搁浅了一晚上都不得休息了。
没有韩青的指点,这些船就白瞎了,没人玩的转。
就这样,还是有一个僧兵不慎落水,韩青跳下去给拽住了,大家伙扔绳子、递长杆,总算给活着弄上来了。
汽船上抓的两个机器工人,幸亏没有给干掉,要不然汽船也成了一团废铁,其他的几个水手和船长没那么幸运,死在了夺船的厮杀里。可惜了。
牛二转交给王猛的小瓷瓶,王猛小心地拿出来,倒了两粒淡红色的丹药出来。
举手跪在他面前的两个老毛子,有斥候上去,一巴掌拍开了嘴巴,强令着把丹药吞服下去。
有枪口的威胁,肩膀又被狠狠地按着,两个老毛子想要活命,只能无奈地张大了嘴巴,挨了几下重击,不懂汉语也知道要张嘴了。强壮的清国人?凶神恶煞的清国人?他俩已经蒙了。
这还是自己认知中的清国人吗?
远在石头屯里的泽正,刚刚睡下,突然睁大了眼睛,漆黑的石屋里,响起他淡淡的笑声,“呵呵,”
“王猛那里,大概是有收获了,”
耳畔丝竹声悦耳,良久不断,不用说,自己获得的功德相当不菲。
脚后睡着的小曼,梦呓了一声,裹紧了身上的棉被。
有了好心情,泽正干脆起身穿衣,顾不上忙碌一天带来的疲惫,钻进了石壁上的七彩光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