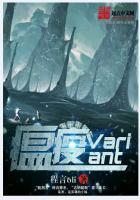徐夫子说实在的确实是一个古板的人,认识他的人都把它比作石块,又臭又硬的那种。但是他绝不是蠢货,他知道自己的古板不讨喜,所以他也不强求什么声名,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讲讲历史考考学生也是不错的。
他最初对这所学院的印象并不好,或者说对整个下城区的印象不好。封闭,落后,野蛮,混乱,尽管本着历史学者一贯的客观精神不能过早、主观地下结论,也知晓其中水分很大,但他的最初印象确实如此。
他大概是少有的主动申请留任的教员了。
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许在回忆过去,然后等待某一天某个无名的人传来久违的密令吧。
世盟援助中心学院,简称世中院,下城区最庞大也是最先进的学院,采用着一种独立而封闭的教学系统办法。实际聚集了下城区最精英的一批人才,而每年有下城区外的学院精英作为“交流生”前来这里并近年渐成惯例,某种程度这所怪异的学院是下城区与下城区外域精英共同的聚集地——当然你要有钱或者权,它绝非慈善机构或者社会义务福利机构。
没办法,南境没有义务教育法案。这是一片荒蛮、苦难的土地,这个远离大陆的星球同样如此。
徐夫子喜欢这里还说不上,但毫无疑问下城区尤其是世中院的学生许多都很特别,吸引了他。尽管下城区出去的旧世代的人难免遭受歧视,但还是有无数人期望在这里通过努力走出下城区。他们不乏天分,或许后天培养不足,资源缺乏,但他们更有活力与拼搏的勇气。
他见过有人走出去融入外界,也见过有人默默无闻消失在这世盟的浩瀚疆土。
干了十几年,徐夫子实际上也少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了,一个不揽权的研究员想想也没什么波澜的生活。
但是他今天很恼火,也心有隐忧。世中院他早就知道背后的成分很复杂,毕竟稍稍用脑子想一下也知道能安排与白塔翰林学院等一批精英学院派遣交流生、建立新旧世代混合教学制度的学院肯定不简单。
他听说了许多最近不好的流言,而世盟边土似乎又生了变乱,四大镇守府的隐患世人皆知,十几年前那位凤凰横空出世,盖压四方,如今当年的黑手们又蠢蠢欲动了,今天居然受到了世盟安全调查局一上午的审查盘问。
安查局的猎犬简直令他厌恶至极。当年的往事袭上心头更是令他怒火飞腾,要不是这些年养气功夫,估计早就一言不合打上去了!
“一群鹰犬!”
他自然没真正和这些猎犬翻脸,但好脸色肯定没有的,他怎么说也是挂在联产科协下的人,安查局也管不了这么长。
徐夫子怀着这份糟糕的心情上着近代史的课,最前排绝色夺目的夏洛特,然后就是那些“公主”的追求者们,来到这里的自然没有无能之辈,可是能让他记住留有印象的却也不多。比如,沃顿家的小子,可惜今天似乎请假没来。
“在天萝星区一场少有人知的战役同年发生,那位同学能够回答一下?”
他看着或低头或皱眉,陷入思考的台下学生,眼皮微微垂下来了,更给人一份阴郁与严肃的感觉。其实徐夫子倒也并非真的生什么气,他自己是自知的,有的问题不是钻研这一行有所心得的绝对难以答上来。他一则是心情糟糕,另一则是过去的黑色工作习惯使然。
他见到夏洛特和另几个科目顶尖的家伙都苦思不得,就准备自己接过话题继续讲下去了。
可有一阵乱糟糟的响动从后排位置掀了起来,就像一串普普通通的石子坠落静湖。
下城区已近黄昏的阳光沿着阶梯洒下,褐色而显庄重的窗帘微微摇曳,瘦弱的大男孩正将桌上书本收入书包。一个样式不算新潮的斜跨包。坐在最靠后的一排,徐夫子大致就明白了这个没有什么印象的学生的定位。
他皱了眉头,本就有些额头纹,这回更是两眉毛锁了一块儿。他心底又窜上来一团火气。像近代史之类的自选课程某种程度上是允许中途有事离场的,顶级的精英许多都会申请免修,而有些不是致力在此的学生更是常常报到后中途悄悄离场,毕竟只是来那个“全勤”的学分。
徐夫子心底冷笑,看着少年有些颓废的样子,打定给他个教训,要怪就怪他撞枪口上了吧。他不动声色地视线落在了刚刚起身的陆小释身上,点道:“站起的那位同学,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很自信嘛!”
——————
陆小释这会儿才刚刚回神,眼睛游离了一下,对上了徐夫子如炬的目光。他知道自己倒霉了,早退什么的在这种客座的课程上实在太正常了——曾今听说过有人不幸被人从这方面挑毛病,他还幸灾乐祸过。
因果报应?
他没有慌张失措。人百分之八十的错误来自慌张,这是名将舒克也是他的信条。舒克,正是陆小释所推崇的一位名将。三榜第二榜玄外第十,一位武力登上地榜小宗师位的名将。
而且他的反应绝对是快的,远超常人的快——
这里面有来自于他的骇客生涯的锻炼,而其中更重要的是一种本能,后天锻炼的奇异本能——他曾一度怀疑老师收留他的原因是否于此。
后来,他自己就否定了。
绝不是这样。天赋卓绝之人世上不知凡几,而其中佼佼者也多有,他又算得了什么?
地窖图书馆他查过关于血脉的书籍资料,祖先在血统高贵或者祖先存在过不可思议的奇迹的家族会有近似的干涉现实、打破桎梏、天生权柄的超凡之能,称为“血脉天赋”。
他没有血统,作为旧世代,天生机械信息不亲和,血统低劣。
陆小释知道他是凡人,在人海中,刻意去记也未必会记得的那种。在他真正取得高人一等的力量之前,他自然没有资格去做任何僭越的行为。
“我不知道,我只想请个假。”
他微微低头,避过徐夫子的视线的烧灼。他有预感徐夫子的眼里包含着某种他无法理解的火气。但他不想说,不想辩解,心里一点涟漪都没有。
空落落的,死了灵魂似的。
陆小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状态始终不对劲。
徐夫子眼里和耳里所感受的却是这个不遵纪的家伙赤裸裸的嘲讽。请假是吧?哼哼。
“同学你是想当逃兵吗?学习可不是简单的天赋问题,这是态度决定的问题!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不意小过,终成大错!”徐夫子声音不高,却声调一下提高了起来,给人厚重如山的气势压迫,“我不歧视旧世代,但逃兵一样的旧世代,在我眼里简直就是对世中院资源的浪费,叫嚣着公平,乞讨者怜悯,却不承认自己的过失使得自己与出色之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想学生自治与检察会应该提交份报告书,表决劝退那些不思进取、甘作平庸的人,世盟的资源不是来浪费的!”
徐夫子越说越流畅,虽然开始时借题发挥、排解郁结,可这会儿切切实实是他想一吐为快的看不惯的事了。
他刚刚歇下一口气,准备继续,一个他预料外的声音发了出来。
“徐夫子,学者可不是那些钻营小人、拨弄是非政客。学者们遵循法则,仕子从于利益。您是想加罪于我,借题发挥,莫不是您要做张乖崖吗!何至于此?”
少年不卑不亢,神色平静地抬头,却是语出惊人,言辞如刀。
徐夫子的话一下卡在了半路,脸色由黑变白,又由白变红,最后变作一脸的铁青,只差没拍桌喝骂了。
张乖崖何许人?
酷吏、刻薄之人,曾以“一字之罪”诛杀当年翡翠王立学院上下院一百七十人,面对两府问责回复“一字有罪,日积月累,毁坏国祚”。
“夫子不见政,不妄动权力。您是否有违圣道?”
陆小释很犀利地再补一刀。
学者之中的规矩,理念之争、道统之争可争于庙堂之上,苍穹之顶,但是政客止于太学院的规矩,除了破门而出、重启格物的策士一门外,就再无例外。
学者、夫子、仕子、政客,是不同的。
在昙花一现的白银王朝之前,从政者多讲门第、师从,那时自治领遍布四方,“学而仕,仕而学”,学者、仕子不分;十七年乱战结束,擎天域网建立,令出中枢,学者托庇于门阀世家,不涉政权独立政权之外,寒门世家子弟俱以科考晋升,未入中枢皆为仕子,屡考不第而学问名于一方,脱离科考序列的即尊称为夫子,运筹庙堂、奉命于外的仕子之途顶点的人就是政客。
前排那些本来丝毫未投过注意力的人也有些看热闹转头来看。
“人总是要用各色的眼光和标准看待世界,我可以理解,而无论如何争辩,最终的真理皆是要在强大之上——”
“夫子,您的问题,诸位听,我来答。”
平静的言语在这个时刻无疑成了嚣张的表现,各色的目光中,陆小释毫不在意,徐夫子的脸上黑得似乎可以滴下墨来。
实用主义的争辩,终归要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陆小释轻轻吐气,忽然觉得实在是流年不利。
瘦弱的少年背着有些老旧的背包静静地抬头,目光很平静,没有微笑,也无愤恨之意。黄昏的阳光刚好抚过他头顶,给了他一点点有些单薄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