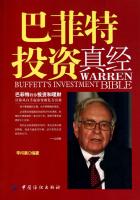日寇将他们认为的共产党员、八路军及其家属,和美貌俊秀的姑娘、媳妇,集中到这儿戏弄、抢奸,之后直至杀头,也有活埋的,放火烧死的,尸体扔在万人坑里,也有野兽吃掉的,霉烂的,扑鼻的血腥味久存不散。
此起彼伏的狼嚎鬼哭声把他惊傻了。他忙舍去大老犍钻进炮台里,从炮眼往外瞧去,闪着蓝光的鬼火,点点盏盏像似元宵节的灯光。借着鬼火的光,只见白色的骨架,灰色的碎骨如同小山。他真想从窄小的缝隙钻入地下。
静静的夜,淡灰色的月光洒在杀场上,显然是那么杀机腾腾。借光看得清楚,那些牛儿分伙卧了圆型防敌阵——凡大牛者一律头向外,犊子挨着妈妈卧在圈内。它们警惕地竖着耳,睁着眼,在防敌——凶兽。
一会儿那头大老犍站起来,走向另一边,嗅了嗅那黑色的血迹,拼命地吼了起来。八十多头牛刹那间都跑过来嗅着,号吼起来。
听老年人说,牛可嗅出牛血的味儿来——是它的本性。牛恨杀牛者,不一会儿它们飞快地原路原方向躲了去。
二日天刚亮,李宝和姑奶奶的邻居,多人寻找小枝和牛来。他们一见他守着牛儿吃草,就问起其因来。经他备细地说过,他们异口同声地唉叹了,流露了恻隐之心,说他是举世无双的受罪人,赞他是铁骨铮铮的小牧童。
太阳快压西山顶时,小枝放牧回来,姑奶奶说子祥找他来。真巧,说子祥,子祥推门进来。他说:“我等你够等急了。”小枝拉着他的手说:“听姑奶奶说你要我钉地鼠呢,我早给你说过,你要把钎头子磨锋利。越锋利越好。”
“都准备好了,俺妈说要你这会儿去钉,因为俺小小的山药苗苗被它吃掉大大一片。”小枝愉快地答应下来。他听奶奶说,地鼠是生在地下的小动物,它不出地外活动,与老鼠一样,是害人的小野生动物。它吃地下的果实,什么的山药、萝卜……它不但吃,还往去运哩,是万恶的地害,因此人们视其为大敌。小枝用锹挖了挖,可巧挖中了它的跑道。他把跑道铲断,做成尺来大的正方形坑子,把三根坚利的钎子从顶面,顺着鼠洞插下一截(不可钻入洞壁),露天多半,洞的两侧栽了一尺高的权架,架上横梁,板石系了绳,用短棍的一头把板石挑起来架在架上,另一头系在做好的土球上,把土球虚放在洞口内(要留通风口)地鼠跑出来要封口子,一撞,土球掉出坑内,系绳脱拴,板石就砸了下去,地鼠就被钉在地上。
二日天明,子祥和小枝跑来,一只大大的地鼠被铁钎子从它的背部钻入,从肚下穿出钻入地内,地鼠一命归天。子祥拿了死鼠,他俩咯咯笑着回了家。后来村里人们常请小枝去钉地鼠。子祥与小枝早交了朋友,他挽了小鞭子,常常跟着小枝上山玩耍,两人成了双双的牧童,也是灭地鼠的伙伴。牛官说,小枝虽是个娃娃,却成了灭地鼠的老手:草坡有多少,每日去那放,他都心里有数,做到有条不紊。
一日,天气突然要下雨,他把子祥送回村边。几个拉磨雷,倾盆大雨洒落了下来。牛的习性很怪,越是狂风暴雨,越要拼命顺风奔跑,大约是寻找遮风避雨的地方。
一会儿平地起水,山洪从四面八方围来,一经汇合,像似大海波涛,咆哮之声,震撼天际。小枝见一群滚瓜似的肥牛要闯洪过沟,眨眼,莫大的天灾——要赔牛。他不顾一切地扛着钢锚把那头领头牛刺回去,众多的牛跟着转回来,而安全无恙。但小枝却飘,飘,飘,被洪流飘了去——可巧,小枝命大有救,山洪把他飘上岸去。
雨过天晴,洪水没了,太阳出来了。表叔从家里跑来,见小枝被水飘上岸边,他摸了摸还活着,忙抱起两腿,让他头朝下吊着。嘴里、肚里、鼻窍里的水全流了出来,鼓鼓的肚子变瘪了,他出上了气——人生不过是一口气,只要有气,则还有活的希望。表叔给他脱去泥衣,洗去满身的泥巴。他昏昏迷迷地发出了问话:“表叔,牛死吗?”他用低沉的声音说。
“没有死,你放心吧。”他又昏过去了。但他一听说牛没被冲走,又闭上了眼儿。表叔给他铺了雨衣让他睡着。太阳像似为救他,是那么炽热。晒,晒,晒,直晒得脱了险,把他背回了家去。
也怪,老天跟坏脾气的人一样,干起坏事来没完没了。抬头太阳红,低头雨淋淋。蒙蒙小雨下着,下着,莜麦铃吊上了晶莹的水珠儿,银白色低头弯弯。
越是雨天,牛儿越不吃草,越要乱跑。不管吧,它要吃庄稼,管吧,一走,冰凉的露珠儿头上洒,身上滴,脚底流。他怎能不走呢?他那破烂的单衣紧贴着肉皮,一会儿变成了硬硬的冰片子。他呢,浑身哆嗦,牙齿也打起架来,真是揣不着,摸不住,料想不到的灾难又一次摆在他的面前了。
他想:“日寇没把我处死,这冷雨……”又想:“这这到底让我怎办?撵牛回吧,空着肚子的它们,别说鞭子打,用锥子也锥不回去。怎么办?怎么办……”他忽然想起费力可流汗,而流汗还冷吗?于是他围着庄稼地跑了起来,跑,跑,跑,直跑得气喘吁吁,浑身津出了汗水。他高兴而激动地叫起来,吼起来:“我又死里求了生!”山里发回了回话:“……”
“咯咯咯……”他笑了。谁知这笑声可笑晴了老天,笑掉了寒风。而此刻,风没了,雨停了。太阳从乌云里钻了出来。满山的白雾,一会儿聚扰,一会儿散去,一会儿徐徐腾空,一会儿滚滚向前。忽然,表叔又跑来了,雾天,雾地,什么也看不着。许多牛犊哞哞叫着看不见的牛妈妈,而牛妈妈也在哞哞地叫。表叔听着这些叫声和它们噌噌吃草的声音。就高声地吆喊“小枝——!小叶——……”
小枝答应了,表叔放心了。他笑嘻嘻地跑在他面前说:“表叔!牛没吃莜麦,我在莜麦地里看着哩!”表叔掉下两道儿泪,抓着了他的两只小手,呆着,呆着……
雾没了。红彤彤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牛儿懒懒地卧在那儿返嚼倒着沫儿。有钱的人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变,像蓓蕾要变花朵儿,是那么坦然自如。可是,小枝生活的转变,是重重而难以逾越的横沟。指天靠地的孤儿,只有河水可随便唱,野生野菜可随便吃,太阳也可随便晒。
太阳给他送温送暖,救了他的生命。他对太阳有着浓厚的感情,惟它是痛爱自己的慈母,是生命的支柱,也可以说是生命的源泉。他饿了,太阳以慈母般的笑脸,催他挖野菜,找野生去糊口渡日;他冷了,太阳早早出来笑着给他送温暖。
在寒冷,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里,当他被沙沙入骨的寒风审判之时,他总是一次次地昵着它,念念不忘地要它救救。太阳出来了,寒流没了——消失了,大地温暖了,小枝被释放了。他又兴高采烈地奔呀跳地干起来,唱起来:
太阳暖,
太阳红,
太阳救活俺没钱的人!
我要太阳永不落,
我要太阳日日红。
小枝小心谨慎,对他的红英枪不仅常磨砺,而且要学会保存利刃的方法——常用鞘套着刃头——无时不防敌——他有预感天智。今天他总觉得心里有所不安。突然喜鹊飞来喳喳地叫,是他的朋友。此刻,忽听叶子在前边号叫起来,越叫越响,越来越清晰,像是在眼前:“哥——呜——!”小枝拿着红英枪,向着叶子号吼的方向冲去。只见一只大而灰色的狼,拖着他,要钻狼窝。小枝箭似的冲上前去堵着窝门。那凶狼瞅见他人小,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它站在那儿逞出一派狰狞的凶象,拖着尾“叭叭”地摔起地面来。
小叶还被那狼紧紧地咬着,拖着,他一见小枝跑了过来,求救声更加清晰响亮,更加急切,更加沉痛。他拉长声音叫:“哥——我——”小枝呢?一手难捂两耳,离开狼窝口吧,怕它钻进洞里,等着吧,它不上来。双方在伺机窥探。他灵机一动,要求授了,高声地吼叫:“表叔——!狼来了——!”表叔跑来拿着红英枪冲了过去,那狼却巍巍不动。他一个踏步将它的后胯穿去,落了空。那狼还是不慌不忙地走着。他又剌去,那狼一松口,小叶他连滚带爬藏在小枝的背后,紧抱着他的两腿。狼虽已挂花,但它恃才傲物,顿时张开血口咆哮起来,它的尾巴摔地有声,向他攻来。胆大、勇敢、机智的表叔往侧面一闪,使劲“噌”地捅了进去。那枪尖穿过狼身,钻已入地下,它惨叫了声,舌头拉了老长。
小叶呢,他的破白衫已被染成红色。脖子被狼咬了几个口子。
表叔背了叶子赶前回家去。姑奶奶给小叶包扎了伤口,将全身洗干净,养伤不提。
表叔唉声叹气说表哥不该参军去。姑奶说:“那娃,看你说错了,谁能有早知道?他不是孔明先生,世上谁不是谋胜怕败吗?你二舅的牺牲,你表嫂的牺牲,你想过吗?世上只有孔明先生才知后事呢。表叔点点头笑了。他说:“妈,我梦见表哥和表弟回来了。表哥说日寇被八路军打垮了。他们是回来探家的。”“唉,那娃,别提他们啦,提起来让人心酸呢。”她的两眼潮湿了。她思忖着,只见两个没娘的娃在甜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