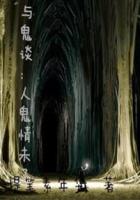有那么一对父子,异想天开,用蜡把羽毛一根一根的黏成翅膀,终于在命运之神微笑的那一天,做好了两对人工翅膀,一大一小,老父一面替兴奋得不能自已的儿子把张开的双臂改装成两翼,一面对儿子说:要是真的飞上了天空,千万记着不可离太阳太近。儿子说:知道啦知道啦,快点快点让我们飞吧。啊,张开幻想的两翼,人类终于起飞了。在无与伦比的狂喜中,他们忘了远近忘了太阳忘了人的宿命,在蜡开始熔化羽毛一片片脱落的时候,父子俩才明白了命运之神微笑的原因。
花了一生的起飞,只需要几秒钟的失败,他们就……坠海而亡。
冒险的高度原来是没有极限的,但过于惨痛的经验不得不使人先行设限。多少人想好了降落,才飞。多少人巴望着旅行,离开了还是要回来,回到所谓的家。
飞,如今只为了离开。
在所有暂时的离开里,也许只剩下读与写的本质较与古之飞行相近了。为了更高品质的灵魂,我们的思想可以一次次地起飞,去创造最大的冒险。
以前读书,为了寻找飞翔的羽翅。里尔克说:即使每一天不是灵感本身,也是通往灵感之路。现在我读书:读别人的高度,读别人的坠落,也读出别人的翅膀来。
这就是我的工作吧?我想细心地把那些美丽新鲜而又适合于将来之花园的树丛修剪出来……
不需要蜡和羽毛,不需要离家出走,文学是我亲爱的魔毯,随时出发随时降落。
旧书情
在董桥的书中读到一个有趣的关于藏书家的故事:有个人因为穷,买不起书,但很喜欢翻阅坊间出版的书目,于是就用那些他感兴趣的题目自己动手来写,结果他也有了一屋子的藏书。一屋子自己写的书,像这样子的藏书家,从来不曾听过,因此难忘。
刚好最近朋友寄给我一本《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正是董桥提到的那个故事的出处。本雅明是德裔犹太人,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及文学评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流亡法国,最后为躲避盖世太保的迫害在法西边境自杀身亡,死时四十八岁不到。
关于他的论文,我以前也有过一本《本雅明文选》,内容艰涩,译笔又差,没兴趣读完。这次文汇出版的袖珍本,就好看多了。尤其谈藏书的那篇随笔,把藏书者与书的神秘的缘分,写得既散逸又亲密。人家去拍卖场买古董,他去那儿是为了买旧书。他说:激情往往近于狂乱,而收藏者的激情则近于记忆错乱。
这“记忆错乱”用字极妙,我虽不是藏家,但家中舍不得丢的破铜烂铁也实在不少。每次透过藏品可以看到遥远的过去,那种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为了功能与实用,只是把它们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与欣赏,因此,每个回忆每种感觉都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富足的基础和钥匙。旧书,除了外在的命运,因为它本身还有作者读者间微妙的爱的价值,那感觉格外高贵。
我想起我自己书房里的书来。我收售诗集几十年了,诗集很少有一印再印的,所以,绝大部分的诗集都成了绝版本。但我绝不会去拍卖场为了某种版本的书而甘愿冒心脏病发的危险跟人去比价来买书的。以前做学生的时候,逛逛旧书摊找到几本好书,一看书价比在书店里的便宜不知几倍,就欣喜若狂以为掘到了宝贝,哪里有什么对年代,印刷,书目等的考究学问?后来,有钱买书,也纯为了“捐助”诗人才去买那些经常滞销的诗集,哪里懂得真正藏书家的痴情?如今搬家搬来搬去,还嫌藏书是种负担呢。
有收藏癖的人,往好处说是痴,往坏处想其实是病态。难怪本雅明会自杀。他连他母亲的一本贴画集都舍不得丢,更不用说莫泊桑的《驴皮记》了,然而逃亡在异国他乡时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还能拥有什么?而这条命,这藏书人的命当然是宁可与其藏书同归于尽的。书并不因他而活,乃是他因书而活。他说:看书不是阅读定居书中,驻足字丛。定居书中,给我的启示不小,那感觉真好。
五不知
柏克莱图书馆为时两年的重建工程四月总算大功告成,重新开放了。新的图书馆很新很宽亮,蛮不错的。可惜就是大了点,中文部要上二楼,儿童部设到四楼去了,只有影带部一进门就能看到。由此可知,最受欢迎的地盘在哪儿了。
以前的影视部门在地下室,中文影带又旧又少,如今几部有名的电视剧集,如《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之类也都有了。可是,一次只能借三卷,每次去图书馆,头三卷老是从缺。我不知道一次只能看三卷的人怎么受得了“且听下回分解”的煎熬。不过,也有朋友觉得这样才好,不然,有二十集影带在手边的话,所有生活秩序都会弄乱。因为要能忍得住在一定的时间停下来,吃饭睡眠全不受影响,除非是影集太不好看,要不然就是看的人简直没有“人性”。我看《雍正王朝》时,每次看到半夜三更,欲罢不能,尤其第二天还要上班,真痛苦得莫名其妙。
想想我们这些作家里头,写长篇小说的最为可恶,写短篇的比较仁慈,写论说文的也讨厌,写小品的就可爱多多。因为太不为读者着想的作家,多少有点自恋的倾向,这是我最近看影带看出来的一点心得。
新的图书馆使我想到文明的浩劫之一就是跌进知识的黑洞。愈大的图书馆带给我的压力也愈大。旧金山的图书馆常使我迷路,中文书在计算机中的目录,常使我摸不着头脑(拼音文字像单向道,一洋化就再也方块不起来)。我有个朋友为了搞清图书馆的运作,只好申请去做义工。我自己常跑图书馆,只是为了避免去书店。每次去书店,几乎每天都有新书出版,前仆后继的,自卑感油然而生,自觉渺小无以立足,益发寂寞。但是去图书馆却不同,那是个森林,前有古人,后也有来者,不必推挤,躲在里面,静待知音,从不孤独。
几年前去过中国河北的避暑山庄(以前的热河省),在那儿看到文津阁,据说那是清朝的四大皇家图书馆(文津阁,文渊阁,文源阁和文溯阁)之一。文津阁的环境美得像苏杭一带的名园,书在里面有如退休学者,跟一般大众完全隔绝。在那儿,书十足的贵族气。与柏克莱图书馆中的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不知道当作家是潜意识中想当贵族呢,还是想挤进图书馆那个书的丛林里与读者玩狩猎的游戏。
走在柏克莱街上,手中抱几本书,忽然想起四知书屋: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如果我开书店,我想取名叫:五不知。除了那四样我都不知,还有一样我也不知:不知足啊。
那瓦荷之梦
早先美国的印第安人用柳枝打个圆环,以仙人掌的刺做针,在环上钻孔,再以一种叫世纪植物(因号称一百年才开一次花而得名)的纤维像穿鞋带似的在针孔里来回穿绕,一张人造的蜘蛛网就成形了。过几天心血来潮又在网上挂几根羽毛或者几枚贝壳磨出来的珠子,于是,一张捕梦网就告完成。
捕梦网,这个过于文明的名字,我不大相信是印第安人自己取的,可能是白人的生意经吧。如今每家卖印第安人纪念品的小店里都看得到。可是,现在这些摩登的人造蜘蛛网都没悬在窗上,不是钉在墙上就是挂在售货的架子上,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
原来印第安人的意思是:把它挂在窗沿,阻挡坏梦进来,防止好梦出去。
梦——不论是出现在我们睡眠中的“超现实”,还是我们过于美化的野心——在原始人的心中,跟我们现代人的,好像相去并不很远。来无影去无踪,混沌的梦,要分出其中意识的好坏,谈何容易?科学已经快要把印第安人的生机赶尽杀绝了,这一张可怜的网子里似乎也只能网住那么一点稀薄的神话的影子而已。
三年前,我收到过一张捕梦网,却是一个真正的印第安小孩做的。那里面不知缠绕着多少捕梦者的心愿呢。
那个故事,也像捕梦者的心愿一般,不知该从何说起。
大约是十几年前,有一对中国学人。一位物理博士,一位化学博士,都是大学教授。业余时,常替中国孩子们补习功课,辅导他们升入最好的大学。日子过得愈平顺,他俩愈想到回馈的问题。
也许是中年危机作祟,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有一天,太太忽然想到:其实,在美国最需要辅导升学的不是中国孩子,而是印第安小孩。为什么不去印第安人那儿教书呢?
先生以为她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真的开始给印第安人保留区里附设的中学写信,问他们是否需要教员,她甘愿放弃大学教职,去为印第安人服务。可是,写出去的信却如石沉大海。
一年后,太太亲自到亚利桑那州的那瓦荷部落去了。她终于在那儿的灰山中学见到了校长,直接说明要为印第安人服务的心意。校长说:“您的信早已看过,只是不大相信真有博士肯来我们这里屈就。并且,我们这儿不容易留住老师,所以,无所谓发不发聘书,你如果愿意现在就可留下。”
她因此留下了,没有再回过华盛顿。
很久很久了,她的故事一直感动着我。
终于,有一次听小华说那瓦荷印第安的学校打算跟内蒙古的学校结为姐妹,想跟中国交换双语教学的心得。她的朋友郭子文在带队出发前,要她去给那十几位老师临时恶补一点中国文化。
我一听到子文的名字,立刻问:我可不可以同去?我很想见识一下真正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更想认识那两位隐士。
就这样跟小华飞了过去。在凤凰城机场,见到了子文和述中夫妇,子文圆胖幽默,已经十分印第安化,述中却瘦高还是个中国学者样。不知道是因为在故事中早已熟悉,还是难得“他乡遇故知”,我们半分钟都没有浪费在客套上,就上了他们的休闲车。
几乎开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他们那瓦荷印第安保留区,路是愈开愈偏野,天色也愈来愈暗沉,沙漠中落日的余晖虽然璀璨非凡,但夜色之暗也暗得彻底,真的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在黑得只见车灯照射之地的路边,却不时闪现出一两个白色花圈,我忍不住问:“那是什么?”
“是印第安人被撞倒的地方。他们酗酒的情况真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子文说,“真的,说来真叫人伤心。我有个学生本来是很有前途的。好不容易让我教得可以代表学校去跟白人比赛数学了,谁知道比赛前一天晚上,他喝得烂醉,第二天根本没办法去。”
那种伤心,是不属于血泪的那一种,可是当你一个人静静地想起来时依然会心如刀割的那一种,我想我可以体会。后来呢?
“后来我发觉那就是他们逃避现实的方法。我们做老师的完全斗不过他们的家长。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整个民族的自尊、自信让白人摧残得不像样子。帮他们重建信心真的很不容易。”
夜里,我们还看不出那里的贫困与荒凉。但第二天在大太阳底下一望,这才明白所谓的保留区就是一望无际沙不沙土不土连仙人掌都懒得生长的荒原。这儿唯一的中学名叫灰山,倒很贴切。想当年印第安人不签字也是死路一条,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黄土地上几排平房,散落如一个营区,使我想到眷村。简朴是够简朴的,但这是在美国吗?是啊,这就是灰山中学的教职员宿舍。然而,屋内倒很舒服,子文用印第安人的披肩做了窗帘,述中在客厅自己装配了大耳朵大银幕电视,墙上桌上都是孩子们的手工艺品。三毛在“白手成家”中也是因陋就简,在化外自开天地。灰山竟也有了个中国之家呢。
述中说:子文的学生都管她叫grandma,常常一进来自己就打开冰箱找东西吃,晚上有时还问可不可以睡在这里。这些手工都是学生或者家长送的礼物。
中国人总说要融入美国的主流,总说要奉自己为别人服务,可是子文夫妻俩什么大话都没说过,悄悄地就来跟印第安人同甘共苦了。诗人纪弦写过的小诗,又一次在我心中响起:
从前我真傻/没得玩耍/在暗夜里/期待着火把/如今我明白/不再期待/说一声干/划几根火柴
我不知道他们的火柴划在印第安人的荒原上,能有多大的光亮,但在子文身上我真正见到了女强人的典范:那种韧性,那种包容力,那种随遇而安,那种无私的爱。在她灰山的家中三日小住使我对她倍加感佩。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们家窗子缝隙中生长的一株瘦小的沙漠植物,连窗台上的沙都长得出植物来了,那外头每天吹来的风沙可想而知。随沙尘吹来的种子,卡在那儿,生长就是使命,其他都是天意。粗砾其外,丰润其内,正像子文他们的写照。
由奢入俭或由俭入奢,或许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那顿悟时的灵光一现从何而来?我也常想在暗夜里划几根火柴呢,可始终梦一样还挂在窗上那张网上。
那就是我从子文那儿得来的一张印第安小孩亲手做的小网。上面曾经捕到过一个那瓦荷之梦,那个梦已经舍不得出走,留在灰山的窗隙中,为谦卑的人做着永远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