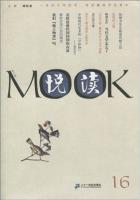除非有病,一个人要能让自己胖到痴肥而丑陋的地步是不可思议的。中美两国,富足的程度当然有异,可是如果两国的富足程度对调的话,我想中国胖子也不会有美国胖子多的。因为在自制力、耐心与勤劳这些方面说来,美国人都太不及中国人了。如果吃时能稍稍有点节制,平日操作勤劳些,对减肥运动多点耐心与恒心的话,一个人又能胖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大概也很重要,中国人胖了会自卑,不大敢见人,美国人太个人主义,胖了会自以为有特色,还要争取“胖”权。若不是胖与许多疾病有所瓜葛,我们这些瘦老中在美国,早就要“无立锥之地”了。
“美国人怕死,每战必败”是越战之后的“趣谈”。可是,近年来美国人怕胖已怕出一种病来。那病是精神性厌食症。任何食物都不想吃,吃了就吐,有人一天吐上十几回。要不了多久,就瘦得不成人形,最后还有生命危险。“木匠二重唱”的才女歌星就是得了这个病症,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死得真冤。非洲人因饿荒而亡,美国少女因怕胖而面对着佳肴呕吐。《镜花缘》的作者就是有再好的想象力,也写不出这样奇怪的“胖子国”来吧?
据说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准的高低,与那个国家糖的消耗量成正比是很明显的事实。美国年消耗糖量居世界第一,这大概也是他们胖子多的原因之一。这里食品店里蛋糕、巧克力糖之类的甜点,其甜度往往是中国人不能忍受的。我每次看见食谱里有糖的地方,总是要把分量减成三分之二或一半才行。糖,实在是食物当中,最坏却最具有诱惑吸引力的东西,很像风骚的女子,我这么说,是因为忽然想起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头的王娇蕊。
娇蕊的晚饭就吃一片烘面包、一片火腿,因为怕胖。可是平时又手里捧个玻璃瓶,里面是糖核桃。这又不怕胖了?她的先生士洪是这么解释的:
“他们华侨(娇蕊是新加坡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跟外国人学会了怕胖,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动不动就吃泻药,糖还是舍不得不吃的。你问她为什么吃这个,她一定是说,这两天有点小咳嗽,冰糖核桃,治咳嗽最灵。”
我现在左邻右舍,左边是太太胖、先生瘦,右边是先生胖、太太瘦。韩国诗人许世旭有一天酒后发言道:
“我看夫妻当中,一胖一瘦的话,多半是瘦的脾气坏,胖的脾气好。”
我说:
“如果两个人胖瘦一样呢?”
他说:
“那一定是天天大打出手。”
两个瘦子相打,我可以想象。两个胖子不知如何打法?一般说来瘦子跟悲剧有关,胖子根本就是喜剧。我们在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里,看到的男主角是个胖胖壮壮的中年人,因为他演得太好,不觉有异。后来我在匹得芒看了一次舞台剧的《屋顶上的提琴手》,男主角竟是个瘦高的人,剧散后想想,一个在农庄上辛勤工作,养了五个女儿又要对付啰唆太太的这么一个人,当然应当是瘦子才对。可是按照老许的理论推演起来,男主角是给他太太“气”“胖”的倒也十分可能。
人家说:人到中年,发胖如同水火,挡都挡不住。有一天,我若发起胖来,我愿意说那是因为我脾气变好的缘故,与年龄无关吧。
花生糖
我小的时候,很好吃。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固定的零用钱”这类玩意儿的。有时在路上捡到一毛钱就会高兴得雀跃三丈,因为一毛钱可以买到两颗橄榄、话梅或是一块花生糖呢。
我的故事,是从跟一位同学的友情开始的。
我的同学高胜利——因为是在抗战胜利那年出生的——是标准眷村里长大的孩子,非常能吃苦。除了上学,在家的时候总是得帮忙料理家事。我记得有一次晚饭过后,功课做完,十分无聊,就到她家去找她。
“她在抽水机那边洗衣服呢。”高妈妈说。
我跑到抽水机那儿,一看,好多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聚在那里,一人一只大水盆。盆里一大堆待洗的衣物,盆边斜架着一块木制洗衣板。昏黄的路灯下,白白的肥皂泡沬沿着洗衣板一揉一搓地膨胀起来,好玩极了。
“我帮你洗。”我还记得当时兴奋的心情,后来读到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头说到汤姆被处罚去油漆围墙,他的同学争先恐后,甚至用苹果、玩具来交换工作,我就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可是,胜利只让我帮她打水。那时候自来水还是奢侈的事,水都得用“帮浦”自己打着用。我家有个大水缸,我记得还要请人每两三天挑几担水来,把缸注满。
总之,后来我天一黑就跑去帮她洗衣。其实,是蹲在洗衣盆旁边玩那滑滑溜溜的肥皂水。
有一天,胜利来找我,给我看她妈妈给她的一毛零用钱。我们俩兴高采烈跑到小杂货铺去买糖。为了铺子里“琳琅满目”的零食,我们起码费了十来分钟,最后终于决定买了块花生糖。
那时候的花生糖,可没有现在这样的“秀气”——一口一块。那时是一大片,长方形,胜利把它对分了,掰开递给我一半。多够朋友!
好景不长,可惜。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们吵了一架,再也不愿彼此是“朋友”了。她决心要讨回她那一半白浪费在我身上的花生糖。
我在家没有洗衣、烧饭过,哪有零用钱?运气又不够好,低头在路上来回走上十趟八趟也没捡到过一分一毫。怎么办呢,只好关了房门,不敢出去。母亲觉得非常奇怪,她那个野丫头一样的女儿居然有一天乖乖地自动闭门读书,而大门外还站着一位满脸怒容的同学,忍不住追问起来:
“高胜利为什么站在门口?”
我觉得丢脸极了,死不开口。
母亲又去问门口的那一位。
“花生糖还来。”我只听见胜利的“怒吼”。不记得母亲是给了她一毛钱呢,还是要我去照样买块花生糖还给她?反正只有那一声“花生糖还来”永生难忘,其余都已淡远,不复记忆。
女儿由牙医师那儿回来后闷闷不乐,因为发现了两颗蛀牙,平日爱吃甜食之故。我本想给她一点“机会教育”,看她一脸郁然,实在不忍。故改口说了一则小时候的故事。“花生糖的故事”对女儿而言,是一则十分可笑的小插曲,然而,在我童年回忆的百宝箱中却好似一样蒙了尘的古玩。如今我拭去岁月的尘埃,在上面看见的是淡淡的甜与浅浅的伤——那两个月光下同洗着一盆脏衣的小女孩到哪里去了呢?那两个放学后小店门口细心对分一块花生糖的小女孩哪里去了呢?
滑雪记趣
美国人把“过生日”看得比“天”还重要:我有个朋友,同事为她开生日派对,她得先做头发、修指甲什么的,一看日历,却是星期日,就说:“教堂不去了。”
可是,林肯的生日,华盛顿的生日,他们却可以胡乱更改。要是林肯先生这一年的生日是星期二,他们就不客气地移到星期一去;要是华盛顿的生日在星期四,他们就请华先生星期五才过生日。要是碰巧是星期三,那就更是左右随之了。总之,他们生日我们放假,那样的好好先生,就是活着,大约也不会反对将就着成全我们大家过一个“长周末”吧。
加州就更妙了。有些中小学校干脆把林肯、华盛顿生日合并为“滑雪周”:放一整星期的“春假”(其实四月初复活节前后那一星期的假才真正是“春假”)。据说,因为那两位伟人的生日使周末拉长了一日,好多家长就带着孩子去滑雪,怕再不去,雪要融掉了,所以学校里头一到了这个时候,学生就纷纷“告假”。校长老师一看,半数学生都不在了,课还上得成吗?有假大家放吧,因此就创造了这个美名:滑雪周。
在旧金山这里,滑雪的胜地是在太皓湖附近,车程只有两三小时而已,当日来回都可以。可是,太皓离赌城雷诺不远。多数的人喜欢滑完了雪,到雷诺下榻,晚上在那个不夜城里拉一拉吃角子老虎或者过一过赌城的“风流”瘾,第二天再滑滑雪才回来。旧金山(或者说加州)变得这么“不伦不类”实在不是没有道理,谁叫它有个靠赌博吃饭的邻居呢!本来滑雪跟赌,多么的风马牛呀,但在这儿的旅行社,“滑雪发财团”却是白菜豆腐一样。
不过,我头一次滑雪是真正的“纯滑雪”。纯粹是为了陪女儿蜜糖那个“小人”,我想这条命也值不了多少,大不了断上几根骨头罢了。
其实,到滑雪的地方去,就是不滑,看看风景也已值回油价;尤其人少的时候和入夜时分,手里拿着一杯热咖啡,在看台上遥望穿红着绿的小人影儿坐上了缆车,由小而无,消失在白雪的山峦、青蓝的天空和苍绿的松巅之间。不一会儿,山上滑下来一粒小红点,飞似的落下来,还跟你招招手呢。那种快乐,连那种快乐的感觉也都成了美的一部分。
可惜,女儿的爸爸既怕高又怕冷,宁可待在家里,我只有硬着头皮单枪匹马也去雪地上凑了一个粉红色的“逗点”。
我们参加的是初级滑雪班,每人每两小时学费十二元(如要私人教练则每小时二十五元)。雪鞋、雪板租费每人十一元。这是下午的价格,上午还要贵些。有人说滑雪、网球是“贵族”运动,大概不差。小孩子不停地长,鞋子不断要换新,雪板和手杖的长度跟身高、体重更是关系密切,买一次都挺贵的,更不用说这些还是“消耗品”。其他御寒衣帽手套什么的还不算在内呢。
平均起来,我大概在雪地上每十分钟就要跌一次跤。原来一个人想要平衡自己,使自己不至于跌倒,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的容易,在冰上、在雪上,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是。两小时课毕,我已累得筋疲力尽,女儿却跟别的小朋友坐缆车上山去了。
我大部分的精力与其说是用在滑雪,倒不如说是用在跌倒后再站起来。我们通常形容别人摔倒的样子,用的大抵都不是什么好词句,好像天生有笑话别人跌跤的本能似的。那还是在平地,雪地里穿着这千斤重的鞋,鞋底套牢着一根数英尺长的板条,跌倒了要想爬起来的那副狼狈相,可真是连企鹅见了大概都会走过来笑话的。
“举步维艰”那里面的“步”,指的一定是滑雪人的“步”,我现在才想到。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里有位教授过百岁生日,记者去访问,他说:“我四十岁才学滑雪,一学就爱上了。七十岁时,我是冬运滑雪队的领队。我不知道什么叫‘老’。”我看着女儿蜜糖一小时不到就学会了滑雪,两小时后就上上下下独自去搭缆车,我可是知道什么叫做“老”。尤有甚者,滑雪回来第二天,全身酸痛;第三天,发高烧;第四天,咳嗽……得了“菲律宾流行性感冒”,非常地不中用。
病也有病的好处。病中,报上大字小字没有不看的,倒发现美国报上的妇女家庭版与中国的有点儿不同。中国妇女爱说儿女,美国妇女爱谈的是猫狗。其中有一篇文章说:
现在又到了全家出动去滑雪的时候了。有时候,家里的狗也不能不带。如果带狗去,有几件事你得注意——所有狗的预防针是不是都打了?给它买件毛衣,很需要。多带些浴巾,给它擦干身子用,尤其是脚心的碎冰片和肚子上的残雪。“家狗”是已经给我们驯养惯了的,跟北极拉雪车的那种狗并不一样。北极狗毛多皮厚,有自然的御寒能力,家狗却不行。每年滑雪周一过,兽医那儿就会出现许多患了冻疮症、伤风症等等的狗。……
我没敢把这篇文章给家里的人传阅,因为我知道外子会怎样的来取笑。唉,不争气的“家狗”是做定了与滑雪无缘,虽然没跌断半根骨头,亦复何言!
半月湾里南瓜肥
万圣节来了,孩子们的丰收节。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唐人街主日学校的老师,带着一群中国孩子,到半月湾的南瓜田里选南瓜。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一个个橘黄闪金的大南瓜摆满了一田。孩子们这个摸一下,那个抱一下,恨不得每一个都带走的样子,真是暮秋时分最最动人的景致了。
半月湾到处都是菜田,有几处南瓜田傍着海湾,湾里有各式游船——有帆无帆、单帆双帆、小艇汽船皆可一见,风景很好,所以很多人不远千里到这儿来买南瓜。就像圣诞树,人工做得又好又不掉叶子,可是,有很多人年年要买真树——自己到林里去砍或者在苗圃里去选,假的永远无法取代真的,因为人们要的不仅仅只是那个瓜或者那棵树而已。
半月湾一路上有很多的南瓜田。有的粗放没有一点打扮,一个个南瓜灰头土脸地排着不很整齐的队伍,放眼一看,很有质朴的魅力。有的则是一副旅游胜地之貌,田里扎着牌楼上写“万圣节快乐”之类的“标语”,玉蜀黍秆做成草人状穿插在南瓜堆里。有的南瓜已经刻好变成南瓜灯,咧着笑开的大嘴讨人的喜欢。有的地方更有赶集的味道,南瓜田边还有来卖花、卖室内植物、卖南瓜派的小摊子。
大部分的南瓜田里都铺着稻草,走在干草上的感觉,跟走在草地上或水泥地上的多么不同。孩子们的裤管上沾着稻草,捧着南瓜的小手上沾着泥,脸都笑得跟南瓜一样滚胖滚圆的了,这哪里是城里头或者高尔夫球场旁边可以一见的场面?这里不是江南,我们从来不曾赏过秋荷或者划过采菱角的小舟。这里也不是高原,风吹草低牛羊一现的情致也只在书上读过。幸有万圣节,我们才得以分享了一点大地秋收后的余兴,虽然是没有一点中国味儿的。
不过,这星期的《亚洲人周报》(Asian Week)上,倒有一篇文章说万圣节是中国发明的,因为中国的七月半是鬼节,跟万圣节有点相似,虽然有点附会,但是因为万圣节而能想起一点中国文化来总是好的。
不论中外。我看节庆都是给大人返老还童设的,孩子们只有参与的份儿。唯有万圣节,孩子们较像主人,大人们也比较地不像“喧宾”。
你瞧,孩子们给南瓜画脸打洞,比赛穿着存心吓死人的奇装异服;等挨门挨户讨了糖果回来,还要数来数去,直数到圣诞呢!在这满是糖的快乐里,我们也只好暂且不提看牙医的事了。
在美国过中国年
那年的春节第二天,女儿跟我嘀咕:“老师要我星期一在学校里给同学们报告中国新年里,我吃了什么、玩了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们只吃了一只烤鸭,怎么搞的?”
她说在书上读到舞狮舞龙、年糕、压岁钱什么的,比我知道的还详细,我心里一阵凄凉。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她交代吃年夜饭的事,我想说的是:那些吃食倒不怎样,要有那份人情与热闹才显得特别。人情?如今要想三代团聚,筹了路费还得愁假期。人各一方,恐怕五年也难一家凑齐一回。热闹?没有唐人街的地方,只有冷清依然。
幸而我那童心未泯的大姐,带着鞭炮由纽泽西飞来。孩子们乐极了,她们把小鞭炮一个个插在雪上,我点了一支香,她们在雪里放起鞭炮来。邻居两个小男孩赶来争着要玩。小小的爆竹在雪上炸成一个个浅坑,坑沿是淡黄色的火药和碎碎的纸片。因为被雪闷住了,所以爆炸的声音不大,我们便不去担心邻居的反应。偶有邻居探出头张望,也笑着对我们说:“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