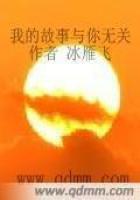尽管一连出了几件使韩欲明大为苦恼的事,但由于杨介人的耐心开导和精心辅助,经过一段日子的认真整顿,天门大会的组织性、纪律性普遍加强了。各基层香坛的组织成分较之以前大为纯洁,其骨干力量基本保证了贫苦农民的绝对地位。加之杨介人兼任了牛光耀的职务以后,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向广大民众灌输了不少的新思想、新观念,这就使天门大会的各级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是令人振奋的。
紧张的操劳,过度的思虑,使韩欲明消瘦了许多,面色显得相当憔悴。
这一天,韩欲明的心情格外地好,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想到城外去踏秋,于是就叫了杨介人和刚刚从修女院治伤回来的路欲启,款步出了南门,跨上田间小路,一边说笑,一边顺地岸溜达起来。
啊!多美的秋天!虽然遭受了严重的雹灾,但由于新政权唤起了广大军民战胜天灾的巨大力量,所以这一年的秋景还是相当可观的。
天上没有云,地下没有风。天地万物都在静静地运动。大地呼出的氤氲气息中,饱含着五谷杂禾的馨香。黑亮的蟋蟀从地堰边的小洞里探出头来,轻摇触角,款动响翅,鸣奏出“哩——哩——哩——哩”的悦耳动听的咏叹调;绿油油的蝈蝈儿爬在高高的庄稼穗头上,把响翅对着阳光,演奏着“哲哲哲哲”的高昂激越的行进曲。金秋,这是一年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节啊!
韩欲明他们兴致盎然地钻出田间小径,跨上通衢四方的大路,正要回返,忽听一处新做的打谷场上传来了孩子们击掌齐唱的歌声:
当当嘀,嘀嘀当,杏黄大旗冲天扬。
欲明大师过漳河,杀得奉军喊爹娘。
呛呛采,采采呛,天门大会把家当。
苛捐杂税全免掉,家家都过好时光。
啊!多么熟悉的歌声!韩欲明听了,心中忽如刀绞,哀哀长叹一声,向杨介人和路欲启说:
“唉,不知你俩心里咋样儿,俺一听见这歌儿,心里就像扎刀子。”
“根子哥,俺真有些蹊跷。”路欲启略显埋怨地说,“当时你咋没细细问问那破鞋,她和刘先生是真有那事,还是咋的?”
“唉,先启呀,当时也真叫那破鞋把俺气恼啦。”韩欲明解释道,“赤屁股露肉的在俺面前耍不要脸,那不是臊俺的面子嘛!俺一时火起,就……”
“根子哥,这些日子咱们的‘檩条’儿可折得不少啊。文的、武的,死的死了,跑的跑了。再说俺咧,唉!”路欲启用骨朵儿手指指可怕的右脸,眼眶里禁不住涌起了伤心的泪花。他脸上的伤痂揭掉后,只在洗脸盆里照过一次,就再不敢端详自己的五官了。那是一张啥样儿的脸啊!右颊两个铜钱大的红疤把右眼角和右嘴角紧紧地向一起拉去,外翻的下眼皮亮着红肉,扯开的嘴角里露着白牙。英武的小“赵云”变成了丑八怪。他伤心极了。他曾想吊死在修女院教堂后边的树下,也曾想跑到渺无人迹的深山老林和那些山禽野兽为伍。然而,韩欲凤那最珍贵的给予,融开了他冰冻的心田,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他用树枝当标子,当步枪,练呀练,练呀练,那残废的右手除了失去抡大刀的功能外,竟然还能和左手配合着使枪呢,那变了形的右眼也还照样能瞄准目标呢。终于,他恋恋不舍地辞别韩欲凤,兴冲冲地回到了离别多日的火热的总部。可是呢,惨变的面容毕竟无情地改变了他的个性。在众弟兄面前,他失去了那种英武活泼的气概,取而代之的是沉郁寡欢,冷森逼人。尤其当他知道了韩欲虎被杀,刘珏自尽,牛光耀遁走的事情之后,越加显得心事重重,面色忧烦了。这当儿,韩欲明提起了刘珏,他禁不住就又伤感起来。
韩欲明见路欲启伤感、哀怨,一时也低头不语了。
杨介人为了消除这种不愉快的气氛,忙向他俩安慰道:
“二位团师不要伤感。刘珏的事日后总会明白的。还是那句话——要从中吸取教训,增强思辨力和洞察力。”
“唉,杨先生,话是这么说呀,”路欲启感慨道,“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咧,忽霎儿少了这几个人……哦,还有谷酉元也没有回来,心里该不是灰失失的哩!”
“哦,是这样。”杨介人其实已经利用参政先生的身份,以走访四街百姓为名,多次和吴旦孩交淡,详细调查分析,基本弄清了刘珏的死因,只是怕揭出高堆才的劣迹而再度出现大的思想混乱,才掩着没向任何人透露。他打算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要揭出案情,清除混入领导集团内部的不纯分子,进一步教育全体官兵擦亮眼睛……眼下他只能多给韩欲明操一份心,帮他提高觉悟。他诙谐地安慰道:“二位团师的心情,我很理解。不过革命队伍里就是这样。有来的就有去的,有去的也必有来的。”
韩欲明一展眉头,深有感触地说:“杨先生,说真格的,眼下俺真正实靠的人,就数你和先启呀。俺也觉得日怪,咱们到一块儿,不论好话赖话,说出来都熨帖。”
突然,东边的岔路上跑出一匹快马,慌急朝韩欲明他们奔驰而来。三人定睛一看,见是高堆才,心中疑惧顿生。
“总团师!叫俺好找啊。”高堆才来到近前,滚鞍下马,面带惶色地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双手递给韩欲明,急巴巴的说:“俺绕城转了一圈儿才瞧见你们在这儿。他娘的!冯玉祥又派人来啦!”
“啊?”韩欲明惊愕地问:“多少人?”
“一个。”高堆才悻悻地回道:“说是只管送信,不管别的。”
“走了没有?”
“没哩。说是讨了你的回书才要走。”
“他娘的!总不叫爷们安生!”韩欲明骂了一句,和大家急步向城里走去。
一支二十一人的小队伍,凭着韩欲明的回信,越过韩欲德分队驻防的横水镇,匆匆向林县城赶来。
这支小队伍一律肩扛“汉阳造”,腰挎盒子炮,高视阔步,威风凛凛。队前三个骑马的,更是腰板挺直,英武端庄。为首的戴眼镜的年轻长官,正是前不久来和天门大会谈判收编事宜的冯玉祥的代表——刘斌。
刘斌一反上次来时的仪态,浑身上下是一副威武严肃、盛气凌人的武官风度。他从郑州乘火车来到彰德,又来到庞炳勋部驻防的水冶镇,先派出一个士兵带了冯玉祥的手谕,到林县城讨了韩欲明同意接见的回信后,才于今早带了随行人员急急向林县城赶来。这一次,他决意要完成冯将军赋予的艰巨使命,以消除上次谈判失败给同事们留下的笑柄。
刘斌十分敬服冯将军的心计。上次谈判失败之后,冯将军曾分析说:天门大会能够控制太行山上下几百里地域,又敢于和阎锡山、张作霖作战,确是十分了得。然而,谅他韩欲明一个粗野山汉,绝不可能有此大韬大略。其中必有高人辅助。共产党最善组织农民运动,且以乡村为立足之本。天门大会势力猛振,共产党不会不派人去操纵啊……哦,那个姓杨的,是不是过去曾抓捕过的杨介人呢?那可是个难斗的人啊……果然,就在冯将军和蒋介石总司令举行了“徐州会议”不久,从南边秘密送来的“CP”名单中,真的就有杨介人和马春汉两个名字。而且都是和周恩来共过事,又直接受毛泽东指派打入天门大会的。刘斌恍然大悟,啊!难怪那次谈判的时候那个姓杨的那么机智主动,导致了谈判失败。原来天门大会已经叫他操纵了啊!那么,这次谈判能不能成功呢?刘斌心中虽无把握,却很自信。他已经反复考虑过了,只要把那两个CP分子一抓,再向韩欲明讲明当前的大势,连唬带哄,软硬兼施,不怕他韩欲明不受招抚。共产党的许多组织已经土崩瓦解,冯将军的国民大军已经控制了彰德一带,人非草木,孰能无心?难道韩欲明就不考虑他的处境、地位和命运吗?在刘斌想来,这次履行使命虽不敢说十拿九稳,但至少应该是大有成功希望的。
刘斌被韩欲明和杨介人等人客气地从城东门迎进了黄华书院总部。这一次的接见情景和上次大不相同——没有过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刀门;也没有见到赤裸上身、持枪执刀的凶悍卫队。中厅门口两边全是手持步枪、腰挎盒子炮,身着整洁戎装的军人。若不是那圆筒形的帽壳和军装上隐隐地显现着手工缝制的痕迹,刘斌简直就不敢相信这里是土百姓的神会“窝子”。
刘斌带着六个随从士兵走进中厅,更是一番新异的气象:用木板新做的高高的神台两边,竖着两扇大屏风,屏风上各有两个紫心红边的圆形图案,图案上分别写着“忠”“义”“勇”“武”四个斗大的隶体黄字,透射出一股庄重的豪气。屏风内侧是一副黄底黑字的对联。上联曰:“除世间恶魔无往不胜”,下联云,“扫天下不平所向披靡”;横批是“替天行道”。东西山墙下摆了两座丈余长的枪架,红樱标枪整齐地插立其间,犹如仪仗侍立。地当间一反上回的座次,一溜纵摆了四张方桌,桌面上罩了家织黄色布幔,从门口直通到神台前边,仿佛是一座圣洁的“仙桥”。四盆含苞待放的黄菊花摆在桌上,散发着浓郁的艾蒿香气。桌子两边是两溜紫黑闪亮的太师椅,椅垫、椅披也全是黄色土布做就。桌上的茶壶茶盅也相当精致……整个中厅里呈现着一派素雅幽静、庄严肃穆的气氛。刘斌正暗自惊讶,忽见韩欲明展臂谦让道:
“刘参谋远道而来,请入座用茶。”
“总团师不必客气,请一同落座。”刘斌大咧咧地点点头,诡谲的目光从眼镜后一乜斜,坐在了客位第一把椅子上。
韩欲明同路欲启、高堆才、杨介人、马春汉、韩欲龙、韩欲庭等六人相继坐在刘斌的对面之后,韩牛牛便立即上来挨个儿倒茶。韩欲明见刘斌的随从士兵都规规矩矩地站立在一旁,心中很觉有些不忍,就指着客位那边的空椅子说:“诸位也请坐呀。”
“不必。”刘斌摆摆手,冷冷地说,“国民军军纪严明,不敢俯就。”
“哎,俺天门大会兴的是官兵一致。”韩欲明笑道,“入乡随俗嘛。坐吧坐吧。”
“那……”刘斌板起脸孔,向他的士兵们招了招手,说,“好吧。客随主便,那就坐吧。”
韩欲明见刘斌的举止言谈和上次来时大不一样,禁不住心里犯了嘀咕。他顿了片刻,强作客气地说:
“刘参谋上次来,本坛招待不周,请包涵着点儿。这回咱是吃酒说六国,有啥事儿边吃边喝边说。牛牛,上菜!”
刘斌毫不拒让,冷冷一笑,点了点头。
按当地的传统习俗,两桌酒菜很快摆了上来。酒过三巡之后,韩欲明开口道:
“刘参谋二次找俺会谈,不知又有啥瓜葛。请明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