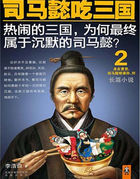她的穷戏剧家恋人,自从一些激进派的社会科学研究家频繁进出他的家之后,他终于写完了一部长篇戏剧。他履行了诺言,写了柠檬林。柠檬林是全剧的尾声,然而他在现实社会中无法找到明亮的柠檬林。在他所说的根基颠倒过来之后的理想世界中,只有在这片柠檬林中,男女主角才能得以相会和倾谈。然而,他写是写了这部戏剧,却同一话剧团的名演员坠入了情网。按照惯例,柠檬女又退出了情场。正如她所说的那样,他也出名、发迹了,爬上了天梯。
她接下来的一个恋人,是一名经常到戏剧家家里高声大喊大叫的职工。但是,也许上帝赋予她观察男人的感觉是有限的缘故吧。的确,这个男人不仅没有出名、发迹,而且他还作为煽动者,失去了职业。她丧失了观察男人的感觉,这是她活生生的感觉。然而,她是犯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判断上的错误,还是对出名、发迹感到厌倦了呢?
为她举行葬礼的那一天,戏剧家的戏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台。扮演女主角的是他的新恋人,他从她的台词中感到她在模仿柠檬恋人的口吻。这出戏以辉煌的成功宣告结束的时候,戏剧家把这戏尾声时舞台上的柠檬果全部装上了汽车,向柠檬女的墓地疾驰而去。然而,在她的木牌前,大概已有人上供了吧,点燃着犹如柠檬的层层叠叠的灿灿的灯火,恍如一层层摞起的十三日之夜的月亮。戏剧家见此情景,喃喃地自语:
“原来在这种地方也有柠檬林啊?!”
兄弟
——[日本]岛崎滕村
弟弟为了支付嫂嫂和残疾的弟弟阿吉的生活费四处借钱,哥哥那儿借不到就去别处借。当他把生活费给照顾阿吉的山胁时,他感到阿吉在嘲笑他。
此时,在旁边听着的弟弟已不耐烦了,因为嫂嫂总是唠唠叨叨地说话。就像本来是讲雷门的事,可是她偏要先从新桥扯起。开始,他用“嗯、嗯”、“然后又怎么样了”之类的话搪塞一下,后来他实在应付不下去了,就很无礼地打断了嫂嫂的谈话:“山胁不能再照顾阿吉了,是这个意思吗?”
嫂嫂苦笑着说:“那倒也不是这个意思呀。山胁也是个赋闲的人,倒也很愿意照顾阿吉。但是无论怎么说,阿吉终究是个很拖累人的病人呀,物价又一个劲儿地上涨。”嫂嫂想了想又接着说:“听说阿吉也有点过分呢!山胁跑来说,以前对付着吸烟丝就行了,最近却提出要吸纸烟,没办法,只好买来给他了。现在是每天吸两盒朝日牌香烟。……”
嫂嫂说着说着又要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弟弟急忙插话说:“如果有十元的话,阿吉的生活过得去了吧?”
“问题就在这儿呀!山胁说如果每个月不多给两元的话,他照顾不了阿吉的生活。”
弟弟摸着下巴说:“你看这样行吗?嫂嫂,你把阿吉接来照顾,我每个月拿十二元,这对你来说岂不是更合算了吗?”
听到这话,嫂嫂消瘦的身体明显地战栗了一下,说:“算了吧!让我和阿吉住在一起,那我死也不干。”
这时候,弟弟恍然明白嫂嫂特意从下谷来此的用意了。
“就这么办吧,请你告诉山胁。”弟弟沉吟了一下说,“难为嫂嫂跑了一趟,今天可实在没办法。”
弟弟的妻子这时候进来了。弟弟转身对妻子说:“你先拿两元给嫂嫂,剩下的让阿吉来取吧!你把衣服拿来,我现在出去一趟。”
弟弟离开了长火盆,开始换衣服。妻子从壁橱的柳条包里拿出几双洗干净的布袜子,一边看一边笑着说:“出一两趟门,就不穿了,有多少双也不够啊!”
尽管妻子这么说,仍从里边挑出一双好一点的递给了丈夫。弟弟漫不经心地扯断了连缀的线,硬将皱巴巴的布袜子套到自己的脚上。
“嫂嫂,库页岛那边有信吗?”弟弟一面扣着袜扣一面问道。
“前些日子来信了,说工作挺好,——还向大家问好。”
“只要他好好干就行了。”
“是啊,我也这么想呀!”
“还没往家里寄生活费吗?”
“才刚刚到外边干活一年,怎么可能呢!”
弟弟戴上夹帽子,离开嫂嫂,随后走出家门。
弟弟来到哥哥在工地的公寓里。正巧哥哥刚打完电话回到二楼自己的房间。哥哥说要写封信,就伏在桌子上,急急忙忙地挥动着笔杆,然后又从头到尾把写完的信看了一遍,封上口,在拍拍手叫人的同时,把身子转向弟弟。并对进来的公寓的女仆吩咐道:“这是封急信,马上给我投送出去。”
待女仆走后,哥哥打量着弟弟。
弟弟说:“今天我来有点事。”
“哦,等等!”哥哥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站起来从橱柜里拿出一个新的装着点心的铁盒子说,“这是别人送的,来,尝一块。”
哥哥已经有些秃头了,而弟弟的黑发里也早已夹杂着白发了。这几年以来,兄弟两个一直承担着住在下谷的嫂嫂一家人和阿吉这个不幸的弟弟的生活费用。从一定程度上讲,哥哥的秃头和弟弟的花白头发就是这段历史的斑斑痕迹。
“哥哥,想请你先垫一下阿吉那份生活费……”弟弟说,“我这个月太拮据了。”
“哎,你也竟至如此!”哥哥苦笑着说,“我满以为你应付得了呢,这个月我也没给下谷那边送费用。哈哈哈哈哈!都困难到一块儿去啦!”
“忘了告诉你了,山胁又要求增加费用了。刚才嫂嫂来说了这个意思,我已经答应了。”
“阿吉真是个使人操心的家伙呀!可他终究是个活着的人嘛,如果是个野兽的话,那家伙早就让别的野兽吃了,这是一定的。”说着,哥哥捋起袖子,又接着说,“唉,话又说回来了,他的思想方法就是错误的。既然是个窝囊废,就应该像个窝囊废似的,老老实实地听从大家的安排。残废到那样,还动不动要责难别人。”
“刚才我和嫂嫂商量:把阿吉接到她那儿,这样在经济上岂不是对她更合适吗?可是嫂嫂说:算了吧,若和阿吉住在一起,她宁愿死掉。”
“受照顾的人还说这种话!”
“唉,说起来阿吉也真够可怜的了!”弟弟说着,又改变了语气,“我的岳父指责说,我们这样帮助兄弟是不对头的,哪有借钱帮助人的道理。”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哥哥爽快地笑着说,“确实,你岳父靠不屈不挠的创业劲头起家。这也是你岳父所以能获得成功的原因。当然啦,他说的也只是一种见解罢了。而我呢,也有我的看法。我在公寓住了十多年,尽管世人认为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但是我不记得我麻烦过任何人,一个硬币我也从来没有从哥哥那儿要过。尽管这样,我还是帮助了下谷的嫂嫂一家人。总之,我是在尽力而为。”
“这种事一个月两个月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长年累月的话,可就有困窘的时候了。”
“可不是嘛,真有困窘极了的时候呀!”
既然哥哥的情况不允许,弟弟站起来,准备再到别处去借钱。
“你看,特意来一趟,实在抱歉。”哥哥说,“喂,等等,我把这些点心分分,带回去给孩子吃吧!”
弟弟把哥哥给的点心包放进袖兜,离开了公寓。
阿吉已经四十岁了,整日对着冰冷的墙壁,寂寞地卧着病躯。给吃的就吃,不给吃的就不吃。不知什么时候,阿吉开始对世事不闻不问,像生活在黑暗里的墙壁似的,在打发着日子。只要是一想到阿吉,弟弟的眼前必定同时浮现出那堵冰冷的墙壁来。可以这样说,墙壁就是阿吉的一生。而且一想到世上还有阿吉那样的人,弟弟便不由得为自己的奔波忙碌而感到可笑起来。但是,又觉得只要是阿吉活着一天,就不得不养活一天。
那天,弟弟也因为还有别的事,风尘仆仆地跑了整整一天,才好容易凑够了钱回到家里。
次日,按照约定,嫂嫂的女儿来拿照顾阿吉的生活费。当弟弟从钱包里拿出十元交给她的时候,却反而觉得受到了阿吉的嘲笑:
“虽然兄弟很多,却都不够意思啊!”
“恶”的化身
——[日本]芥川龙之介
一只在艳阳下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雌蜘蛛为了自己的儿女献出了生命,尽到了作母亲的天职。
沐浴着盛夏的阳光,雌蜘蛛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
空中响起振翅的声音。不久,一只蜜蜂落到了月季花上。蜜蜂振翅的余音,仍然在寂静的白昼的空气里微微地颤抖着。
不知什么时候,雌蜘蛛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出来。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把嘴插进藏着蜂蜜的花蕊里。
几秒钟过去了,其间充满了残酷和沉闷。
在红月季花瓣上,几乎陶醉在花蕊里的蜜蜂的身后,慢慢露出了雌蜘蛛的身子。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死死地咬住不松口。蜜蜂一边拼命地振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蜇敌人。由于蜜蜂的扑打,花粉在阳光中纷纷飞舞。
短暂的战斗马上就结束了。
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接着脚也麻痹起来,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这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悲剧的结束——瞬间之后,蜜蜂在红月季花下,伸着嘴倒下来了。翅膀上、脚上都沾满了喷香的花粉……
雌蜘蛛开始静静地吮吸蜜蜂的血,一动也不动。
在重新恢复起来的白昼的寂静中,不知羞耻的太阳光透过月季花照着这个在屠杀和掠夺中取胜的蜘蛛。它几乎是“恶”的化身一般,灰色缎子似的肚子、黑琉璃一般的眼睛以及好像害了麻风病的、丑恶的硬梆梆的节足,趴在死蜂身上,使人毛骨悚然。
这种悲剧极其残酷,而且以后不知要再发生多少次。然而,在喘不过气来的阳光和灼热中,红月季花每天仍在争奇斗妍。
没过多长时间,也是在一个大白天,雌蜘蛛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似地钻到月季的叶和花之间的空隙,爬上一个枝头。在地面上酷热的空气的蒸烤下,枝头上的花苞将要枯萎了,花瓣一边在酷热中抽缩着,一边喷放着微弱的香味儿。雌蜘蛛爬到花苞和花枝之间,然后开始不断地在二者间来回往返。不久,洁白的、富有光泽的无数蛛丝,缠住半枯萎的花蕾,并渐渐地拉向枝头。
不久,一个似圆锥体的蛛囊出现在这里,好像绢丝结成的,在盛夏的阳光的反射下,白得耀眼。
巢做完以后,雌蜘蛛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儿,自己坐在上面,然后又张开类似顶棚的像纱一样的幕。幕完全像个圆屋顶,只是留一个窗子,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但是,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躺在洁白的丝垫中间,一动也不动,月季花也好,太阳也好,蜜蜂的振翅之声也好,好像全忘记了,只是专心致志地沉思着。
几周过去了。
这时在蜘蛛囊巢里,无数在蛛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最先注意到这件事的,是那只在白色丝垫上,断食静卧的母蜘蛛,它已经衰老很多了。雌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地蠢动着的新生命,于是慢慢移动着软弱无力的脚,艰难地把母与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咬开。随后,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
接着,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一哄涌上通风透光的月季的花枝。它们中的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枝之间,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还有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假如这帮小家伙能喊会叫,它们一定会在这白昼下的红月季花上举办最狂爆的晚会,让欢愉声充斥整个白昼。
此时,在巢囊里,瘦得像个影子似的母蜘蛛寂寞地独自卧在窗子前边。不只这样,而且过了好久,连脚也一动不动了。生了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伴着洁白大厅的寂寞,以及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道,尽到了作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只在酷暑之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雌蜘蛛。
入浴——一幅水彩画
——[澳大利亚]H·H·理查逊
四个朝气蓬勃的少女,叽叽喳喳像鸟儿般飞进了寂寞的浴室, 给浴室带来了朝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一幅动画的水彩画。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灼热的北风吹拂着天空,云彩被风吹成一条条的横道,带阳台的小巧的房子、闪闪发光的马路,甚至连空气本身,在炽热的阳光下和飞扬的尘土中都变成了一片白色。相比之下,浴室里显得很凉爽。浴室没有窗子,完全靠屋顶上的天窗透进光来;浴室很大,原本设计就是作洗澡房的,屋里不怕水,水泥地板略带倾斜,以便洗澡水进入渗水坑。浴室除掉一面挂着的大镜子和一张木桌子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一个很大的用锌皮做成的旧式浴池,由于每次放水的深浅不同,在它的四周留下了一道道棕褐色的水纹的痕迹。在浴池靠墙一面装有一个淋浴用的莲蓬头。莲蓬头的开关密封较差,有些漏水,水滴逐渐变大,然后危险地悬在那里,最后落进澡盆,发出一声重浊的声音。浴盆上面那旧式龙头里流出的水也令人失望,简直和泥浆差不多,而且都是温吞吞的。不过流得倒很痛快,也许它想用水源的充足来弥补它的温吞和浑浊的缺点。
今天流出的水一片通红,因为昨天夜里降了一次暴风雨,把蓄水池的浑水给搅动了。
四个少女蹦蹦跳跳地走进了这浴室,八只手全不停地忙活着;嘴里也都大声叫着:“快洗个澡!我们快洗个澡吧!”在水池子里的水哗哗流动着的时候,由于她们都想抛开裹在身上的一切东西,鞋扔得东一只、西一只,衣服也扔得满地都是。
最先准备好的是一个胖胖的金头发的小姑娘;可能因为她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她在脱衣服时比其他的人显得稍文静一些。在她们四人中有一个姑娘因为急于抢先下水,把一个结子给拉死了,一个长着棕红头发的姑娘正帮她解那个结子。
这时金发姑娘已经在浴池边坐下,摇晃着一条腿。她的皮肤非常的娇嫩,就像是透明一般,透过它可以看见勿忘草似的蓝色的血管。从她胸部往下有一道线条优美的浅沟,这沟到了下边便向两边分开,最后消失在她的雪白的胸脯上。在那里,少女的特征才不过刚刚露头。围绕着她的脖子有两道仿佛是用大拇指指甲在软泥上掐出的线条;在她的肋骨下面还有两条——坐美人的曲线——呈波纹状深陷下去,那样子很像海岸上的水波留下的痕迹。
那个死结终于被拉开了,红头发姑娘很快脱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服,她现在躬着背两手交叉抱着正向前走去。她站在那里等待着浴池里灌水,用一只脚的脚跟擦着另一条腿。相比之下,她使得她的那个棕头发的小伙伴——四人中最小的那个小姑娘,现在还像一个男孩子一样,干瘦得一点线条也没有——显得非常的黑;大家都说,红头发的姑娘一定长着一张带着雀斑的雪白的脸,而她也确实是这样:她全身的皮肤白得像雪一样,摸上去既富有弹性又像玫瑰花瓣一样的柔和。
那个拉结子的姑娘也下来了——她又高又瘦,长着一双棕色的眼睛,脸色有些蜡黄,但因为天气很热,加之她十分匆忙,脸上倒露出了一片红润。她长着一头金色的卷曲的头发,和别人相比,她的颜色显得非常丰富。她的皮肤是从淡淡的象牙色到琥珀似的颜色,在一切夹缝的地方又变得像赤金一样发红:比如像她的头发刚刚可以达到的后脖儿和她的隔肢窝下边。她那还很稚嫩的胸部,现在显得很平,现在她正把两手紧紧地交叉在脖子后边像小猫一样使劲舒展身子——只能看到一圈微带棕色的深蓝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