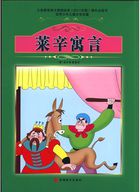她的手在他的唇上只停留了短暂的一瞬,便感到那只干枯的手不再动了,失去了温度。屋子里突然一片静寂,原来那咕咕作响的氧气的滤瓶不再作声了。时间到了!
她没有落泪,站起身来,看着那一张曾经无比熟悉、突然变得陌生的脸,慢慢抓起他的手,轻轻地贴在自己唇边。她觉得沿着手臂的桥,那个人的生命跑了过来,融会在自己身上。
她相信自己不会孤单,明天,依然会是两个生命、两个灵魂面对这同一世界。
一毛不拔的情人
——[美国]欧·亨利
百万富翁欧文·卡特在陪母亲买雕像时爱上了漂亮的女营业员梅希。
于是,他在与她第三次约会时向她求婚,而梅希却在听到他们的蜜月旅行的地点时,断然拒绝了卡特。
这是一家最大的商场,光女职员就有三千人,梅希是男士手套柜上的售货员。在这里,她熟悉了两种类型的顾客——一种是来商场给自己买手套的男士,一种是给不幸的男士们买手套的妇女。除了对这两种人已经有了广泛的了解以外,梅希还学到了别的东西。在她那隐秘而机警的脑袋里,藏着她从商场的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姐妹那里听来的种种经验之谈。这也许是造物主早就预料到的:由于她长大后得不到聪明人指点,因而,在赋予她美丽的同时,又赋予她狡黠的性格作为补救,犹如在赋予了银狐以珍贵毛皮的同时,又给了它超出其他动物的机敏的禀性。
梅希是个天生的美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举止神态安详,和橱窗招贴画上烤奶油蛋糕的厨娘一样。她站在商场的手套柜台后面,当你看她第一眼时,不禁会想到青春女神赫柏;而你再看她一眼后,又会觉得奇怪,她怎么生了一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眼睛?
在商场的铺面巡视员不注意的时候,梅希嘴里嚼着什锦果脯。一旦他的目光扫视过来,她便抬起眼皮,像凝望天上的云彩似的,脸上带着遐想的微笑。
这便是一个女营业员的微笑。见到这样的微笑,除非你久经考验,心上已磨出老茧,或是备足了耐嚼的卡拉梅尔奶糖,或是像丘比特那样天生喜欢逢场作戏,否则,我劝你还是避开的好。对于梅希来说,这种微笑只是在娱乐时才会挂在脸上,跟商场的工作不相干。然而巡视员的微笑则不同,他是商场里夏洛克式的人物。他探头探脑,四下里张望,以便寻找罚款的机会捞钱。瞅见漂亮的妞儿时,眼睛里喷射出色欲的火焰,或愣怔着眼像只木鸡。当然啦,并不是所有的商场巡视员都是这副德性,就在前几天,报纸上还表扬过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巡视员。
欧文·卡特,是一个集画家、诗人、旅行家、驾车能手于一身的百万富翁。有一天,他碰巧走进了这家最大的商场,但并不是他自己想要买什么东西——我有责任替他补充说明,他陪同母亲来看看这里卖的青铜和陶瓷的小雕像,完全是出于一片孝心。
为了打发时间,卡特逛到了对面的手套柜台。他倒是真的需要一副手套,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了。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手套柜台上可以调情取乐,所以他也完全用不着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什么。
走近他的命运女神的时候,卡特迟疑了,突然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地中了丘比特的圈套。
三四个穿得花里胡哨的花花公子,正伏在柜台上翻来覆去地摆弄几副样品手套;姑娘们咯咯地傻笑着,你一言我一语露骨地跟他们卖弄风情。卡特见状想转回头,但已来不及了。梅希从柜台后面向他投来询问的目光。她那双蓝眼睛晶莹发亮,像夏日的阳光照射在南海的浮冰上一样,显得冷峻、美丽而又热情。
荣誉众多的欧文·卡特此时感到他那贵族式苍白的脸上热辣辣地升起了红晕。他脸红并不是因为腼腆,而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觉醒。他即刻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那些站在别的柜台前向嘻嘻哈哈的女营业员求爱的纨绔子弟的行列之中的一员。他自己也靠在丘比特设下的幽会处——那橡木柜台上,想赢得一个卖手套的女营业员的欢心。他突然发现与比尔、杰克、米基他们相比,他并不高明。接着,他又突然觉得他们的行为完全可以容忍,他自己头脑中从小养成的传统观念才是最应该蔑视的。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把这个美人占为己有。
手套付了钱并包好以后,卡特没有马上离开。梅希的嫣然一笑使那粉红色的嘴角的两个小酒窝变得更深了,所有来买手套的男士们都想多逗留一会儿,卡特当然也不例外。她弯起一只胳膊,露出衣袖下面洁白的少女手臂,将胳膊肘支在玻璃柜台边上。
卡特从来没有遇到过他驾驭不了的场面,可是这会儿,他发现自己比比尔、杰克、米基他们显得更尴尬,远不及他们那样应付自如。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他没有机会见到这个漂亮的姑娘。他竭力思索着,想从以往读到过或听说过的商店女郎的故事里找到有关她的性格和习惯的记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头脑中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这些女孩子并不总是固执地坚持要通过正式的渠道才可以介绍相识。于是,他想打破常规,直接提出跟这位纯洁可爱的姑娘约会。想到这里,他的一颗心不禁怦怦直跳,然而内心的激动却没有打消他的希望,反而增添了勇气。
彼此客套了几句以后,卡特便将自己的名片递到柜台上她的手边。
“请原谅我的冒昧,”他说,“但我真心诚意地希望您给我一个再次与您见面的机会。这是我的名片。请相信,我是怀着极其敬重的心情,请求做您的朋友——希望能认识您。您可以满足我这样的奢望吗?”
梅希了解男人,特别是来买手套的男人。她没有丝毫犹豫,瞅着他坦然一笑说:
“当然,我想可以。虽然我通常不跟陌生的先生一道出去,因为那样有失女士身份。您想什么时候再跟我见面呢?”
“希望越早越好,”卡特说,“如果您同意我去府上拜访的话,我……”
梅希笑出了声,也打断了他的话。“哎哟哟,那可不行!”她随即认真地说,“您可没有见过我们住的是什么样的单元房呢!我们五口人住三个房间。我要是把尊贵的男朋友带回家的话,我妈肯定会给我脸色看的!”
“那就随您指定个什么地方吧!”痴情的卡特说,“只要您觉得方便就行。”
“这样吧,”梅希建议说,得意的神情挂上那张白里透红的脸,“看来这个星期四晚上我大概有时间。你七点半钟到第八大道跟四十八街的拐角处等我。我住在那拐角附近。不过我得在十一点之前回家,如果我十一点以后还呆在外面,妈妈会非常生气的。”
卡特感激地答应说他一定信守约定,然后赶紧朝母亲的方向走去。他母亲正在四下里张望,等他来决定是否买个黛安娜铜像。
一个细眼睛、塌鼻子的女售货员友好地瞥了梅希一眼,并悄悄走到她身边。
“那阔佬迷上你了吗?”她亲热地问梅希。
“那位先生请求准予拜访。”梅希以洋洋得意的口气回答道,同时将卡特的名片塞进衬衫口袋。
“准予拜访!”细眼睛忍不住扑哧一笑,鹦鹉学舌似地重复了一遍,颇有点嫉妒地说,“他有没有还要请你去沃尔多夫饭店用餐,然后还要亲自开车带你兜一圈?”
“嗨,别唠叨了好不好!”梅希有些不耐烦地说,“我看你还没有真正懂得怎么才叫摆阔气、讲时髦呢!自从那个消防队的驾驶员带你去过一次中国馆子,你就自以为了不得了。没有,他可没提去沃尔夫饭店,不过他名片上的地址是第五大道,他要是请我吃饭,上菜的服务员脑后决不会有辫子。”
卡特驾驶着他那电动的敞篷小轿车带着母亲离开商场时,他心里觉得很痛苦,下意识地咬住嘴唇。他已经度过二十九个春秋,却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爱情已经来到身边。而他爱上的人竟然如此爽快地提出跟他在街角约会。虽然说这是实现愿望的第一步,疑虑却将他苦苦折磨着。
卡特不认识这个女售货员,也不知道她家里究竟是因为房子小不够住,还是因为亲戚朋友多才常常显得拥挤。但无论基于什么原因,附近的那个街角是她的会客室,公园是她的客厅,第八大道则是她散步的园中小径;她宛然成为这些地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人,就像我将来的太太是她那绣房的主人一样。
第一次约会以后,又过去了两个星期。一天傍晚,卡特和梅希手挽着手,逛进了梅希那光线幽暗的客厅——小公园。在僻静的树荫下,他们发现一张长椅,便在那里坐了下来。
在这里,卡特第一次伸出手臂,轻轻地搂住梅希的腰,她一头金发舒舒服服地滑上他的肩头。
“唉,”梅希感激地叹了口气说,“你以前怎么没想到这样啊?”
“梅希,”卡特郑重其事地说,“我是多么爱你呀,这你肯定知道。我向你求婚,是真心诚意的。你现在已经对我有了足够的了解,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我要娶你,我一定要娶你为妻。我不在乎我俩身份上的差别。”
“什么差别呀?”梅希好奇地问。
“其实也没什么,”卡特连忙改口,“这只不过是那些可笑之人的愚蠢想法。我是说我有能力让你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我有无可置疑的社会地位,我还拥有大量的财产。”
“和他们说的没什么差别,”梅希说,“全都是骗人的鬼话。我看,你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个在熟食店或赛马场干活的伙计。别以为我年轻幼稚,好欺负。”
“你需要什么证据,我全都可以提供给你。”卡特耐心解释说,“我要娶你,梅希。我第一次看见你的那天就爱上你了。”
“你们怎么都用同一个腔调说话呀。”梅希忍不住笑了,“要是能碰上个人,看见我三次以后还仍然缠住我不放的话,我恐怕真的会迷上他呢。”
“请别这样说,亲爱的。”卡特央求道,“你要相信我。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眼睛,你在我心目中就成了这世界上惟一的女人了。”
“哦,你真是个骗子精!”梅希笑着说,“这话你已经跟多少个女孩子说过了?”
卡特毫不放松。深藏在这个女售货员可爱的胸脯里的那颗脆弱而骚动不安的小小的心终于被他触及到了。她的心扉终于被他的话语打开了,因为轻信恰恰是她最后的一道防线。她抬起头,深情地注视着他,冷冰冰的脸颊上泛出温暖的红晕。她像只蝴蝶,战战兢兢地收拢起双翅,似乎决心要栖息在爱情的花朵上了。从她的脸上已经隐隐约约看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在手套柜台之外实现的可能性。这个微妙的变化被卡特感觉到了,他决定赶紧抓住机会。
“嫁给我吧,梅希。”他凑近她的耳朵悄声说,“我们离开这个丑陋的城市,到美丽的地方去。让我们忘掉工作和事业,把生活变成一个永久的假期。我知道应该带你去哪些地方,那些地方我经常去。想像一下吧,一个四季如夏的海滩,海浪昼夜不停地在可爱的沙滩上荡漾,大人们像孩子一样快乐、无拘无束。我们乘船去那些海滨,你高兴住多久就住多久。在那遥远的城市里,有许多雄伟漂亮的宫殿和钟楼,里面到处都是精美的图画和雕像。那个城市的街道全在水上,你要逛街就得坐……”
“我知道,”梅希蓦地直起身,接着卡特的话说,“你要逛街就得坐凤尾船。”
“是的。”卡特脸上露出微笑。
“这个我已听说过不止一次了。”梅希说。
“接下来,”卡特接着又说,“我们将继续旅行。想去世界上什么地方观光就去什么地方观光。游览完欧洲的城市以后,我们就去印度,看看那里的古都,骑在大象上参观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那些金碧辉煌的庙宇。还有日本的花园,波斯的驼队和马车大赛,以及所有外国的奇观。梅希,你会喜欢这些的,是吗?”
“我想我该回家了,”梅希蓦地站起身,冷冷地说,“时候不早啦。”
卡特对她这种喜怒无常、轻口薄舌的个性已经有所了解,知道反对是没有用的,只好顺着她,不过,他还是感到了一种成功的满足,因为毕竟有那么一会儿,他抓住了这个任性的蝴蝶的心,她曾一度收拢起双翅,把他的手紧紧握在她那冰凉的手里,虽不牢固,但希望增加了。
第二天上班时,梅希的同事露露把她拦在柜台的一个角落里,低声问道:
“跟你的那个阔佬朋友谈得怎么样啦?”
“哦,你问他呀?”梅希拍了拍鬓角两边的头发说,“我不跟他谈了。喂,露露,你知道这家伙要我干什么吗?”
“要你登台演戏?”露露屏住气,小声地猜测道。
“不是,他才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呢!他提出要我跟他结婚,而蜜月旅行却只是到科尼岛海滩上玩一趟!小气鬼!”
桥畔的老人
——[美国]海明威
我执行任务回来,看见浮桥边那个因战火而背井离乡的老人仍坐在桥畔,疲惫的他念念不忘他养的牲畜。那天,因天气不好敌机无法上天,这就是老人碰上的全部好运了。
这是一座浮桥。桥畔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戴着一副钢边眼镜,满身尘土。
此时此刻,桥上车水马龙,汽车、卡车、男人、女人,还有小孩,蜂拥地渡过河去。一辆辆骡拉的车子靠着士兵推转车轮,在浮桥陡岸上摇摇晃晃地爬动着。而这个老人却一直坐在那里,犹如一尊雕像,一动不动。他已经没有一丝气力了,挪动一步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去执行任务:过桥了解桥头周围的情况,摸清敌人的动向。
完成这项任务以后,我又回到了桥畔。这时,桥上的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而这个老人还是坐在那里。
“你从哪里来?”我走上前问他。
“从桑·卡洛斯来的。”他说到这个地名时,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显然,桑·卡洛斯是他的家乡,所以一提到家乡的名字,他就感到快慰,露出了笑容。
“我一直在照管家畜。”他解释着。
“喔。”我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这句话。
“是呀,”他继续说,“你要知道,我在那里一直照管家畜。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桑·卡洛斯的!”
老人看上去既不像放牧的,也不像管理家畜的。我看了看他那满是尘土的黑衣服,看了看他那满面泥灰的脸颊,和他那副钢边眼镜,问道:
“是些什么家畜呢?”
“好几种,”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没有办法,我和它们分开是迫不得已的。”
我一面留神地听着是否有不测事件发出的联络信号声,一面注视着这座浮桥和这块看上去像是非洲土地的埃布罗三角洲,心里揣摩着还有多久敌人会出现在眼前。而这个老人仍然坐在那里。
“是些什么家畜呢?”我又问他。
“共有三种家畜,”他解释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一定要同它们分开吗?”
“是呀,因为炮火呀!队长通知我离开,因为炮火呀!”
“你没有家吗?”我问的时候,向浮桥的尽头望去,现在最后几辆车子也正沿着河岸的下坡,疾驰而去。
“我没有家,”他回答说,“我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家畜相互陪伴。当然,那只猫不用我担心,它会照管自己的,可是,其他的牲畜怎么办呢?”
“你的政见怎样?”我问他。
“我毫无政见,”他说,“我今年七十六岁,刚才走了十二公里,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再也无法迈动脚步了。”
“在这个地方歇脚可不怎么安全。”我说,“要是你还能走的话,你就到托尔萨的叉路口公路上去,那里还有卡车。”
“我等会再去。那些卡车往哪里去呀?”
“去巴塞罗那方向的。”我告诉他。
“那个方向我没有熟人。”他说,“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老人面容憔悴,望着我的目光是那样呆滞,似乎要谁分担他内心的焦虑似的,然后说:“那只猫不用担心,我心中有数,它没有问题。但鸽子和山羊呢,你说它们该怎么办呢?”
“嗯,它们可能会安然脱险的。”
“你这样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