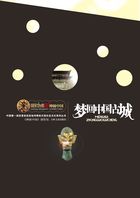征石国、灭突骑施、推翻勃特没,一连串不费吹灰之力的大胜大捷,令整个安西都护府如过年一般欢腾,处处张灯结彩,妇女们抹上了浓厚的胭脂,熊孩子们点着“爆竿”,前呼后拥,欢天喜地。都护府四周的百姓们结成长长的夹道,迎送有功将士东行赴京。高仙芝胸前挂着红绶带,一身亮银甲映得如同天人,神清气爽。队伍中段,囚车内的俘虏们忍受着沿道百姓烂菜臭蛋的袭击,他们大多闭目装睡,一身腌臜作呕的气味,对这些俘囚而言,越接近长安,离解脱苦难之日也就愈近了。
此次进京受赏的将兵约有千人,沿着塔里木河下游东行,在焉耆镇休整盘桓了一日,再向东进便走入一片茫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冬季的狂沙并不寂寞,风之伟力能卷起千堆雪,也同样掀起万顷沙。所有人都将自己牢牢埋进斗蓬,诅咒这片暗无天日的生命禁区。狂野的沙粒无孔不入的钻进七窍,让身体的每一个分子都变得粗糙。伴随着俘虏的大批死亡,高仙芝下令快马加鞭,尽早赶到前方补充饮水。
当一千多具缺水干涸的躯壳挣扎着接近水源,我瞬间便被这沙漠中壮丽的水泊绿洲所折服。狂风雕琢出月牙状的层层沙丘,万道阳光为它们披上了金黄色的涂装,如无数把金弓瞄准风来的方向引弦待发。月牙丛中,晶莹的湖泊如波斯女郎的美目,清澈深邃,动人心魄。围湖而生的胡杨林为这眼美目添上了翠绿的睫毛,令其姿色陡增。
兵士们欢呼着卸下重甲,丢掷兵器,拖着遍身沙尘一头扎进湖中。嗣业也兴奋地指着这片水域道:“到罗布泊了,老弟你不下去灌个饱么?哥哥我可先洗为敬啦!”这黑大个儿光着膀子,宽大的脚板踩出巨大醒目的浪花。
我拣了一处势高迎风的沙滩席地而坐,狂蛮的野风经过湖畔绿洲的过滤,果然清新爽朗了许多,令躁动不安的心境也沉淀下来。原来此地便是罗布泊,幼时上地理课学到,罗布泊在20世纪70年代便已彻底干涸,想不到千年之前的这片绿洲碧波如此至美,湖域面积恐有三百余里,目力所及之处绿意无垠。父亲曾告诉我,在这方神秘的沙国之中,埋葬了一位叫作彭加木的科考者,留下“去找水井”的字条便不知所踪,被地狱般的沙暴吞没。而此刻的我却是这沙漠中瑰宝的拥有者,后世人们付出生命而不可寻的水源我竟唾手可得。
兵士们在湖滩捉起了沙蟹,还有人在湖中摸到了无鳞盲眼的怪鱼。自出征石国以来,罗布泊的湖水终于洗去了连月的不快,再次体验到蜕茧重生的感觉。夜幕初降,绿洲显得更加神秘魅惑,我不可抑制地疯狂思念着阿兰,她的眼神她的灵魂,是洗净我疲惫的沙中清泉。整个夜晚,我都摩拭着那柄乌兹钢刀,从象牙刀柄上感受她的温润。嗣业仰脖咕咕饮着胡酒,抹嘴笑道:“终于开始想女人啦,好,证明你小子又活过来了!”
在静谧荡漾的罗布泊畔,我第一次梦遇阿兰,那是在一座摩天入云的高塔之上,我与她十指相扣,缠绵拥吻,身周乌云滚雷,烈焰翻腾,却不能阻止爱侣如胶似漆。只是梦到最后,阿兰的影像渐渐朦胧淡出,如一层薄雾消散在无尽虚空。我急切伸手想拉回她,竟从塔巅失足坠下……
夜半惊醒,冷汗沾湿了内衬的中衣。嗣业鼾声如雷,正睡得深沉。打着赤足披散长发,甘甜的湖水良药一般滋润我新愈的伤口,仰面浸润在罗布泊冰冷的湖面。没有工业污染的净朗天际如深黛色的丝绒,时尔眨眼的灿星将之点缀的富丽堂皇。我暗下决心,从长安返回安西之后,哪怕行遍整个中亚,也定要将阿兰寻回!
皮囊中注满了来自罗布泊的甘泉,迎着风沙又走了十多日,过阳关,宿沙洲,雄伟连绵的玉门关已横亘在队伍面前。守关大将见是高大帅的人马,不敢怠慢,对过口令之后急忙开城跪迎,用上好的羊肉和中原美酒大献殷勤,连俘虏们都喂饱了米粮。
玉门关是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门户,逾往东,帐蓬慢慢变少,汉人的檐角屋廊变多了,女人们越发婉约秀气,似乎连空气也精致起来。用隶书写成的“玉门关”三字,苍劲古朴,浑厚着力,令这座雄关愈加气势恢宏。我不禁想到了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登上城阙,穷极远眺,南侧的祁连山脉当真有万仞之险,山关相连,牢牢扼住中原的西大门。一道土砖墙,将关内关外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关外黄沙漫卷,石砾累累,只有低矮的沙棘诉说着生命的顽强;关内生机盎然,官道平整,成片的胡杨林拨弄层层绿浪。
自打过了玉门关,队伍行进的速度明显变快,车马欢骋于宽阔的官道上,沿途的州府、驿站有充足的粮米饮水供应。穿过河西走廊,从兰州近郊摆渡过奔腾不息的黄河,荒凉的塞外景致一去不复,关中地区相对平缓的地势,富庶的阡陌,正如盼儿归乡的母亲般向我们张开慈睦的臂弯。
隆冬临近尾声,纷扬的雪花似乎没有停歇的意思。已是次年一月下旬,融雪泥泞的官道上飞驰着往来递书的传令兵。成队的羽林军不时与我们相向擦肩而过,这些拱卫京师的军中骄子,银盔上佩有华丽的缨穗,身披斑澜的大氅,盛装加身,英气勃发,用我后世的流行语,应是“颜值极高”的人物。嗣业与我并马而行,未待羽林军士兵走远,便轻蔑道:“纨绔富家子弟,披上甲胄就以为自己是军人了?笑话!这一个个白皮嫩肉的,怕是连一柄陌刀都抬不起来吧。”
我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慎言,小心道:“羽林军士也是万中挑一,训练严格,大哥为何如此轻漫?”
嗣业摇头道:“日日练武与日日杀人,那不是一回事。两军对阵,对的是什么?不是武艺高低,而是士气强弱。士气在哪里?”他对我眨了眨眼,比划了一下胸口,“在心里。”
尽管嗣业压低了音量,但铜锣般的嗓子还是引起了队列末尾几名羽林军士兵的注意,驻足回首向我俩投来挑衅的目光。可这没心没肺的黑大个儿还是演说个不停:“坚如铁石的心肠是如何炼就的?是用敌人的污血,一滴一滴喂出来的!”说罢,举起陌刀向羽林军示威性的挥了几挥。几名羽林军士正欲发作,带头的百夫长估计是认得嗣业的,朝军士屁股上踢了两脚骂道:“李陌刀你们也敢惹?命不要了?赶紧给我跟上!”
嗣业将陌刀插回背带,爽朗笑道:“还算识时务!”
我明显觉察到,原先在西域苦寒之地蜇伏的兵将,待回到中原故地,一个个变得飞扬跋扈不可一世,足见在大唐戍边军人地位之高,非后世人所能想象。
“不出意外的话,午后我队即可到长安西门,晚间你便能见到父母高堂了。二老足有六年多未见你,怕是想坏了,这回呀,一定要多呆些时日,尽尽孝心。”
他一番话令我暖意融融,在杜环的记忆库中,我曾见过其父母双亲的音容,熟悉而陌生,咫尺又遥远。那份浓浓的亲情感十分异样,真实与虚无并存,无隙与隔阂交错,我无从得知,初见到这个时代的父母时,自己会如何的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