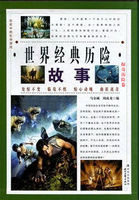周道如领着冯国璋,来到将环洲、樱洲隔开的一湾碧水前。一群衣着华丽的达官贵人、富豪商贾,正围着斗鸭池边的栏杆,津津有味地观看斗鸭,连都督来了都未察觉。
张兆坤见状,登时火冒三丈,冲到众人背后,抡圆马鞭子,劈头盖脸地打过去,嘴里边骂道:“奶奶的,都瞎眼了,没看见都督来了!”
众人这才回过头来,见到冯国璋,一哄而散,远远地躲在一旁。冯国璋紧走几步,来到斗鸭池旁。他抬眼仔细观瞧,但见斗鸭池方圆有五六丈,四周围着雕花红木栏杆,旁边摆着几个精致的竹蔑笼,每个笼里都有一只斗鸭。斗鸭池中有两只斗鸭,其中一只长着花翎,另一只长着绿头,在水中游来游去,围绕着对方转圈儿,寻找争斗时机。张兆坤站在冯国璋、周道如身后,伸长脖子,饶有兴趣地观看着斗鸭。
冯国璋见状,回过头来,向张兆坤问道:“张营长,依你看,哪只鸭子能赢?”
张兆坤琢磨半晌,犹豫不决地答道:“奶奶的,俺从小在程善策表叔的鸡舍里厮混,只懂得斗鸡,没见过斗鸭,还真说不准。”
口奥——看着张兆坤憨态可掬的样子,周道如登时来了精神,故意戏弄他说:
“那你敢不敢跟大帅赌一把?”
张兆坤瞟了冯国璋一眼,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赌就赌,赌场无大小,俺就不跟大帅客气了。”
冯国璋听罢,郑重地点点头,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就依你,咱们五十个大洋一局,你先挑鸭子。”
张兆坤露出赌徒神态,孤注一掷地喊道:“奶奶的,俺要花毛鸭。”
二人说罢,死盯着斗鸭池,再也不敢吭声,唯恐揽了两只斗鸭。此刻,两只斗鸭正拼命地争斗,绿头斗鸭伸着头,从水面上跃起,向花翎斗鸭俯冲过去,用脚蹼猛蹬对方。花翎斗鸭翻了一个跟头,扎进水里,巧妙地躲开绿头斗鸭。它绕到绿头斗鸭背后,从水里钻出来,用嘴狠命地琢对方的脑袋。绿头斗鸭虽疼痛难忍,却拼命反击,扑打着翅膀,拍击对方。一时间,浪花四溅,斗鸭翻腾,花翎斗鸭血迹斑斑,染红碧波。受伤的花翔斗鸭扭过头去,嘎嘎嘎地叫着,扇动着翅膀,在水面上半游半飞,朝远处逃去。绿头斗鸭穷追不舍,来到花翎斗鸭身后,继续拼命地琢对方。
花翎斗鸭被琢怕了,只好把脖子扎在绿头斗鸭身下,不停地蹭着,表示认输。
冯国璋见状,哈哈大笑,得意扬扬地对张兆坤说:“本大帅赢了,你赴决掏钱吧。”
张兆坤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二话没说,掏出毛瑟手枪,“砰”地一枪,把花翎斗鸭打死在斗鸭池中。他心疼自己输的钱,悻悻地对冯国璋说道:“斗鸭真没劲儿,不如斗鸡有意思,俺认赌服输,拿军饷还赌债。”
周道如回过头来,笑着对张兆坤说道:“把死鸭子捞出来,带回都督署,做个盐水鸭,好好庆贺一番。”
话音未落,褚玉璞已经扒下军装,扑通一声跳进水里,把死鸭子捞出来。褚玉璞提着死鸭子,打量半晌,没有吭声。他心里琢磨着,这斗鸭子,还真不如斗蟋蟀有意思。
周道如陪着冯国璋,一边向樱洲走,一边噪喋不休地继续介绍道:“盐水鸭是南京的特产,过几天就是中秋节,正是做盐水鸭的时候。先把炒热的花椒盐,擦到鸭子身上,腌上一两天。再把鸭子放在锅里,用文火煮熟,捞出来的鸭子色白、味美、酥嫩,好吃极了。”
两个人说着,已经来到樱洲。见树上挂满樱桃,黑里透红,煞是好看。张兆坤用军装兜着刚采摘下来的樱桃,送到冯国璋、周道如面前。冯国璋学着周道如的样子,吃了几个,果然味道甜美。
冯国璋、周道如离开樱洲,向北走过小桥,登上梁洲。梁洲岛上建有湖神庙、大仙楼、观音阁,冯国璋毕恭毕敬地上香,请求神灵保佑,让自己官运亨通,财源茂盛。冯国璋、周道如沿着湖堤,来到翠洲。翠洲长满苍松、翠柏、绿柳、墨竹,人迹罕至,空灵幽静。
张兆坤垂头丧气,暗中埋怨自己,不该跟都督赌博,白白丢了五十个银圆,心中十分后悔。冯国璋、周道如流连忘返,直到天黑时分,方才游完玄武湖,坐上马车,回到都督署,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汤玉麟送走张兆坤,马上带着第五十三旅士兵,逼着老百姓种植罂粟。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只得乖乖地听话,在地里播种罂粟籽。待到收获季节来临,远远望去,罂粟地里一片花红叶绿,绿叶衬托着火红的花朵,圆圆的浆果挂在枝叶间,煞是好看。烟农们带着烟刀下地,在罂粟浆果皮上,用烟刀划了三五个口子,让白色的烟浆流出来。第二天,他们赶到地头时,流出的烟浆已经凝固,变成黑色的生鸦片。他们用烟刀刮下生鸦片后,再次划开浆果皮,放出新的烟浆,等到转过天来,刮取新的生鸦片。就这样,如此反复,前后长达十余天。烟农把收获的生鸦片,装人坛、罐、瓮、缸等陶瓷器皿里,封住陶瓷器皿的开口,在阴凉干燥处保存起来。
又过去一个多月,汤玉麟派出一个排的士兵,赶到皇姑坟,陪着董老蔫和两个账房,收购生鸦片。烟农们闻讯,喜出望外,当即抱着自家的生鸦片,赶到收购地点。一个白胡子老烟农来到收购点,抬眼仔细观瞧,但见前面站着一堆儿烟农,密密麻麻,吵吵嚷嚷,数不清有多少人。他凑过去,挤进人群,探头探脑地向里窥视,只见地上铺着二三丈宽的油布,油布上堆着生鸦片,好似小山一般。油布旁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放着烟灯、烟枪、烟钎、算盘、账簿、杆秤等,董老蔫和两个账房坐在桌子后面,周围站着七八个士兵,个个身着灰色军服,端着曼利夏洋枪,倒也威风凛凛。
老烟农看了看董老蔫,赔着笑脸,小声问道:“掌柜的,今天是个啥价钱?”
董老蔫头也不抬,随口答道:“官定一口价,每两一块大洋。”
一个账房手拿铁烟钎子,挑起老烟农的生鸦片,放到烟灯上烘烤,用鼻子仔细地吸着烟雾,鉴别着生鸦片的质量。他把生鸦片放进秤盘里,仔细称了称,大声喊道:“四斤三两。”
账房喊罢,把秤里的生鸦片,倒在油布上。另一个账房一边把算盘打得山响,一边在账簿上记着,也大声喊道:“六十块大洋。”
董老蔫听罢,掏出六十个银圆,递给站在面前的老烟农。老烟农没有接银圆,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少不得摇了摇头,生气地说:“掌柜的,先生算错了,应该是六十七块大洋。”
美死你——”董老蔫瞪了老烟农一眼,不耐烦地训斥道:“烟钱值百抽十,交给汤大帅作烟税,只剩下六十块大洋了。”
老烟农不服,张开嘴还要争辩,一看到那七八个士兵,正端着曼利夏洋枪,张牙舞爪地盯着自己,便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他接过银圆,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转身挤出人堆儿。他走出老远,回头看了看,见没人注意自己,方才朝地上吐了口唾沫,小声骂董老蔫道:“妈个巴子,瞧你那臭德行,有啥了不起,不就是闺女靠上了当兵的。等俺闺女靠上当兵的,说不定比你闺女还强呢!”
眼见董老蔫雁过拔毛,有一个烟农当即收起自己的生鸦片,扭头就走,打算把生鸦片卖给其他烟商,多挣几个烟钱。那七八个士兵见状,马上端着曼利夏洋枪,冲上前来,抢过他手里的生鸦片,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妈个巴子,董掌柜承包了本地的烟土生意,别想把烟土卖给别人。”
那个烟农被逼无奈,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痛割爱,把生鸦片卖给董老蔫。董老蔫花了十来天,方才收完生鸦片。他先把代扣的大烟捐税,给远在沈阳城的汤玉麟送去。汤玉麟见到银圆,大喜过望,美得找不到北。有当时民谣为证:
汤玉麟,汤二虎;逼着俺们种烟土;
这个捐,那个税;弄得俺们活受罪;
啥烟狠,啥土毒;要数俺们关东土。
董老蔫和账房用油布把生鸦片包好,装在三辆马车上,由第五十三旅士兵押运,送到营口方府。方北斗见过董老蔫,收下他送来的生鸦片,堆放在里院西厢房里。
按照张兆坤的交代,方北斗在里院架起五六个大铜锅,出高薪请来几个熬烟匠,帮他将生鸦片熬制成熟烟膏。熬烟匠将生鸦片放进大铜锅里,又倒进去半桶凉水,然后点燃灶膛。他不时往灶膛里添柴,熊熊大火把铜锅里的凉水煮沸,几个时辰之后,生鸦片化在开水中,变成黏糊糊的一锅烟粥。熬烟匠拿出一个竹篦子,在篦底铺上宣纸,放在另一个大铜锅上。熬烟匠端起滚烫的大铜锅,将沸腾的烟粥倒进竹篦子里。烟粥滤过宣纸,流到另一个大铜锅里,把渣滓留在纸上。熬烟匠拿开竹镜子,点燃那个大铜锅,用文火将宣纸滤过的烟粥煮沸,直到烟粥里的水分全部蒸发,变成一锅熟烟膏。就这样,足足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方北斗方才把董老蔫送来的生鸦片,全部加工成熟烟膏。
在方北斗监视下,长工们用油布把熟烟膏包好,装进木箱里,外面写上“军用?品”字样。长工们赶着马车,把写着“军用品”的木箱,运到大石桥火车站,装上开往浦口的火车。火车离开大石桥,沿着南满、京奉、津浦铁路,直奔南京浦口而来。
张兆坤早就接到电报,嘴里哼着《十八摸》,带着卫队营士兵,等在浦口火车站。装“军用品”的火车开到站,他押着车站的劳工们,把写着“军用品”木箱卸下。他用兵舰将“军用品”木箱运过长江,卸在下关招商局码头张兆坤雇来马车,把堆在码头上的“军用品”,运回都督署卫队营营房。南京城的大帅们闻讯,顾不上禁烟戒令,纷纷赶到卫队营营房,购买张兆坤运来的关东烟土。一时间,卫队营营房大门外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仿佛闹市一般。张兆坤毫不忌讳,让史虎开张营业,大卖特卖起烟土来了。短短十来天的工夫,“军用品”烟土便销售一空,颗粒无存。张兆坤嘴里哼着《十八摸》,只顾着收银圆,忙得不亦乐乎。他留下自己应得的银圆,把剩下的银圆给冯国璋送去。
冯国璋见到银圆,两只眯缝眼变成一条线,咧开大嘴“嘿嘿”地乐了,当即对账房先生王辰说:“把大洋收好,俺打算再买一批枪支弹药,有枪就是草头王。”
张兆坤见状,忙对冯国璋说道:“要想当草头王,就得跟袁大帅学,办将弁学堂。”
嚼——冯国璋点点头,满意地说道:“你说得不错,不过别叫‘将弁学堂’,最好叫‘军官教导团’。俺封你当团长,替俺训练人马。”
张兆坤走马上任,在南京城西孝陵卫,很快便拼凑起人马,开始培训教导团第一期学员。此刻,全体学员在操场上集合,列队等候张兆坤阅操。张兆坤头戴有鸡毛掸子的军帽,身穿挂着肩章、缓带和勋章的军装,手扶洋刀,来到全体学员面前。
张兆坤站在队列前,得意扬扬,大声吆喝道:“奶奶的,有人说带兵的要从军校毕业,暗奶奶的军校洋学生,老子是军校毕业的绿林,大帅照样让俺当团长。有人还说带兵的要懂军事理论,啥奶奶的军事理论,老子的军事理论,就是几句话,弟兄们都要好好记着,要当长腿士兵,敌人来了’咱就跑;敌人跑了,咱就追!”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