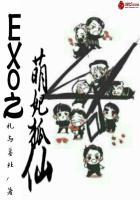醒来时已日上三竿,看了看枕边,一滴眼泪都没有,心里堵得难受。这才发现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阿伊丽见我昏昏沉沉的模样,少不得又说了我几句,便去端了解酒茶给我喝下,沐浴换衣后,脑袋又清醒了几分。北风微寒,天却是极蓝,满目的草原已经是一片金黄的草色,这才恍然我来到这里快大半年了。
侍女前来传话,说阏氏想见我,我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单于的阏氏有好几位,想见我的只怕也只会是那一位罢了。
我问道:“姑娘可知阏氏为何要传唤阿欢?”
侍女颔首低眉,笑道:“姑娘去了便知道了。”
想来也是问不出什么,阿伊丽便将人好生接待着,替我装扮起来,十分紧张庄重。我见她紧张,便宽慰道:“不过是普通传唤罢了,不用如此紧张。”
“哎呀,你可是第一次见阏氏,怎么能马虎!”阿伊丽手里的衣服挑来挑去,全然没有将我的话放心里,指着手上的衣服道:“你看,哪件好看?”
我笑了笑,从箱子里翻出了我的汉服来,淡蓝长衫,下面绣着百花蝶舞,又挽了个汉人发髻,别了海棠花簪,乌云鬓发倒有几分长安女儿的模样了。
这些,该是她怀念的吧。
侍女见了我,一刹那有些愣住,很快便正色领我去见了阏氏。虽有失神,却反应灵敏,也没说这着装不妥,一言不发地领着我,到叫我心中添了几分忐忑,不知阏氏找我究竟是何事?
行至营帐前,侍女前去通报,一个四十左右的嬷嬷从营帐里出来,见到我却愣了神,眼中氤氲出好似云雾般的泪,旁边的侍女推了推她的胳膊,方回过神来,使劲眨了眨眼,嬷嬷微笑抬手道:“姑娘请。”
营帐很大,华贵又美丽,炭火在一边静静燃烧,我一走近觉如春天般温暖,心里却不敢半分懈怠。
果然是她!她着乳白锦绣装,四周绣着少量的鹅黄色梨花,鬓发简单挽起,珠玉首饰近乎没有,那些俗物在她身上好似是一种亵渎。坐在毡垫上,轻轻煮着茶水,眼眉处带着些许落寞冷淡,却莫名给人淑和温婉。
嬷嬷低声在她耳边道:“主子,人带来了。”
她没抬头,手里正在洗着茶具,随口嗯了一声。
我也不知该用何礼来见她,便用了汉人的礼节,叩拜道:“民女见过阏氏,阏氏万福安康。”
她抬了抬眼,眼睛在我身上留恋了片刻,又低头倒了茶,水注缓慢注入杯中的声音格外缓慢,她放下茶壶轻声道:“起来吧。”
我这方才起身,看着她娴静雅致的模样,每一个动作如行云流水,潇洒沉静。
她指着面前的位子,对我微笑道:“过来坐。”
我从善如流,跪坐在她面前。
阏氏对身侧嬷嬷道:“你让她们都下去吧,我和她说说话。”
嬷嬷依言领着婢女出去,自己守在门口处,不声不响地看了我一眼,眼中却有些泛红,我被她看得莫名其妙,疑惑地回看她,只见她很快将目光偏向别处。
阏氏递了杯茶给我,含笑道:“这是长安的翠云滴露,你尝尝看喜不喜欢。”
我有些受宠若惊,毕竟来时虽强装镇定,但还是想着该如何和这位阏氏斗智斗勇,没想到她却如此和善待我,就好像一个慈爱的长辈对待晚辈一样,见此情形,倒显得我小人之心了。我呐呐地接过茶:“谢谢。”
她瞧着我喝水,问道:“你是从长安来的?”
我点点头:“是,长安……是我家。”至少,曾经是吧。
阏氏道:“我有二十多年没见过长安了,你和我说说现在的长安吧。”
她要我与她说长安,可我都好几年没回长安了,哪里知道如今的长安城还是不是我的长安呢?见她思乡情切,我便将我记忆的长安拿出来侃侃而谈,本以为流浪这么多年,早就忘却了,一开口却发现哪里是说忘就忘的了得!长安城就像是我脑中的画卷一样,不想看见的时候就卷轴扔在角落,一旦想起来,就发现每一处时那般亲切。
“长安大道和二十年前其实也没太多不一样,只是西市和东市比以前大了许多,额,我也不知道,是听老一辈人说的,夜市开的也以前要晚,还多了许多小吃的,小玩意儿,我最喜欢逛西边夜市,因为那里有好多歌舞坊,四周种了许多的花树,四周河流淌过,季春时节花随流水,很多才子佳人对月而歌,热闹非凡……”
说了许久,嗓子干干的,我停下来灌了杯水。这才发现自己口沫横飞地叽叽咕咕讲了一大堆,我吐舌笑了笑,她递了一叠糕点,我也不客气吃了起来。
阏氏眸光越发温和,好像看着我,又不像是看着我。记忆好像回到了少女时候,还是长安的贵女的时候,声音柔和又温暖:“长安的姑娘都喜欢像你这样打扮,虽说这时下的装扮一天一个样,可这大致的模样我却还是记得。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总是和一群小姑娘一样,喜欢云锦庄的绸缎,金师傅的首饰,花姑子梳的发髻……”
她说的越来越多,记忆像开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我静静听着,嬷嬷却在一边无声哭了。说道一半,她缓过神来,低叹一声道:“人一老就格外念家,吓着你了。”
我刚想说什么,就听一个声音道:“母后还这么年轻,哪里老了。”
于单大步走进来,面庞上还渗出细细的汗水,胸前的衣服被撕开一截,有些狼狈却不减潇洒。
阏氏笑了笑,很快发现他衣服破损,嗔怪道:“你这是去哪里闹得的,衣服都撕裂了,这么大的人一点没个规矩。”拉着他的手就紧张地看了起来,“可还有哪里受伤了吗?”
于单笑道:“母亲,别大惊小怪,不过是和他们去打猎弄得,一件衣服而已,不用担心!”
阏氏无奈道:“你这孩子,你明知道母亲不是说衣服,母亲是担心你,你这些个年还没长记性吗!”
于单笑道:“我知道了,母亲,您看看您一见面就唠叨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阿欢还在这儿呢!”阏氏白了他一眼,又无奈一笑,于单嘻嘻哈哈笑着,扶阏氏坐下。
嬷嬷早已取了干净衣物来,请太子换下,我起身告退:“打扰阏氏许久,阿欢先告退了。”
阏氏笑着执我的手道:“以后若有时间多来陪我说说话,和我说说长安。”
我眼睛有些干涩,点头道:“阿欢会的。”
退出营帐,突然有人从背后叫住我道:“小姑娘!”
我回头一看,是那个奇怪的嬷嬷,诧异道:“嬷嬷怎么了?有事么?”
她眼睛红红的,似乎强忍着什么,抿了抿唇道:“殿下叫您且等等。”
我点了点头,她似乎想和我说什么,终于还是垂眸回去了。
奇怪的嬷嬷!难道我见过她,想了想,我这十几年来怎么也没见过这么个嬷嬷呀!想了半天想得头痛,干脆不想了,坐在地上揪着狗尾巴草在嘴里嚼起来。脑袋里全是阏氏温和的笑容,对子女的嗔怪,渐渐地和母亲的身影融合在了一起。心里酸酸的,我这是嫉妒了,嫉妒华英和于单,有疼爱他们的母亲和父亲,而我什么都没有……
眼睛涩涩的,本以为要落泪,揉了揉眼睛,却发现怎么都哭不出来,将头埋在腿上哼了几声,还是没哭出来,又掐了掐自己,还是哭不出来,反倒越来越清醒。索性扔了手里的狗尾巴草,苦笑起来,这一笑却一发不可收拾,笑容像长在脸上一样,生了根,发了芽。
于单见我哭笑不得的丑陋模样,堪堪吓了一跳!
指着我的脸故作惊悚道:“阿欢,你得疯病了!”
我眼神一扫,恶声道:“你说什么!你才得疯病呢!”
少不得又将他追着打一顿,他随着我去,滋儿哇乱叫的样子颇似顽童。
我们倒在金黄的草地上仰望天空,他见我嘴里叼着狗尾巴草,问道:“这个有那么好吃吗?”
我闭目养神道:“没有山楂糕好吃。”
“那你为什么老是吃它呢?”
“因为饿!”
“那我带你去吃东西!”
“不要!”
“你真是奇怪!”
“我以前老是饿肚子,也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我就喜欢往嘴里塞点什么嚼一嚼,时间久了就好像自己在吃食物一样!用这样的方法来骗骗自己,希望减轻饥饿。”
“那,有用吗?”
“没用,越嚼越饿!”
“那你还嚼干嘛!”
“不知道,可能明明知道没用,还是想试一试吧。”
他侧身看了看我,似乎想着什么,也从草堆里捡了一根狗尾巴草放进嘴里嚼,和我一样闭目养神,晒着日光。两个人不说话,只有牛羊时而传来的叫唤声,和嘴里嚼草的声音。
我睁开眼看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庞,和高耸的鼻梁,阳光洒在身上,秋风时而从我们四周吹拂而过。
我问道:“你今天去干什么了?”
他睁眼瞥了我一眼,道:“打猎。”
我道:“那你的衣服怎么都破了?”
他嚼草的动作顿了顿,道:“不小心弄得。”
“哦。”我见他似乎没心思告诉我,也没再问,只是小声道:“以后你还是小心点吧,免得阏氏担心。”
我躺正了身子,继续重复口中青草香味的动作。于单侧眼看着我,嘴角好似向上勾勒,又和我一样不言不语。
阏氏今日那句意味不明的话看似是无心之失,实则令人深思。她毫不避讳的在我面前透露出于单的四周危险重重,草原上的争斗危机,不知是何意?
我一向只顾自己,故意对这些真正争斗视而不见,总想着一旦有危险便逃就是了。现在看着于单、伊稚斜、还有大将军牧原和草原上几大首领,总是心中隐隐不安。
景帝在位时,七王之乱牵连了多少无辜臣民,我虽未能亲眼见到那场王室政变,听三叔所说便已经令我胆寒。匈奴也好,中原也罢,历来都逃不脱权力争斗,政权变更,再英明的君主也有衰老的一天,无论何等贤明的人,相信都或多或少难抵住权利和金钱的诱惑。我很后悔没有及时离开,政治的漩涡一旦涉足便很难逃脱,我已经隐隐感受到匈奴帝国不久以后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