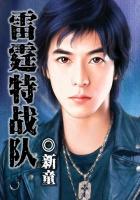“很好,”莫斯文克大手一挥,给自己的演讲做了个粗略的总结,“接下来,马扎尔同志,你来给各部队分配一下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夏亚同志,你去给我弄些汽车。”
然后凡卡带领十几个士兵,在圣约翰施洗礼者教堂和西法克斯家族墓地里,用“伟大的马列主义思想”“说服”了那些虔诚的,早早起来祷告的美国人(对此,我这个政委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提供了不少汽车,然后扬长而去。
我一直保持着对“上帝”的不信任,这种感觉加深了不少。因为他似乎并没有要惩处冒犯他信众的我们,相反,接下来的事情证明,他不仅拒绝戴着钢盔来华盛顿前线保卫美国,甚至拒绝和盟军同在。
“会下棋吗?”等待马扎尔他们回来,还没有开拔的时候,夏亚突然问我,“尤其是国际象棋。”
“这两者好像没有区别,”我摇摇头,抱歉地回答,“都是你们中国人发明的,我对此不擅长。”
提到中国,夏亚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不快,然后烟消云散了。
“这话……不像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年级第一的索菲亚同志说出来的啊,”夏亚嘟哝着嘴,“战略规划什么的,不和下象棋很像吗?”
“但我没有下棋的天赋啊……”我挠着脑袋,突然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我抬起头,错愕地问夏亚,“等等……你认识我?”
“好吧……毕竟贵人多忘事。也许你的确不太认识我了,但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夏亚脱下钢盔,向我伸出一只手,“记得毕业考试吗?我就是那个年级第二。”
年级第二……这个词……让无数的记忆,一股脑儿涌到了我面前!
“你就是那个……”我拍着手,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脑袋就被后面的莫斯文克,用手指弹了一下。
“我这边已经忙完了。如果你们想要闲聊的话,等我们用卡维利的头盖骨喝酒的时候再聊吧,”莫斯文克的语气里,毫无一丝感情,“现在的话……该执行任务了。”
此时的我们,就像是象棋棋盘上,一个红色(或者比作白色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联军是先手)的兵,直插代表黑棋方的美利坚的战场里,攻击目标,正是“黑王”。
当然,上了战场,我才知道,参谋部里的地图上摆弄几个兵棋棋子,就感受战争本身而言,远不如亲临一线那么真实。但把我们的行动,比作洛马诺夫这个曾战胜过美国棋王的家伙,对杜根进行了一步有力地将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要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同志太蠢的话……这一步,简直就是绝杀。
我慢悠悠地打开电脑,接收维拉迪摩派来的其他部队的情况。很不幸,此时其他方向上空降的联军部队,总体上简直一团糟。其他方向的伞兵已经损失惨重,除了我们这里该进行了有效(而且是极其有效)行动,其他人都是一盘散沙。
也许是觉得局势不够乱,稍后维拉迪摩又空投了新的部队。虽然吸取了教训,这批人基本上都能在预定地点着陆,但是哥伦比亚特区的军警已经反应了过来,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电台里充斥着诸如“呼叫空中支援”“请提供撤退路线”“向我靠拢”的惨叫。不用想也知道,他们一定是伤亡惨重。
虽然后续支援部队也没有得到接近白宫和国会大厦的机会。但他们倒把盟军驻守华盛顿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给了我们极好的机会。
“真是苦了在其他地方降落的同志们了。”看着莫漫天飞舞的联军白色降落伞,沐浴在即将走向正午的阳光中飘荡下来,聆听着警报声刺耳地催促声,莫斯文克感慨。
没关系。以维拉迪摩的性格,他还会空投更多部队到华盛顿,力求成为第一个占领这座城市的人。要不了多久,整个华盛顿都会笼罩在红五星降落伞的覆盖下的,这点盟军根本无法肃清所有的空降兵。
1970年8月17日,9点30分。一支由福特、大陆、奔驰、克莱斯勒等名牌汽车组成的奇怪车队,下了二四四号公路立交桥,分成五路,向五角大楼的五个大门加速前进。
莫斯文克似乎很淡定,我已经紧张得冒汗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争,也是第一次在战争问题上提出军事建议。但愿不是最后一次。
进攻五角大楼,无疑是所有疯狂的计划当中,最为冒险的一个。我们根本不清楚,五角大楼里有多少盟军(也许空无一人,也许人山人海,多得就像是要打我们一个埋伏一样),就带着两百名士兵杀过去,更像是一种毫无理智的赌博。
这么说起来……能另辟蹊径,想到绕过所有军事专家都无比重视的欧洲、中东、远东三大前线对峙阵地,直扑北美,攻击美国本土的洛马诺夫……也是在进行赌博把?
“停车!”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南门的盟军守卫想喝止我们。
一个士兵一手竖起中指,另一只手拿着突击步枪,冲对方大喊:“资本主义杂种,辛苦了!洛马诺夫同志让我给你们带来了礼物!”
“哒哒哒……”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一串子弹就从车上射出,将那守卫撂倒。直到我们撞断栏杆,冲到大门下的时候,无线电还回荡着大家对这一英勇行为赞许的笑声。
“冲进去!”莫斯文克率先蹿出来,高声大叫。要不是我拉了他一把,他恐怕要冲在第一个了。
“给我记住!”我在无线电里大声提醒,“不要再发生那种极端冒险的行为了!这与自杀无异!”
“跟我冲啊,同志们!马列主义永垂不朽!”无线电充满了马扎尔的口号,鬼知道他们听进多少。
“马列主义永垂不朽!洛马诺夫同志万寿无疆!”士兵们也激动地高呼着口号(还加了两句),沿着台阶,潮水般地涌向了大门。
守卫迅速拔枪射击。但还没来得及打倒哪个,就吃了冲在最前面的塞克卡的子弹,不再抵抗了。
枪声惊动了楼内所有人,但走廊里只有寥寥几人走出来战斗。当我目送着莫斯文克,沿着五角大楼无比宽大的楼梯冲上二楼,电脑显示,仍无成建制的盟军做出抵抗。
我观察了一下已被击毙的几个敌人。他们的外表看似豪华威武:头戴大檐帽,身穿礼服,胸前都别满花花绿绿的勋表和工作卡……
然而他们的手上,在入伍时磨练出来的皮茧早已消失,很多人甚至还没来得及拉开自动步枪的保险栓,就被我们的战士当场击毙了。
毕竟,那些手更习惯铅笔和高尔夫球杆。只有面对复杂的军事地图和娇翠欲滴的高尔夫球场时,他们还可以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
但现在嘛……枪声四起,杀声震天,个个都只能……等死了吧。
“马列主义万岁!杀光帝国主义狗杂种!冲啊!”斯拉维克挥着带刺刀的突击步枪,厉声督促后面的士兵冲锋,从我身边快步跑过。
“喂?莫斯文克同志?收到后请立刻回答!”我在对讲机里喊。
莫斯文克终于接起了无线电对讲机,不耐烦地问:“什么事?”
“有个好消息,”我翘起一条腿,得意地汇报,“有个盟军鬼子一路收编着冲出办公室的家伙,正在上楼,装备和军服都挺漂亮。七个带将星的,领头的是个美国佬,还是上将。不快点干掉他们……”
“知道了,”莫斯文克简短地打断了汇报。对讲机那边,隐约听见莫斯文克怒吼,“塞克卡同志!带一个排,跟我去杀鬼子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