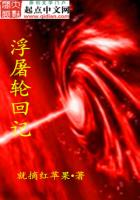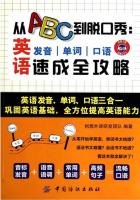周幽王末年,岐山祖地天崩地裂,天兆预示国祚将衰。谏臣赵叔带上奏天子曰:望大王体恤黎庶,勤俭理政,远小人近贤臣,借此感化天道,消弭天灾,才使社稷永续。王曰:常事,勿需惊怪。旁有虢国公石父巧言:国都在稿,宗庙亦移此,岐山废土何须多念。王曰:上卿所言甚合寡人之意。赵叔带见此黯然离朝,举族迁入晋国。时过境迁,赵叔带正气不阿、才气不凡被晋候重用,册为上大夫。数年后。其子赵无极学艺归来,见父、族老皆仕于晋,也然拜入晋室。晋候喜得意外之吉,常笑谈:晋国有上苍庇佑,能得文贤辄送武,武士不凡乃神将。
太行南端,北岭上。
皋落氏,现位戎主——太叔。接到族老数道求救的急令后,太叔带上黄父驻地中还在无忧无虑放牧谈情的小伙子们踏上了抵御外族侵略的征程。事情发生的太突然,简直可谓不可思议。皋落氏与周朝的属国晋国互不侵犯相安无事多年,排除几十年前条戎挑唆下参加对晋国先君的战争外几乎是友好的兄弟邻邦。没有间隙。
太叔及二十名骑兵比之后方的一万余大军至王垣早了一天半日。与老族长见面了。老族长说:我们的族人没有犯一丝愚不可及的错误,晋国的君称国都外的小村是我们的族人洗劫的。晋人聚集在绛城上奏,君要为民做主。晋君赍书劝我为了平息国内的怒火,要我们离开祖地,不然会派士兵驱逐我们。太叔,你说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君主吗?
面对老族长的义愤填膺,太叔沉默了。
能在北岭上山与老族长见面,可想而知王恒沃土上占着兵力雄厚的晋兵。放眼望去这间草堂外的景象,三三两两的皋落氏子民皆是面有菜色,衣衫褴褛的木然倚石或呆或泣,相互扶持。
“族老,我们的族人还剩多少?”说着话时,太叔平静中其实五脏六腑都在泣血。
白发蓬乱的老族长悲恸流泪:“二千三百一十一人。”
一声长叹。太叔咬牙切齿地走出草堂,对着青天白日,裂目痛喝,道:“炎帝啊,六千生灵就被你这样无情的抛弃,我族公室昼夜虔诚将心托付于你,结果却是这般残绝人寰的灾难!我......太叔立誓此生不绝晋国,后嗣万万代于晋人为敌,杀尽方止。”
止......最后的一字,在山间回荡着。这是丛山峻岭、草木溪流为之而悲鸣吗?
不顾族老及下属的遑遑跪谏,太叔心中对天道无情无义的冷眼旁观,几乎被脑海中的恨炎烧成冥府的恶鬼。不是几乎,他已经是了。
“等我族的勇士们赶到,我将屠尽绛城里的每一个生灵,每一个生灵!”他撕心裂肺所诉的每一个字,都似磨盘中碾碎出来的骨浆。毋庸置喙。阴寒的无一丝温度。
王垣。赵无极顶戴黄铜红边盔帽,身擐麒麟兽首战甲,绰一杆丈长青矛,胯下坐骑稀奇:碧眼、龙须,长短角。马形龙像,见者惊叹——龙马?大抵就是龙马了。鼻息进出隆隆声响,凡兽哪有这样的神威。骑将年约三十五,面白无须,眉下的眸中燃烧着是建功立业。高鼻、脂唇轻动:“君上破了黄父,戎兵回师。我必要快君上一步,杀的戎主丢盔卸甲,彰显神将柱国之道。”漠然回首,八千晋卒。持戟如林,持盾如壁,阵法井然有序。在帅纛红旗下不愧有大周北壁御林军的美喻。
君约战皋落氏小宗,佯攻。至半月,戎松懈。赵无极率晋国一师,酷令下,整装待发奇袭皋落氏部落,屠杀戎人六千,戎地积尸如山,恶鬼夜行。
黄父。皋落氏不谙筑城之法,故,只有戎主宫殿是座不高的石堡,其余戎民具以兽帐、土屋而居。姬仇掌贾、杨两国之兵暨晋国两千,合有一万之众约战皋落氏于野地。
开战之前。帅帐中,三君聚焦于军中演绎泥台上的三色军旗。四枚红色小旗乃晋军,一枚绿色大旗及一枚绿色小旗乃贾军,两枚蓝色大旗乃扬军。相对北面戎方,即八枚灰色大旗。
晋侯沉寂在即将发生的战场上,拧着上须细长的尾段,些许眯笼的银海里闪耀着骇人见之的星光。贾伯耸着黑衣衬着黄色内衬的肩头,打量着帐内四周,心中端倪着杨、晋梁君的想法。俄顷,杨君手臂触碰到了演绎泥台山的边角,发出轻微的动静。贾伯霎时掩人耳目地将泥盘映入眼帘。
静寂。漫长的使贾伯战栗不安,即刻将要“原形毕露”。恰时有一信兵掀帷而解。
“君上!”
姬仇浑身一震,回首愠色视去。眼下还好来的是信兵,如是其他的什么不三不四之流,定然不会有一个好收场。可他却也忘了除去信兵,再不可能有别人敢辄入君帐。
信兵将铜管递给晋侯。晋侯拧开铜盖,取出信皮。
观至半卷。内海之中起狂风暴雨。
“武人误国!”这句话几乎就要爆口而出,刹那。晋侯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还未肇成之际,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忍住了。
“晋侯?”贾君欲观书信,从台右走了来。
“嗯?”姬仇一愣,一边说笑:“啊,赵无极将军把皋落氏小宗一万余人困在王垣了,只要我等战败黄父之戎大事可成”,一边将书信羊皮重新放入铜管中,盖好了铜盖。
“哦”贾君不明白晋侯为何不给他看同盟中理应共享的军情,悻悻垂下伸出的右手。
台左的杨君蹙着眉头,疑惑不解。他端详着晋侯君服上威严煞气的虎纹图案,也处处透着讳言的韵味。
一只瘦而有力的大手,覆在贾伯的肩上。据说森中王者,威服林中百兽时也做过这样的动作。
晋侯道:“好了,皋落氏在黄父的军队不过都是些乌合之众,此战吾等必胜!打服了这调皮的野人可保三国百年边疆无患。”
“调皮的野人!”杨君无故嗤笑一声。晋侯随意扫过杨君,含笑着。
适才晋侯这故意大声地鼓气,并非无用之功。贾君便眉开眼笑。然,得利者贾国最甚,无怪此君将晋侯刚才的无礼之举,抛去了天涯海角。但冷静内敛的杨君心藏忧虑有增无减。他透过晋侯的眼睛看到了深深恐惧,什么事情使老谋深算的晋侯会如此表现?百思不解也。
巳时。
约战的时间到了。按照晋侯国书上开战的时间,留守黄父的皋落氏的贵族在无戎主的条件下,呼天唤地召集族内老弱妇孺二万多人合三千戎兵以全族之力抵挡此次兵灾。
战场。姬仇立车驱行至兵线阵圆处,入目之景尽数是哀国之民。这是他与尉迟咏兰所计划的战略,完全背道而驰。
“皋落氏的戎兵应该只有两千。”
“皋落氏的贵族没有交战的勇气。”
“皋落氏的戎民是乌合之众,不是哀国之兵。”
“皋落氏的战争只是恩威并施,入晋为属。”
“孤哪里做错了?......赵无极!”
细腻的风拂过晋侯凹瘦的面颊,似诒,却使晋侯心生作呕的恶心。多么讽刺,服四方戎族,争西地“天子”,本顺应天理,合乎民意。现在呢?无恶不为的暴君罢了。
“大帅,龟卜吉时在此刻,何不进兵?”
杨君一身铠甲裹身,金戈之器填补了他,近看是君主,远观是儒生的那不可自知的一幕。他所乘的是双匹轻车,战车至晋侯左侧一丈余之地,转马首面北,身立车内向晋侯作揖请示。
“攻吧!”晋侯又唐突地加话,道:“勿多造杀孽,此战为你做主,我身感急恙,回营静候捷报。”
言讫。在杨君瞠目结舌之状中,旋转车首,返向大营。
不论晋侯为何会如此狼狈不堪。然,战事不容轻视之。兵者国家大事也,轻之为祸,不可不察。
“攻!”
杨君,军令如山。一万周卒,三面攻入戎阵。
果如如传闻所言,戎兵骁勇善战。中军三千皋落戎卒于一师贾国兵甲鏖战,步步稳推贾军向后而退。左右两翼杨国两师一左一右包着戎民两万不断使其向里缩拢。战过一个时辰。方圆十五里的战场内,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战局。杨君主顾杨国之兵,故,杨卒打的戎民节节败退,胜利可期。五里外的西北处,贾国君卒浴血奋战,且战且退,已至强弩之末。若非贾君身先士卒,定住士气。那此贾国一师一旅早就罄尽元气,非要一哄而散自相逃生不可。
紫玉镶金的髻冠在兵戎相见之中,成了流落民间的宝物。天光之下,贾君所见的地方比想象的要小,看不出到底还有多少忠心耿耿的贾卒不离不弃的护卫着他,眼帘模糊中依稀所见的皆是倒地的尸体,穿着是贾国的兵服,分不清年龄,有的衣甲不全,铠不蔽体地杂乱无章地散放在乱军之中。看着像是泥人,从来没有活过的样子。粗犷马虎的贾君涓然泪下,他承认自己在国中不是一个仁德的君主。奢华荒淫、大兴土木、视民如草芥,此类昏君的品格不胜枚举。然而此刻他大彻大悟。
黑色金线点缀着领口君服的边条,华丽。身后神鹿彩绣的君服,精美。袖口条框状内画浪卷祥云,高雅。髯须一尺垂胸,夫之美也。如若不是血迹斑斑,行驶途中还发出艰难的嘎嘎声的战车。能跑的更快些。贾国之君确实是人君表率。逃不了。戎卒里里外外将贾国残兵围了三圈。戎将不会杀他,此时他已经派使者兵分两路去杨君、晋君处谈判,凭贾君之命换此战兴兵之师全部退出皋落氏的领地。这也是最好的结果,戎将如此想着。
围困之中的贾君发现了戎兵不在杀戮,旋即一想便知道了戎人的算计。一股无可按奈的屈辱,涌上心头。他目眦尽裂咬碎铁齿,四周贾卒尸体上若隐若现的亡魂,让他不禁捂住醋酸的鼻口:“你们的君主,孤若此时还投降了戎人,下一世孤必为糟糠氏。”一甩袖,泪流满面。
贾君顾盼余下的忠勇国卒,许诺道:“若能活下来。孤将会努力学做一位好君主。”
四下。心口各异,皆有怨恨的贾国兵甲,在贾君此言后,众心归一。气冲苍穹,大喝:“君待吾如子,汝待君如父,谁言要君死,先过吾此关!”
众戎人,惊而齐向后一步。
贾君凛然立于战车中,拔出君剑,以剑指天。
“杨侯,孤要不薨,杨国再无宁日!”
“杀!”
......
贾君何以至此?一路屡战屡退中,两千六百贾兵残尸弃野,尸首与鲜血从战前中军驻足处开始。战初贾国士卒就已不敌戎兵之勇,败而退后一里。彼时在晋卒眼中那是近在咫尺,然,晋国都尉尽以没有杨君帅令为由拒绝进兵。戎将见此机不可失,果断将此破绽牢牢把握,移兵止于贾兵后路,晋军目前。戎兵一面驱使,一面攻伐,一路向西北而走,贾国君兵被迫于西北,才有了之前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