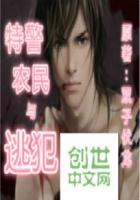河间一名的由来,出自一条贯穿半座城的青丽河道八淮河。
八淮河贯穿半座河间城,河道两岸红坊名楼如雨后春笋林立在河道两岸。
每当入夜后,八淮河两岸,锦灯赘楼,灿若星河。阁楼上,佳人如梦,端一手诗书才气、奏一曲小楼忆梦。
楼外河岸上,迎客人已招呼起一晚络绎不绝的客人。在河道里小舟上,满腹经纶苦诗的学子,沉沦于这如醉如梦的不醒世界里。
真担得一句:佳期如梦,红尘如烟。
在对岸挤出的一座小馆里,点了几道清贫而高价的小菜。这座小馆里坐的,一般都是无什钱财又流连于红馆名坊的书生弟子,偶尔来此闲坐一晚,不在酒食,只在看看对岸红坊里的佳人今日容貌。
小馆里已是屋棚满座,站无虚席。只因今夜,河对岸的知乐坊一品阁将入住一位新主...
宇文锋如一座石像般坐在二楼的一间雅座里,眉头深锁,身旁四五名女子如花蝴蝶嗅到了花蜜,贴着宇文锋不断说着甜心的话,却说的宇文锋心里生起一丝丝反感。
“嗯~好吃、再来一颗,哈哈哈哈~”问闻无言虽看不到,但左拥右抱,都刚好停在肩臂的尺度上,言词神容里表现着已经不需要说的享受,听着姑娘们的话,哈哈开口道,“别为难这位公子了,他可是出了名的冷面先生~”
“冷面先生?呵呵呵、到了这儿,再冷面的人、也叫那心儿~能被化开。”
宇文锋再忍不住,一下站起来,发出椅子挪动的声响,姑娘们受惊四散退出去一段距离,有些不解的望着男子。
无言笑笑,松开抱着的两人,平声道:“你们先去对面坐着继续聊天,我要和我兄弟谈谈事情,你们便像平常一般聊天,我没说停不许停。”
几个姑娘对这突变的状况愣了一刻,直到无言将一袋银两扔到桌上,几人如恍然大悟,立时齐刷刷坐到对桌,兴奋分着手里的银两。
待重新坐回到位置上,宇文锋也已经冷静下来,立刻明白了许多。
二楼的雅间正对着楼下的台厅,既看得到楼下,也能被楼下看的到。而此时二人坐的位置正是靠里,而女子们坐的位置正是靠外。
在离开河间府后,即使是无言也能感觉到有人的跟踪,宇文如何能不知。而先前所做的一切酒醉贪迷,乃至激怒宇文锋,到现在的假作劝解,原心里都已有安排。
“你认为昌隆意如何?”无言磕一颗瓜子,问道。
“他听到太傅之名,曾一时现出惊惧之色,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对救子恩人,留食不留宿,离开时亦未做任何挽留,这是意在赶我们。”
“当日我父亲葬身的米仓便是在此地,而他管辖着此地,府中必然有能成为线索的信息。而且,依他的表现来看,只怕藏有的,还不止普通的线索。”
“可我们如何避过他们耳目?”这对宇文来说,本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若宇文从无言身边消失,一夜不见,对方必定起疑。
“我有一计,你附耳...”无言在宇文锋耳边尽量用最轻的声音详细说完,“到时候,你只需按我说的原话,这样对她们说便可。”
宇文锋一字未回,用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目光盯着问闻无言,仿佛是今天第一次认识了这个人。
“各位少爷~各位老爷~今夜看到这么多人聚在这里,妈妈我啊、心里是暖着呢。不过,想必大家也不是为了看我才来~”一番话逗着台下哈哈大笑,待笑声平息,老鸨继续道,“大家都听说了,今夜是我们知乐坊梨香姑娘的第一次露面。这些天,大家听着梨香姑娘的曲子,想必都已经忍不住想一睹芳容...”
“行了、快点开始吧!”台下开始有人起哄道。
“好,好,好。瞧那猴急样儿~那么、有请梨香姑娘...”
外围的灯突暗了几盏,现场开始奏起一段琴木与萧竹的合乐。
从阁楼上悄声走下一女子,翠绿长裙恰剪至足裸,凹凸玲珑,手捧一张琵琶,梨黄色短发剪及肩处,目若凝水,眉似画俏,粉黛脂皮,朱唇如新摘下的玫瓣,含齿待开。下楼落足处,每一下踏踏声,敲击在男人们的心头上,令人目视处难移一寸。
梨香安坐到台上早已摆好的普通木椅上,琵琶搭肩,闭目凝息,拨弹开一铉试音。
台下收了信号,琴木与萧竹立时停下,四周静的连饮酒声都再无响起。
一段柔婉动人的琵琶曲,若闭上眼,曲乐里能听得到奏乐者浓浓的思念和凄凄的惦怀。
在无言的世界,正渐渐浮现出一副冬日厚雪的街巷图,在一处热闹的街拐角处,一个衣衫陋屡的老人坐在一处闭门的石阶上,手里正奏着一只一模一样的琵琶,另一个破衫的小女孩,卷缩在老人身边,只有一双手伸出,在手上捧着一个缺角的碗。
“琵琶本是阳曲,曲风刚硬。但此女子却奏出了琵琶凄婉柔风的曲面...”宇文锋不知觉讲了许多。
“哼!还不是仗着妈妈宠她。要不是雨苔姐姐...”
“还不住嘴!”
话音制止,听出了一些深意,宇文被勾起了一些好奇,但并未想问。
“刚才的故事,我和我朋友都很有兴趣。”无言再掏出一袋小银两,扔到桌上,道,“谁愿意把它讲完整,这银子就是谁的。”
红楼馆里虽是消息混杂竞走之地,但不同与酒馆,这里做的是门面生意,哪日来的不是贵客?若说一句多嘴,招到了哪位熟客,近了说,客人来追究,妈妈惩罚,都是说话的人一个人担,远了说,日后话若传出去,这一位姑娘的生意链就算是断了。
所以银两虽重,但愿开口的,总是那几个年小辈轻的。
“我来讲!我来讲!”小女子收了银子,整理一下开始讲道,“客官都知道,这每一家红楼坊里都会有一个头牌姑娘,一些是卖艺不卖身,一些是愿意卖身,差别不怕客官笑话,也就是赚的多少。
“而我们知乐坊的头牌,就是居于一品阁里的姑娘,而一品阁原先的主人就是雨苔姐姐...但就在十多日前,雨苔姐姐出事了...那之后不久,来了一个叫梨香的姑娘,给妈妈弹了一首曲子,然后就说了要做头牌,而妈妈就这样答应了。”
“你说十多天前这里出了什么事情?”宇文锋问。
“客官是最近才进的城吧?这些事早在城中传开了,官府都已经下过了通缉令。”
“这么说,是在通缉什么人?”无言沉思,“可否详细说说。”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就是最近几个月,这城里出了一个采花大盗,说这采花大盗,也是怪癖,不采良家女子,只采红楼馆里的女子...”姑娘叹了口气,“采花还不打紧,但此人采完花后,还把姑娘幸苦攒下的私房钱横抹一空...哪家清白女子愿意无端待在这地方,那些私房钱都是姐妹们幸苦攒下,若以后遇上一个称心待己的人,愿把自己洗清做好人家时蓄的。可是这钱无论藏到哪里,都总会被这贼狼找出来...”
“一些年纪已经大了的,知道再无力攒这一笔钱财,皆一一在屋内自刎...”另一位姑娘接过话,却是没说两句已经念不下去。
“官府就没人办事?采花贼的画像可有过画出?”
“画像是有,人也已经确定了,这都多亏了雨苔姐姐,但姐姐自己也...”小女子神容有些黯淡,“官府忙着造运河,也未听到有什么动作,只贴了画像,依旧放任这贼狼逍遥...”
“姑娘刚刚有提到造运河...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言问。
“只是听说,金沙江好像是从三个月前开始造的运河。”
“不对、不对,明明是在偷运黄金。”
“偷运黄金?”宇文锋不解。
“据人说,有人在夜里的河岸上,见到他们偷偷把一车车的东西往岸上送,在车里发着金子一样的光。”
“那哪里是金子?那是龙王的宝藏。”
“龙王的...宝藏?”无言也不解。
“听我奶奶说,那金沙江里,沉着当年龙王兴云布雨时,人们沉下的供物,其中礼教珠宝不在少数。”
“一千三百两!最后的得标者是天字三号座出一千三百两的先生。”老鸨声音听来有些激动,对着一个方向恭声道,“那么梨香会在一品阁里准备,您随时可以过去。”
天字三号座里,一男子出来靠在二楼扶梯上,一撇八字小胡,似是逗弄的朝梨香方向跳一跳。
梨香一下涨红了脸,别过头去,按安排回了房间。
宇文锋吃惊的望着天字三号的方向,似是为了辨认,又聚睛看了好长一段时间,把每个细节都看了一遍,才收回目光,侧头到无言耳边,轻声诉话。
“可能确定没有认错?”无言也有些吃惊,问道。
“若是没认错,你打算怎么办?”
无言思考良久,最后笑道:“既无要事,又何故非见不可。若是事有相冲,到时自然会见。”
无言起身,留下了三女侍寝,两人跟着宇文回了房,无言轻搂着一人去了另一间房,此意已是要在红馆过夜。
刚踏入房内,宇文便回身关上房门。
“哟~少爷真性急,这门儿才刚刚跨过去,马上就变了个性子。”
宇文锋不接话,掏出一袋银轻声放到桌上,走进了,耳语道:“今晚上我要赴一个要约,但不能让我那位朋友知道。一会儿你们在屋里演活春宫,任何人叫门也不能让进,天亮前我会回来,瞒的好,到时候还有银子。”
二人相视,马上了解的点头,微笑答道:“放心交给我们姐妹吧,保管叫偷听的人心痒一整夜。”
不在耽搁,宇文锋轻声翻出窗户,钻入大街的人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