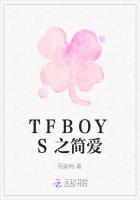德格印经院是世界上最大藏文印经院之一,几百年来无数藏教经文典藏无不出自这里。这里虽不是一个严格意思上的寺院,但是无数寺庙的经书均出自于此,信徒们相信在他们围绕高墙行走的同时,也已经诵读了印经院里经久不衰的经文。
印经院最早只是德格土司的家庙,几百年来不断的修缮扩建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轻轻走进院墙,一座博物馆的大门打开了,这里展示的并非只有近 30万块雕版这样的静态艺术品,重要的是你可以近距离欣赏动态的藏文化——藏文雕版印刷术。
一进门就是雕刻木板的师傅们,他们头发花白,坐成一排。前面是一个洗版的水池,雕刻,洗去木屑,继续雕刻。这里的经版工艺精湛,每一笔都雕琢很深,这源于德格土司的奖励制度:抓一把金粉撒在经版上,抚平,陷入文字缝隙的金粉就是刻版工人的工钱。为防止经版刻漏,土司又提出了两面雕刻,这样不但保证了作品的精度,还节约了材料。
印经院二层的一个廊厅里正在上演着真正的“印”与“刷”。一位老人身体微曲,浮在一块雕版上为其“刷”墨,另一位年轻人不断掀起纸张“印”墨,两人默契配合,指尖飞舞,一张张经文就印成了。伴随着高频的印刷,老人不断吟诵六字真言,任凭那低沉急促的声音在楼宇间回响。每一篇恢弘巨著都是这样诞生的吧?眼前看到的印刷工艺与三百年前毫无区别。
雕版、洗版、印刷、分拣、整理、装订成册……印经院中不同位置有整个印经的全部操作。回廊中陈列的雕版有的版刚刚出炉,散发着红桦木香,有的已经沉寂百年。闻着淡淡的墨香,游走在深邃幽暗的雕版木廊之间,仿佛游弋在藏族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德格与西藏只隔一条金沙江,假期将满,我不得不原路返回。
当听到从德格搭车返回成都至少需要三天时间的时候,我差点哭了。挤上一辆小面包,我被分配在了一个“加座”上——门口的一个小马扎,没有靠背,颠簸的车子一次次把自己抛向空中,和旁边的大叔一起笑。他不知道我的屁股有多开心,车再颠也比骑车舒服多了。车顶上的小红在晨光下划过了长长的影子,路一下子长了很多。几天前亲历的金色像倒叙的电影一样从车窗中静静地滑过。头顶的云如雪片般飘来,清晨的阳光透过阴霾映红了车上每个人的脸。有人已进入梦乡,一路上的美好记忆会像窗外的风景一样离我而去吗?我将再一次回到城市。
西藏骑行无疑是艰苦的,我为何恋恋不舍?只知道在这里简单而快乐,目标在努力中实现,没了都市中的种种迷茫困苦。翻滚的风马旗、草原上的歌、喇嘛的经、孩子们的笑声,还没有离开我就返回开始想念他们了。路上有人不止一次问我,为什么要骑车上路?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在北京的那栋写字楼中,我喜欢眺望窗外,繁华街道之外眼前总能浮现出这些之字形的山路,它盘旋向上,伸向天际,给人以力量。
在德格遇到了一个盖房子的工地,男人们在房顶上唱歌打夯土,女人在下面运土,场面热烈非凡。一个藏族姑娘吸引了我的目光,运土间歇她突然停下来立在一个土堆上抬头仰望着蓝天。她就静静地立在那儿,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背影真美,猜想她一定是在憧憬什么。一种久违的美妙的感觉!一次又一次骑车上路,也许就是因为在路上,我找到了这些久违的感觉,憧憬与经历,平静与坦荡,燃烧与跳动!
独自骑行无疑是孤独的。在去炉霍的路上,路边一座大山直亘云天,伟岸的山脊光滑得像大地的臂膀,上面长了一棵树,只有一棵。突然觉得那个树就是自己,呆立在那儿看了好久。广阔的高原上只有你和你的朋友——影子,白云翻滚,大地起伏,河流绵延,雪山耸入云霄,风声响起,突然发现其实你并不孤独,整个天空都是你的。
路在脚下,勿多言,去感受。
一万公里寻瓜记
文/郑乔尹
我跟在那个男人的身后。他很高,一米九是有的,长得高的日本人是对我们传统思维逻辑的挑战,可是他确实很高。长相也不是标准日本人的长相,不是电视里那种喊着生硬的“嗨!呦西!大大滴花姑娘”的日本人,反而像我老家的某位邻居。那位邻居大叔秃了半个脑袋,发型跟走在我前面的这位日本大叔一模一样。一个人在外面久了,会觉得周围很多人跟故乡人很像,无论他们是欧美的大个子,还是东南亚的小个子,一举一动,甚至不经意的一个眼神或一个表情,都能令你想起记忆深处的故人来——原来地球上的人大同小异。
我瞅着日本大叔的后脑勺,跟在他后面。我们走在京都的大街上,他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而几天前,我还在巴黎。
我决定来日本是因为夏天来了,巴黎的夏天最不像夏天,最高温度都不足以出汗。国内的朋友说我疯了,热得要命的暑天,不好好在凉爽的地方待着,跑到东亚来出汗。其实他们不懂,“热得出汗”也是我记忆里故乡的一部分。说了这么多,理解我的老友肯定会赞同说一句:来日本玩就玩呗,找那么多借口干嘛?
他们果真是最了解我的。
于是我今天跟在日本京都的一位大叔身后,两人穿梭于京都市区的高楼间。太阳浇火似的浇在身上,街上不见几个姑娘,日本姑娘们对阳光避之不及,早躲好了。商店里到处是卖美白产品的商家,跟巴黎不一样,巴黎卖“让您拥有古铜色肌肤”的各种霜啊膏啊,我要是找美白产品,朋友们会不解:脸白得跟屁股一样有什么好看?
大叔拐了个弯,我也跟着拐弯。这条街上,人流稀少。
说起来日本的签证,因为是在巴黎申请的,所以手续跟国内不一样。但我的银存款不够,日本使馆里迟迟不发签证。离机票上的起飞日期只有几天了,绝望际,我忽然收到一笔可观的稿费,签证立马媚兮兮地飘到我面前,赤裸裸地躺着上面印满了樱花,有一朵刚好在我照片的额前,看上去有点儿怪模怪样的美感我整理好行李。因为是夏天,行李不多,再者,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手续我很熟悉很快登上法航飞往日本的飞机。飞行过程比飞往上海多了一个小时,十几个小的飞行,到东京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可惜旅馆工作人员对我说:“旅馆只能下午三点后入住。”他们很有礼貌,即使执到令人发指,也还是很有礼貌,“不行啊,规定下午三点后入住,真的很抱哟。”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夏天的东京街头,晴天,中午,阳光极其好,空气有烤章鱼丸子的油味、味噌汤的酱味、牛肉饭的肉味……而我像一条移动的腌鱼拖着发臭的身子在阳光下寻找栖身之地。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下午三点之后我冲入旅馆,洗去旅行的风尘之后,天慢慢黑了,东京的夜景清晰浮出夜幕。曾问朋友:“东京的市中心在哪里?”他稍有惊讶,答:“东京哪儿都是市中心啊!"
我选的是池袋的一家旅馆,入夜后,不喜阳光的日本姑娘们一个个都出来了,虹灯闪得到处都是,广告铺天盖地的,不放过任何空隙,令人视觉疲劳。我以经过一天的飞行,会轻易入睡,结果强悍的生物钟让我时刻保持清醒,时差停在巴黎时间。我料想东京的夜景会美过日景,于是凌晨两点后,我走上街头。
这时,我收到约翰的一条信息:帮我带个“油八里”。
我问:“‘油八里’是什么?”
他说:“是一只瓜。”
“这只瓜的名字叫‘油八里’,还是有个品种是‘油八里’?”
“是瓜的品种。”
约翰是这样一个人。他曾到过上海,对上海南京路某家包子铺的包子念念不忘,于是在我某次回国之际,他要求我帮他带一打包子,南京路那家包子铺的包子。我觉得这需要很高的技巧性,包子铺只在早上开门,而飞机是午夜的飞机,时间又是夏天。我必须在买好包子之后,冷藏好,送往机场的途中还得通风凉爽而使包子们不变质,放入托运行李后得让它们不受挤压,但谁也不能保证,经过十二个小时的飞行后,包子是否还能保持原样。即使保持原样也不能保证不变质。
而这次,我来日本,他要求我带个瓜。我非常简洁地说:“带不了。”
他说:“拜托。”
“真带不了。”
“比包子好带。”
“瓜长得像炸弹,万一被海关怀疑,我完了。”
“借口。”
“东京夜里两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
“时差没那么快倒过来,你不是在街上么?我听到汽车的声音。”他又说,“如果帮我带个‘油八里’,我请你去坐地中海邮轮,玩10天的那种。”
心动,不免也好奇,又问:“这瓜有什么过人之处?”
“很有名的,巴黎米其林三星饭店都用这瓜,一定很好吃。”
我的日本之旅计划是东京五天,然后坐新干线去京都,玩五天后,从大阪机场接飞往巴黎。这是我在东京的第一夜,旅行计划不会因为一只小小的瓜而有什变化,我打算等天亮去超市找找看,而寻瓜的过程中却逛到了著名的东京歌舞一条街。我是忽然觉得来到了非常热闹的一条街上,到处充斥着浓浓人间烟火的饭馆酒肆,灯很亮,异常地亮,突然就有三两顶着超级赛亚人发型的男女出现踩着被酒精浸泡得发软的脚步,游魂一样飘过身边,跟平常所见的拘谨的日本完全不一样。他们叫着,跳着,累了就倒在地上,吐得一塌糊涂。有个黑人路两女孩身边,拉拉扯扯的,女孩不愿意,他又转向其他女孩。有拉客的女孩使拉住一个白人男子,那阵势是不将他拖进店里不罢休。我像是闯进了一个禁区隐隐觉得这里大有巴黎Pigale红灯区的风范,莫不是来到了传说中的“牛郎街”我抬头,头上一个闪闪发光的匾,上面写着“歌舞伎町一条街”,这个牌匾像是界线,里面的醉生梦死,外面的清冷寒凉。我奇迹般地从池袋走到东京边缘,日本的治安是不错,这又让我想起日本人的“巴黎综合征”,大多数来巴黎旅游的日本人会得这种心理病,理由是“想象中的巴黎与现实的巴黎完全不一样”。没错,三更半夜在巴黎街头乱逛,丢一个包一部手机是小事,没出人命是大幸,而东京无此顾虑。东京在凌晨五点后慢慢安静下来,我坐在旅社窗前,祈祷自己已经适应时差,能够在白天给约翰找到他梦寐以求的“油八里”瓜。不幸的是,一觉醒来,又见东京夜景。
这是我在东京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第二天,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晚上带我去看烟花。朋友叫小淼,人称小淼兄,来日本已有数年,偶尔会漂洋过海给我寄点日本小产品,什么面膜眼膜化妆品,还有法国没有的眼药水。上次给我寄了一包眼药水。包装特像安全套,上面还有两个汉字:“超爽”!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