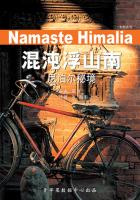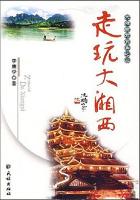文/笨鸡
马尼干戈,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决定来这里了——这是位路上驴友说的话,我深表同意,马尼干戈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奇妙而美丽。
马尼干戈,海拔4000米,是雀儿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古道驿站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今它依然是三省交通要冲。小镇向北去青海玉树,向西进入西藏昌都,向东回成都。骑车赶到这里时已近傍晚,一路上饱览甘孜金秋的胜景爬上藏东高原,来到这里反而特平静,柔和的落日投在孤零零的路牌上。左手入藏,右手进入青海,车把左转。
像藏族聚居区很多城镇一样,这里实际上比我想象的还要小很多,三叉路口边只有一排小房子,房子反射的光在夕阳下变得温柔模糊,让你很难寻找它过去的记忆。与昔日的马帮车队相比,在这里见到的更多的是中途休息的货车,不变的依旧是那份宁静与广阔。
马尼干戈我住进了一家叫作“帕尼”的酒店,外面看是一座二层的藏式楼阁,实则一栋现代工艺的水泥楼。帕尼就是这家酒店的老板,是个矮墩墩的藏族汉子,敦实厚道,笑容可掬。
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三个年轻人:一对成都来的年轻夫妇康康、小幺和另外一个女孩小面。可能是一路上太久没有和人说话了,我厚着脸皮凑过去跟他们聊天,他们干脆把我叫过去一起吃饭。菜是相当地道的川菜,米饭是帕尼大叔用粗瓷碗蒸的口感极佳。我的胃如同搅拌机一般发动了,面前很快堆起一摞空碗。从甘孜县城过来我差不多骑了100多公里山路,三个背包客头一次见识了骑行者的胃口。
小面有点儿轻微的高原反应,胃口不好,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一阵羡慕妒忌恨。帕尼大叔走过来指着她手中抱着的氧气罐说:“千万别吸。”一边指着楼上,“那边有几个广州来的也是高原反应,劝他们不要吸氧,他们不听,一个个抱着氧气罐子猛吸,你们看着吧,他们明天就得原路返回。”小面一脸错愕。“上高原不舒服是正常的,急于吸氧破坏人体的免疫,反而会对氧气有依赖。”大叔目光温柔,慈爱得像个父亲。
晚上,马尼干戈停电了,院子里的柴油发电机隆隆作响,我搬到了他们的四人间,屋中空着的那张床好像是专门为我预留的一样。高原上的深秋之夜冰冷刺骨,四人躺在房间四角盖着双层被子,像是盒子里码好的寿司,蠕动的“寿司”们开始聊天,好像是回到了大学宿舍中的日子。
小幺三个人刚刚从色达回来,五明佛学院就藏在那里的一处山谷之中。五明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佛学院附近的山坡上搭起了木屋。日积月累,一座座红色的木屋连成了片,沿山势流动的红点密密麻麻地环绕着佛学院的金顶,感觉仿佛到了世界的另一端。偏远的地方有幸免于现代的侵蚀,色达、白玉、新龙……几个人想方设法往山沟里钻,我对此亦心有戚戚。
闲聊中小面透漏了一个秘密,小幺和康康居然是在藏族聚居区旅行中认识的,让我感慨那里的山神真的会惠顾这些真诚善良的孩子,几年前川藏南线的骑行路上,一个孤独的女孩。一个落单的男孩,两个人均被不争气的同伴抛弃,偶然在一县城相遇,然后结伴同行,最后与我们的队伍一同抵达圣地拉萨。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周岁了,上个月还收到了他们发来的照片。当时男孩在南京,女孩在武汉,如果不是这条神奇的路,谁会想到他们今生会在一起度过?小幺和康康则是在亚丁相遇的,两人一见钟情,康康说见到小幺就心跳加快、头晕目眩,奇怪这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的魔力,后来才知道是犯了高原反应。
据康康说他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丝骑车去西藏的打算,但家门口的一次远郊骑行让他彻底放弃了,半天下来他的屁股就摩红了,而且蛋疼得厉害。他觉得我们这些骑行者都是异类,是受虐狂。他说:“给你讲个笑话你别生气。我去稻城的时候看到客栈墙上有句留言‘你这个傻逼,你为什么骑车来稻城!’”我哈哈大笑,多像是写给自己的一段话。
我接着说自己曾在网上写骑行西藏的日志,朋友看过之后我就问他:“本人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是否高大了很多?”他摇摇头,“一点儿没有,你一个人在山头上骑车,还下冰雹,下大雨,让朕一下子联想了到天涯歌女,实在太可怜了!”几个人笑得都缺氧了。清晨,走出旅馆,对面的山坡上一群牦牛迎着太阳向东迁徙。红的狼毒,金的草,脸上暖暖的阳光,一切都让人觉得那么地安静与自在。
远远地听到一群孩子的叫声,抬头向平缓的山坡上望去,这里有一所希望小学。孩子们正在课间休息,不大的操场上一群人打成一片。几个男孩子在玩“赶车大炮”,两个人驾起一个活人当大炮,中间的人用双腿发动火力袭击对方。欢笑声夹杂着一阵腿脚相击的声音,草甸子快要沸腾了!看我手里拿着相机,为首的小伙子第一个跳了下来,胳膊还被两个人驾着。看他没正形冲他紧了下眉,小伙子像是想起什么了,嗖地从兜里掏出了红领巾戴上,挺着小胸脯,像个小战士。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挥挥手,小麻雀一样飞回了教室。一个班的孩子正在上藏语课,能清楚地听出发音,却听不懂他们在读什么。悄悄地走到门口,和美丽的老师四目相对,老师笑了一下又继续上课了。
希望小学孩子们齐声朗诵课文,张大的嘴像是嗷嗷待哺的鸟儿,眼神中充满了渴望。那读书声冲破蓝天,飞跃草原。不知是老师的背影还是孩子们的眼睛打动了我,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自己上学时候的样子。学校操场的围墙画着漂亮的黑板报,藏汉文与图片,那么新鲜又那么熟悉。
离开学校的时候,孩子们一张张的脸庞又一次浮现在面前。当时是在给一个孩子拍照,一会儿两三个孩子冲上来,一会儿又过来四五个。很快,镜头前就聚集了一个班的学生。孩子们的笑脸仿佛是阳光下盛开的格桑花。
突然,小班长喊了一声:“敬礼!”
所有的小手齐刷刷地伸向了蓝天。
那一刻,很意外。
抬起双眼望着蓝天,呆了,天空湛蓝如洗,连云彩也在跳着绮丽快乐的舞蹈!马尼干戈的孩子们,你们快乐地长大吧,这里的明天是你们的!天高云淡,那读书声似乎还在耳畔回响,通向雀儿山的路却已经开始了。深秋的风景很迷人,多姿的云在柔和的山峦上留下了斑驳的影子,大地的一切都被金色的草原包裹着。踩着单车,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与今早上看到的一样美丽,只是云朵的形状变了模样。
康康他们的包车追上来了,比他们早起很多结果还是被追上了,骑行者不可避免的悲催。康康跳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我,里面装着酥油茶,火热的瓶子暖着我的手心儿。“加油哦!”还没喝,心里就被暖流袭击了一下。三个人的车消失在了公路的尽头,此行再没有见到他们,如果旅行不意味着告别,那它或许就不是旅行。
金色的草原上点缀着牧民的房屋,屋檐在晨光下熠熠生辉。雪山出现了,宽阔的大山张开了臂膀,车轮呼呼作响,前面就是雀儿山吧?
雀儿山下藏着一个海——新路海,新路海边的一条小溪让人眼前一亮,高高的公路上可以一览它的新路海全貌:溪流中无数块巨石上都刻着六字真言,大大小小的“六字真言”似与溪流共舞。
六字真言:藏族民众祈往极乐世界所唱的六字圣歌。转山的路边,玛尼堆的石头上,你看到的就是六字真言,转经老人口中,磕长头信徒的心中,也是六字真言。六字真言充满了整个藏族聚居区,无论那里多么偏僻,多么荒凉。它告知你信仰的存在无时无刻,不论空间。
在新路海的售票处卸下托包请售票的藏族妹妹帮忙看管,没想到买票的时候她挥挥手说你直接进去吧!踩着空空的单车来到湖边,静静地坐在草地上,一切繁杂的思绪都会变得像湖面一样平静,湖面光亮得像面镜子,雀儿山的秋色倒映其中,水中与天空中的云一齐缓缓移动。新路海藏文名字叫玉隆拉措,意思是心为湖倾倒,传说英雄格萨尔的爱妃徘徊湖边流连忘返,她的心永沉湖底。“新路海”的名字是当年十八军修路的时候留下的,海子正好在新修的公路旁,所以就有了新路海的名字。如今的川藏公路已绝非新路,但名字却依然如故。有人喜欢叫它“心路海”,妙极了,甩开路上的颠簸劳顿,静静矗立湖边,一定会有不少心路体验吧?新路海之后公路急转直上,山风很大,手心却在车把上攥着热汗。雀儿山,我来了。
雀儿山有川藏之巅的美称,藏语叫“措拉”,意思是大鸟羽翼。雀儿山之名给予人们更多的想象,山峰太高,即使是雀儿也难以逾越?
山路盘旋向上,山谷里倒灌着阴风,路越走越荒,里面的衣服已经湿透。呼吸急促,头有些晕,心里发慌。眼前突然浮现出那位老司机,老人面带焦虑,充满了关爱。我们是在帕尼酒店里碰到的,一帮登山的驴友包了他的车去新路海上的雪山穿越去了,几天时间还没下来,老人在客栈一楼的餐馆喝着茶等那帮驴友下山。
他指着我停在窗外的单车问:“你一个人来的,骑车啊?”
“是啊!”
“哪里去啊?” “德格”。他眉头紧锁,“你一个人骑车太危险了,前面就是雀儿山。”他把手臂举得很高,连连摇头,“雀儿山太高了,天气不好全是雪。”我被说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呵呵傻笑。
雀儿山等自己扛着车上了客栈的二层,发现气喘难耐,喉管干裂,还一阵眩晕。山脚下就有反应了?心里开始打鼓……
前方的路还在继续,深呼吸,抛去杂念,伏地向苍凉的大山前进。当你用心去触摸这片天地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融入其中,行走其间,心靠向天际。身体在冷风中冒着汗,似乎找到了一点节奏。
公路在山腰上拐了一个大弯,山中怪石嶙峋,除了深色的地衣,似乎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一座公路道班夹杂在苍凉的山谷中显得冰冷无比:雀儿山的四道班。还记得几年前第一次骑川藏的时候,理塘高原有绵延几百公里的无人区,七个伙伴走投无路投宿道班。暖暖的炉火,牦牛肉炖萝卜汤一下子驱走了身上的寒气,如果没有那个道班,可能真的呜呼了。漫漫川藏路上一座座公路道班透着暖暖的人情味儿,它们散落在山麓两侧,像是银线上的珍珠,又像是一个个期待达成的目标。在距离四道班不远处,碰到了道班里施工的工人。从新路海开始公路已沦为土路,路面经过大车碾压出现了许多大坑,需要常年维护。工人们正在用铁锨平整路面,他们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的路人,打起招呼来都是四川话。他们家都在四川内地,老婆孩子也留在那里,自己却把青春献给了雀儿山。道班工人中有个藏族小伙,脸庞黑瘦硬朗,叫次仁当知,他的家就在山下的新路海,他是众多人当中离家最近的一个。次仁当知用流利的川普跟我说现在还好,再过几天山里一下雪,清理路面的任务就重很多了。雀儿山交通中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拐过了那个大弯不知骑了多久回望山谷居然又一次看到了四道班的工人,他们已经变成了小蚂蚁。停车大喊,声音融化在大山中没有丝毫回应,咫尺天涯!
时间在转动的车轮中不断地滑过,我如乌龟般一点点地挪动。黑云压顶,冰雹砸下来了,冲锋衣噼啪作响。把头埋在帽子里,一阵阵豪情万丈冲上心头,保持踏频继续向前!回首之间,山坳里居然升起了一条淡淡的彩虹!下午五点,身体极度不支的时候看到了那熟悉的经幡,它随风舞动,召唤我一点一点踩上垭口。今天我只吃了两个馒头,一碗稀饭,还有康康送给我的一瓶酥油茶。
成都司机大叔,我上来了,一切安然无恙。
垭口海拔5050米,脚下正是四川公路最高点。站在山口向西藏的方向眺望,横断山脉如战士般排列成行。几年前曾经从那些千沟万壑中骑行穿越奔赴梦想圣地,再一次看到这一排排的山脉不禁要落泪!垭口一侧是英雄的五道班,五道班把最高的山头留给了自己,这里夏天睡觉也要盖棉被,冬天又常常大雪封山,积雪齐腰。五道班出了一名全国劳模,已经60岁的藏族大叔陈德华,据说他在这个山头上已经干了将近30年。正要进去拜访,一位大哥走出来冲我嘿嘿一笑,说劳模去北京开会去了。
山上还有亮光,一路冲下山,山的南麓是一片开阔的山谷,森林繁茂,景观大不同。路边的山窝里有座很不起眼的墓碑,墓碑上写着三个字——张福林。 1951年冬,十八军的战士们还在为打通进藏的最后一道屏障——雀儿山而昼夜奋战。有位小炮班班长,他不顾高原缺氧和贫血带领全班连续爆破作业,准备打开山路最后一段险阻。一天中午,他在工作中突然被一块坠落的巨石砸中,鲜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高原。他就是张福林,据说川藏公路每一公里就埋有一具忠骨,张福林只是他们中的一员。
战士们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他的衣兜里有几包菜籽,这是他进藏前买的。年轻的战士还想着开通公路后,在高原播下种子让大家吃到新鲜的蔬菜呢。那年,他只有25岁,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已经子孙满堂了吧?天色越来越暗,最后彻底黑了。山风作响,顷刻间下起了暴雨,雨水冲刷着双眼继续前行。
这路修得实在太不易了,传说中鸟儿都无法逾越的雀儿山如今已经变成了通途。心中的孤寂感荡然无存,好像燃起了一团火。黑色的树影飞快地向背后划去,沿着河谷飞速向下奔腾,朦胧的山影后好像看到了几代筑路人的身影。雀儿山南麓的谷底就是德格。德格是藏族聚居区文化的中心,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乡。雨过天晴,古朴的木屋成排列在山上,水洗一般,连空气中都透着清新的味道。
昨夜那阴森的山谷中,黑云遮住了最后的一丝月光,奔腾的河反衬出死一般的寂静。树木的黑影形成了深邃的黑洞,似乎要将我吞噬,车轮卷起的泥一片片摔打在自己的脸上,发出“啪啪”的声音。赶到德格已是子夜时分,旅馆中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乐了,身上、脸上全是泥,泥巴风干后形成了坚硬的壳,才知道为什么前台的妹妹见到我一脸错愕。川藏北之行以雨路夜路开始,以雨路夜路收尾,行程圆满。记得第一天从丹巴出发,顶着濛濛细雨在长长的山路上骑了一整天。那天是八月十五,登上山顶时圆月升起,映照着羞涩的雅拉雪山,静静地感受大地的苍凉与温暖。第一天以凄美开端,最后一天则以凄惨结束,不幸被朋友言中。
德 格清晨,与虔诚的信徒一同来到德格印经院,人们如涌动的潮水一般围绕着印经院行走,这是在藏区常见的场景:身体沿着庙宇顺时针轮回,手上经筒旋转,念珠滚动,还有那由远及近的共鸣喉音——唵嘛呢叭咪吽。据说围着印经院绕满一千一百一十一圈就修行圆满,民众们正在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