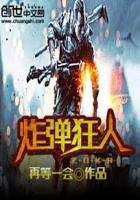八十米、四十米、二十米……
我在心里计算着距离,深吸一口气,跨出一步张开双臂,横挡在小路中央。足尖前方传来自行车急刹车,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车上的男生抬起好像没睡醒的、委顿的眼皮,吃惊的表情只在他脸上停留了数秒,很快就转为漫不经心:“你干吗?”
我的英勇忽然泄了气,声音中暴露出我的胆怯:“为什么你……不再去音乐教室了?”
卫柏丞微微愣了愣,随即不客气地说:“关你什么事?”
也对呢,在他看来我只是个陌生人。我鼻子一酸,强忍伤感问:“你不去练琴,是因为我送的卡片和饼干,惹你厌烦了吗?”
柏丞“啊”一声,眼里的神色变得有些不同,终于认真看看我,说:“原来那些是你送的。”
从音乐教室的窗口望进去,视线最深处,是一台庞大的三角钢琴,端坐在琴后的男生露出小半张脸,柔和的光点就在他的鼻尖、嘴角、额发上跳动。
琴声有些断续,他不时停下来思考下一段旋律,在纸上涂写着什么。
我在教室门边张望了一会儿,生怕惊动到他,轻轻放下袋子里仍然温热的小饼干,蹑手蹑脚地离开了。
同样的事,一连做了三个晚上。忽然有一天,卫柏丞不再出现在那间教室里。
纸袋内除了饼干,还有手写的小卡片,上面是我小心翼翼的告白。
“其实,你不必那么反感地躲开我,”我为自己冒失的举动深深懊悔,眼角渐渐潮湿,颓丧地低垂着头,“只要你向我说明,以后……以后我也不会再做令你困扰的事了。我……”
突然头顶一重,有只宽大的手掌轻轻盖在我的头上。或许见我哭得伤心,卫柏丞嘴角添了少许温柔之色:“你听过雪人和火炉的故事吗?”
“窗这一边的火炉和窗那一边的雪人陷入了爱河。
火炉看到雪人终日戴着围巾帽子,以为她很冷,总是拼尽全力地燃烧,想把温暖带给她。而雪人,见到火炉烧得那么痛苦,便常常把自己身上的冰雪分给他。后来,雪人过早地融化,火炉也把自己烧坏了,成了废弃品。”
柏丞说到结局,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无限唏嘘。
我一直不懂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是在嘲笑奋不顾身的爱情有多么愚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