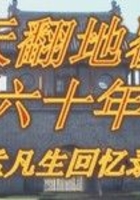在大年三十到来之前,艾姬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随便抽个时间来我家里一趟。我没有主动邀请她,她也没提出来。这让我心里总是无形地生起了某些疙瘩,但我能默默忍受;也许是她的家人把她看得太紧,没有机会。当然,虽然我偶尔也想过把阿吉带回来让母亲瞧瞧,但是我最终没有将此念头付诸行动。母亲觉得自己的愿望渐渐化为了泡影,也不再过问我女朋友的事。她可能觉得儿子不一会儿认识一个女孩子就说是自己的女朋友在她看来那只不过是年轻人的游戏而已,这不能太认真!何况儿子并非什么大龄青年;更何况儿子还有她从小就钟情的绘画理想。
尽管如此,但是我还是从母亲的脸上看到了一些不少失望的神情;这种也许是天下所有母亲就该有的期待神情千百年来一直没有中断。二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他们的身边,若是有幸让命运把我弄到别的城市或别的地方读书,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别离之情何能相比。不知道母亲是不是把对妹子的爱多转加了一层在我的身上。
不过在年关之夜所有在我实际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都会显得微不足道、不足挂齿;惟一重要的事就是到文殊院烧香求佛,让我从前的名字显现!这看似荒谬的事情而此时在我的心目中却显得是那样神圣;若不神圣为何我的名字就这样消失了呢?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似乎都不约而同地将我的名字给遗忘了,改称我为二锅头——这等于别人变向地叫我瓜娃子。佛教不是讲究因果报应吗?也许是我从前做的坏事太多的缘故吧。其实我一个无知少年又没杀人放火、抢劫****,比那些五蠹俱全者差远了!这样说,并不代表我求佛心不诚,为自己开脱;相反,哪怕我其他所有的事情心不诚,而这一次也要决心诚一次!若不如此,到时二锅头此名也给弄丢了,所有人自然都该叫我瓜娃子了;我画作上的题款也落瓜娃子,那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贻笑大方了。那时真不知有多少人成为我的刀下鬼!
那第一个叫我瓜娃子的人我并没有忘记;就像小赖子一直没有忘记勾走他父亲的那个女人一样!只不过我们惩罚对方的方式不一样:我要放血,他要脱衣服。
大年三十,我匆匆吃完午饭就迅速骑车往人民中路赶。快到文殊院时,我走的是银丝街。这里什么金丝街、铜丝街多得很;与成都的那些大道相比,简直就是脚趾、手指与胳膊、大腿相比。这些街细得就像那女人的腰,刚到这里就有种被严重挤压的感觉。这里人多,即使用当年日本侵华时采用的“三光”政策都难以扫尽!
如果从银丝街排队去烧香,我想等到明天还不能看到文殊院的大门口,更莫说趁这吉日想以心换来佛祖显我姓名。事不宜迟,不能等待,于是我绕道向人民中路飞去。啊,这里人更多,我再也找不到任何言辞来形容了。几十个穿制服的警察累得就差歇斯底里,举棍打人了!看到这个症状,我高涨的热情顿时飘得无影无踪。
来烧香的人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不是为了儿女婚姻幸福就是为了他们能升官发财;不是为了孙子健康成长就是为了他们学业有成。最后也许就是为了自己能延年益寿,少生病、少吃药,在有生之年多看看这今日的“康乾”盛世。中年人占少部分,所求内容也许并无多大差别。而唯独我这样的嫩青廖廖无几,更莫说怀揣一颗显名的心愿,那更是别无二人了!
看准了这里的人,我决定黄昏来临时,趁混乱偷偷挤到前面去,哪怕被警察乱棍击晕也在所不惜;至少比无望地排队要好得多!
在等待的这几个小时里,我决定打听一下阿吉过年的情况。
阿吉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这个年为了我过得可惨了;我说为
什么这样说,她说过年公司宿舍里现只有她一个人,原本说好不回家的几个朋友和伙伴一到放假都走了,真让人扫兴!我说,你吃饭没有?她说在外面随便买了点东西吃,想来也确实可怜。她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说在文殊院,你想过来吗?她说方便吗?我笑笑说,怎么不方便呢?阿吉没再问什么,叫我等着。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阿吉风风火火地骑车赶来了,一脸地笑容。那质朴的样子,就像那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略带黝黑的脸蛋在这充满阳光的午后泛出淡淡的红晕。好久未见面了,阿吉被这座城市滋润得越发性感和迷人了,加上她带有的那点少数民族野性,你想你的心跳有多激烈就有多激烈!这样的女孩子对于城市里这些早已有审美疲劳的男士们来说,不会不是一道新鲜而可口的美味。一位植物学家曾这样说过法国画家雷东:世上最美的花儿是天造的,天下最美的女人是雷东画的;阿吉又何尝不是他画笔下的那个少女维尔利.海曼;站在我面前的这个阿吉其实那蒙娜丽莎的微笑也不过如此。
“天哪,这么多人!你们成都人都有在这个时候来烧香的习惯吗?”
“也许是吧,好多年都一直这样。你有什么心愿想求菩萨帮你实现的?”
阿吉愣了愣头,想了一会儿神秘地笑了!
“想好了吗?”
“想好了,但不能说!”
阿吉那个羞涩的样子,不用说明也能猜到八九不离十。
“二锅头,哪你有什么心愿想要实现的呢?说来听听。”
被阿吉这么一问,我的脸变成了一张苦瓜脸。
“不想说算了!我猜你是不是想求菩萨保佑你将来做一个画家?”
“是!是!可难以实现啊!”我顺水推舟,故作难堪状。
“原来是这样,做什么事都是一步一步努力去实现的。没有苦苦地耕耘,哪来甜蜜的收获!”
阿吉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让我感到惊讶。阿吉初中毕业由于无钱再继续上学,在家放了两年羊,然后就来成都打工了,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在上学。她的家是那种最为普通的较为贫困的藏民家庭。
“这么多人我们怎么能进去呢?”
阿吉愁苦起来。
“到天黑下来时我们趁乱挤进去。”
“哪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如果灵了,你就跟我走!”
说完阿吉叫我站在她的背后。
“警察叔叔,我家中爷爷突然生病,昏迷不醒,爸妈让我们赶快来叫烧香的奶奶回去!她到最前面去了!”
这位年纪稍长的警察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似乎没什么破绽,然后摇摇头说:
“你看你们怎么进去吧?”
“我们爷爷快死了,这会让奶奶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阿吉在我面前装着要流泪的样子,差点没让我笑出来。
“年轻人别哭,我把你们带到前面去,然后自己想办法。”
警察把我们带了大约十多米远,然后转身又去执行他的任务去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加紧一路挤到了售票窗口。其他人不平地看着我们,似乎毫无理解然而又无可奈何。他们现在好像把那愤愤不平之气全发在那警察身上了。
平时门票是五元,今天长到十元。我们没管那么多,领了两柱香买了四根蜡烛很快进了文殊院大门口。我的天啊,里面一样人多;若在天上看,这里像是蚂蚁在抢食一块肉!
我们松了一口气,像众多的人一样神圣起来。我取出打火机,点燃了蜡烛和香,屏住气息喃喃自语;此时,阿吉也学我的模样,变得庄严肃穆!由于不能抵达祭坛旁边,我们只能和其他的人一样,把香和蜡烛扔进了祭坛里。然后双手合并做了三个揖……
那红彤彤的火焰啊!你能把每个人的心儿照亮,可你能燃尽尘世所有的烦恼吗?
当年那个抛下美艳的妻子,丢下可怜的婴儿,弃去臣民的王子,在鹿野苑设坛讲经的时候,没想到他的烦恼会像那汇聚点点滴滴的汪洋之水,散布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从文殊院出来,黄昏已渐渐来临,我和阿吉好像各自经历了一场十分神圣的精神之旅。望着那些络绎不绝匆匆赶来的和仍旧徘徊不定的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构成了一幅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难以磨灭的画面。然而在这张画面里,我无意识地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母亲。此时,我的心似乎再也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