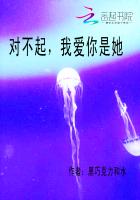成都的冬天非常冷,眼看春节临近,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街边的树叶也稀稀拉拉地快掉光了,让那些不停地忙活了快一个季节的环卫使者也该松口气了。但这样的情景并没有影响大街小巷渐浓的节日气氛,到处都在张灯结彩。尤其是要举行庙会的公园。
在成都生活这么多年,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花里胡哨的活动。年年如此,也没什么新意。而众多的人没到过年那一天,依然是该上班的上班,做生意的做生意,打麻将的打麻将,与平时没啥区别。城市仍旧是从前的城市,它显得淡定而从容。只是每一个人的心里似乎都在隐隐地盘算着来年应该多想法子挣点钱,有一个新的起点,把生活质量提高一点。让日子过得更舒服、更安逸、更清爽。成都人不求大富大贵,只求温饱好耍;只要天天有一杯茶喝、我一份报看,他这一生过得都是非常知足、非常幸福的。
而我的父亲不仅需要以上这些,而且还要有一杯酒喝才行。下岗好像让他得了忧郁症;现在又冒出个拆迁房一事,真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啊!不过他还是有希望,那就是他的那个女儿。
在大年三十那天,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到文殊院去烧香,求菩萨将我的名字显现。尽管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叫我二锅头,但是瓜娃子在我心里一直不能接受。最近我画的几幅比较满意的画作落款题的就是二锅头,就像清代那个所画鸟鱼每作必“白眼向人”,署款亦哭亦笑的“清初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一样;其实他的名字叫朱耷。思忖起这些,有时我还是有点喜欢我这二锅头的诨名,尽管他显得有点俗气,叫起来不那么儒雅。
在等待的日子里,我似乎忘记了艾姬带给我的忧愁,也忘记了阿吉带给我的神往。但是劳苦的母亲却没忘记要我带女朋友回家来看的事情,这让我一时犯了大愁。艾姬肯定不会来的,而阿吉能叫来可她又不是我的女朋友。到时母亲逼急了,只有病急乱投医,把阿吉叫来再说。我希望母亲在干活累了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精神安慰,尽管她同样爱着那个远方的妹子。
新年的钟声在一天天地等待中即将被敲响,我的心在加剧地蹦跳却不是为了那喜悦的节日,而是为了我那从前的名字能“回归”。
妹子在那边发奋攻读学业,而我在这边奇怪地活着。她打来电话,春节不能回家,我们早已能理解。她向我要我与女朋友的合影照片,我说,还没去照;她问我画画进展怎样,我说,我正在努力。就是没问我整天花的是谁的钱。
钱的确是个好东西,没有它,我们如同活在地狱;有了它,我们就像活在天堂。难怪那个中国诗人朱湘因忍受不了贫困而跳江自杀。
俗语道:马好受人骑,人穷逗人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