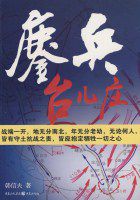因为是第一天,为表示尊重,到得晚间用过饭,李仁杰又亲自过来请张书袁去教授之所。刚到门口就见里面:明亮亮每桌一灯;黑压压一片人头。人虽众绝无交头接耳,两手置于膝间,上身挺直目不斜视,端坐一方,有如木雕泥塑。
张书袁进得屋内见此情景,心里先暗赞声‘果然和所见过的颇为不同’可他却不知道为了整出这幅光景,众人整整练了半日。
执勤士兵见先生、长官次第入内,首先敬礼后引着先生到前面讲台位置。李仁杰随即返身与众人坐于前排,大喝:“起立”,一片‘哗啦’之声,虽不甚整齐但也蔚然壮观。
接着又大喝:“鞠躬敬礼!”带头向先生鞠躬:“先生——好!”直惊得张书袁连连退到墙根忙哈腰带摇手的:“使不得,使不得。”
不等张书袁反应过来,又是一声:“礼毕,坐下!”‘哗’的一声,这次倒显得齐整了许多。
众人等了好一会儿,见张书袁还在发呆,李仁杰这才出声提醒:“先生,先生,请授课。”
读书人极重礼节,见他们如此尊师,张书袁心中甚是感动。勉强稳定了心神,翻开教案从‘上、下、前、后’等讲起。
上面教的仔细,底下听的认真;前面坐着先生,下面一群军汉,大约个把时辰后,张书袁又叫士兵们练习书写,他自己逐个检视以正笔姿。
这下可热闹了,拿惯锄头又使枪的大头兵们何时用过这玩意,抓、捏、握、夹各有姿态,有如拿刀挺枪直攥得指头发白手掌抽筋,紧张慌乱之下打翻砚台洒的到处都是,桌上、地上、身上弄得到处黑墨。张书袁却极为耐心的像管小孩般教着下面满屋的青壮,一个个的板正姿势,那情景当真有趣。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李仁杰又喝一声:“起立!”带头再次鞠躬送别:“先生辛苦”。
慌得张书袁言不答词:“不苦,不苦......”夹了教案忙乱逃窜出去。
等张书袁走后,李仁杰又踱到前台环顾四周:“下面所讲‘历史’”,他上辈子学的就是这玩意,也用不着什么教案直接侃侃而谈:“所谓历史,既先朝所出年代、人物、事情等。你等在入行伍之前,在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处所听之评书、大鼓、快板都是从此或改、或编而来。如:水浒、三国......”
“今天算第一讲,咱不说其他的先从最熟悉的讲起。前朝,满人称之为大清,也可叫做称满清。何为满清......”李仁杰口若悬河‘说一会满人,道一会前事’扬扬洒洒一讲就是多半个时辰。猛然间听到哨响,知到按军营规定到了熄灯时候,这才作罢,但临走之时规定:“以后每日先生授课后都开讲评,设为常态”
感谢时间流逝这个词,转眼间新兵们又被狠狠操.了整整一月有余,这期间杀掉部分,又陆续招来更多的新兵,至于某人敢乱嚼舌头的,恐怕连骨头都变狗.屎了。此时的军营已经修建得有些模样了,里面的士兵也同样逐渐多了起来,最起码再不是篱笆扎起来的牲口圈。
营地四面筑起两人高的土坯圩子,买来成卷带刺的铁丝网栽在上面拉了一圈圈,门口处有了岗楼、值班的岗哨,搬来了拒马、栅栏,又在周边四个拐角的角落处垒了瞭望台,但怎么看都与监狱有几分相似之处。
围墙里面的教官屋舍是首先建成的,虽说国人教官与白俄们是分开住的两处,但用的却皆是砖瓦的好料。至于那些士兵们住的?休要谈什么官兵平等,古往今来就从未有过什么所谓的平等,也包括他李仁杰前世的和谐社会。
倒不是不建而是最后再说,总算紧赶慢赶最终在天凉前,好歹在四面的草围子上糊满烂泥,也能对付着挡住风。当然,这其中也有命好的,被重新分到教官们原先搬出的土坯房里的,又另当别论。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新兵们比起以前稍微壮实点了,表现在身上明显的多了几两肉,虽然还是瘦得很,但也不至于一副干瘪排骨的样子。大概因为队伍上调养的好,兵们的‘雀蒙眼’——夜盲症,在不知不觉中也好了许多,起码夜里灭了灯也能蒙蒙的看见点东西了,只是每次需要等的时间长一些,不管如何,这毕竟也算好事。
俗话说的好‘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夜盲症才刚好的兵们现在更苦了——哨声,犹如催命般的声响已经不仅仅限于白天,这对于习惯了日落而息的他们,想好好的睡上一觉也成为一种奢望,就连深更半夜那万恶的哨子也会每天不定时的吹响。随之而来的便是伴着教官吼骂的棍子砸在他们精疲力尽的身上,他们依旧像牲口一样被踢下来。
这时,窝棚里就像炸开的鸡窝,新兵们胡乱争抢着不知谁的衣服,抢到手的边往外跑着套在身上,手慢捞不到的急得大声嚷嚷起来,又招来教官的棍子,然后依旧像牲口一样被赶出窝棚。
校场内站着乱糟糟的兵们,不等兵们有所反应,教官手里的棍子或鞭子便抽在他们系扣或提着裤子的手上,遂即便被揪着脖领子提起来。俄国佬的力气相当大,单手便跟拎只鸡崽子一样提到面前晃荡着,几乎碰到了彼此的鼻子。士兵的脑袋晕乎乎的,就好像教官手里的鞭子一样来回的晃荡。
教官大声吼骂:“黄皮猪!你妈没教你穿衣服吗!还是你妈也光着屁股!”吼声之大以至于兵们的耳朵震得嗡嗡响,士兵不敢有任何动作,也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任凭教官嘴里的恶臭伴着飞出的唾沫直喷到脸上......
兵们确实已经被打的怕了,但更被罚的怕了。任何敢于违反命令亦或忤逆教官们意愿的,都会享受到一顿结结实实的暴揍,然后再受到加倍的惩罚。
罚的形式多种多样,教官们可以叫你笔直的站上溜溜的一整天:站晕的吐得肚子里翻江倒海,直挺挺的倒下;即便没晕的,那两条腿也硬成了两根棍子,非得几个人帮忙往回挝,直痛的‘嗷嗷’叫唤才能弯过去。
教官们也可以叫你围着校场跑上五、六十圈,即使累的趴下了、呕吐了甚至晕倒了,也会把你踢起来或者泼上一桶水整醒了继续跑,不跑到圈数是不会罢休的。还可以叫你俩只手顶着筐,蹲在地上围着校场跳,跳的时间稍微长点,那腿就会筛糠般的抖起来,一路跳下来,便磕的腿上、手上脸上满是伤痕,直跳到面色惨白,心脏能蹦到嘴里。就算直起身子也会天旋地转。那时候你就会站在原地画圈,俩腿能把自己拌趴下,非要整天才能缓过劲儿来。
他们甚至可以把你像猪一样捆在条凳上,在你的嘴里塞进一个漏斗,然后往你的嘴里拼命的灌进凉水,等肚子鼓起来了涨的足够大了,再一脚踹下去,水便会混着血喷出来......教官们的手段和各种形式的惩罚五花八门,这种种滋味不要说试试,就算想想兵们都会不寒而栗的哆嗦。至于那些胆敢反抗的,无一例外,木桩周边的碎肉和杆子上挑着的人头就是他们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