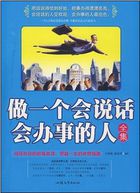那天晚上,我和桃子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当桃子的喉咙里喊出凄美如羊羔死前之绝唱的声音时,我慌张无措了,失去意识的身体如洪峰冲破堤坝,不可阻挡,在那一瞬间倾泻如注。也许是激情过后终归于平静,也许意识逐渐的恢复,也许我根本就是后悔却找不到后悔的理由,我仰躺在宾馆的床上,瞪大了眼睛透过黑暗盯视那天花板,数着窗外的夜车将灯光流星般划过,失眠了。
桃子开始把我当成了她的亲人,她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亲人。我也就知道了桃子原来是自小就失去了父母,而与她相依为命的爷爷也已经过世。这让我很震惊,同时感觉责任重大,我不知道应该将她放在我生命里的何种位置上,因为我自己的位置我都还没有找准。
“你不后悔?”
“不,”她紧紧地抱着我,“决不。”
桃子说完后满足的睡去,手脚依然紧紧地攀附住我,仿佛一只雪白而巨大的蜘蛛,她的**紧贴着我的左臂,这让我感到了她的心脏平缓舒畅的抽搐。我翻了个身,将桃子紧紧地搂在胸前,黑暗中我好像能够看到她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笑容,我想,这一刻,桃子无疑是幸福的。
我在网吧里上网,跟全国各地的女人瞎聊天,我聊地很开心,跟任何一个陌生女人都无所不谈过后却什么也记不住。这项娱乐猴头是不屑参加的,他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记不住。
“切,你知道那玩意儿是公是母长成什么模样?简直是浪费生命!”我笑话他的时候,他吐出一口浓痰,这么评价。
我不置可否,虽然觉得他不无道理依然乐此不疲。天黑的时候,我接到了他的电话,此时,我正在跟广西的一个女中学生大谈生命的意义,跟平城的一位离了婚的妇女讨论爱情的美好,我听见他那独一份的破锣嗓子嘶哑的声音,夹杂着夜排挡上苍蝇般的轰鸣。
“过来吗?我给你介绍我的妞!”
我很反感他,自从那晚以后。“你的妞介绍给我有什么用,你的球****蛋又没长在我身上,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哈哈。”他发出一股子难闻的笑声,使我怀疑他正在嚼一头蒜,“你小子不是在生我的气吧?”他说完这句必是跟什么人在笑话我,因为我立刻又听见电话里有个女孩咯咯地娇笑着。
“你也配!”我大声说。
“那好,有种你马上过来。”说完,他狂笑两声挂了电话。
我结了帐走到黄昏里去,抬头朝日头落下去的方向看了看,想到家里的母鸡应该钻进窝里去了吧;母亲已经端着簸箕回到屋里并开始准备晚餐;父亲也许正从菜园子里往回走,也许已经拧开收音机在听评书联播了……心里头突然空落落的,这真叫人摸不着头脑。
我给桃子打电话,叫她一块儿吃饭。桃子愉快的答应着,使我想起了她笑时的样子。宝贝安静地站在路边,我下车等桃子,一边玩手机里的打蜜蜂游戏。
约莫十分钟,桃子来了。她从我身后突然地蹦出来,一下子将我抱了个结实,同时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口。我看见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如花似玉地笑,就明白今晚她是不打算回去的了。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沮丧,但我还是愉快地笑了笑,至少我的笑容显示我是很愉快的。
桃子从第一刻起就好似贴在我身上了,宛若一块狗皮膏药。她紧抓着我的胳膊,好像垂死的落水狗抓住了一根木头。她神态妩媚,柔情似水,看着问我,“想我了吗?”
“想。”我实话实说。
“怎么个想法?”
“没日没夜地想,不知疲倦地想,神经错乱地想,心跳停止地想,垂死挣扎地想,粉身碎骨的想,总之,玩儿命地想,。”
我一派胡言,任何清醒的人都感觉得到,无奈恋爱中的女人是愚蠢的,因为我让桃子变成了女人而她又彻底地爱上了我,她显得很感动了,痴迷的注视着我的脸。我很难堪,眼睛不由的想闭上。
“唉!真的吗?”她幽幽地叹气。
我下死力地点头,同时睁大双眼防止它们一不小心“吧嗒”合上。
“那想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她等了一会儿这么问。
“真想知道?”
“想!”
“很绝望!”我严肃地说。
“为什么?”她疑惑地问,神情略显紧张。
“因为想你却见不到你。”
她立刻“咯咯”地笑了,一脸灿烂,“傻瓜,我这不是在你面前吗?”她停了停,温柔地抚摩我的脸,充满深情地道:“放心好了,只要你要我,我随时出现,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说完,她又迅速地在我嘴上吻了一下。
我听到我的眼皮“吧嗒”一声关上了,立即紧紧地抱着她。
我们在海林夜市的大排挡看到了猴头,其时他的一只手搭在一个女孩的肩膀,另一只手举着一只虾在那女孩的嘴边晃,他低着头没有看见我们。女孩很害羞地张嘴含住虾后,娇笑着将猴头一把推开。这女孩长得还算周正,穿着也很正派,我不认识。猴头笑着抬头,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我身边的桃子,立刻有点儿不自然地晃了晃,站起来。
我大刺刺地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桃子紧紧靠着我坐在旁边,很镇静。
猴头立刻吩咐摊主加菜,并问我和桃子想吃什么。我看了看桃子,桃子摇了摇头,不知怎地,我觉着桃子看见猴头后镇静得有些过分,她是应该表现出点儿厌恶才对的嘛。猴头开始给我们介绍那女孩:“我女朋友,严丽萍,在师大读书,学中文的。”
猴头如数家珍地介绍完,使我明白了他为什么执意叫我过来,恐怕目的就是想要告诉我他找了个女大学生做女友而已,我同时也就了解为什么这女孩并不怎么很漂亮猴头还拿她当宝贝似地哄着了。我听着“女朋友”三个字从猴头那破锣嗓子里庄严地蹦出来,仿佛听到了一个****的贞洁演讲,一阵好笑。
猴头将我介绍给严丽萍,却没有介绍桃子,也许他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也许是忘了。严丽萍拘谨地向我点头后,目光看向桃子,我只好告诉她桃子是我的女朋友。两个女孩友好地互相招呼,猴头惊讶地看着我,我有一种心被撕裂的感觉,几乎不愿呼吸。我不知道带桃子来是不是一个错误。
严丽萍如果减掉那些太多的好奇心,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女孩。猴头也确实耐心地可以,不厌其烦地将我小时候的那些糗事拿出来向她抖搂,他说到了我为了买一瓶蜂蜜去火车站捡破烂,说到我为了经常吃蜂蜜竟然异想天开要养蜜蜂最后被蜜蜂的屁股蛰了,他为了取悦新女朋友不惜出卖老朋友,连我穿着露腚的牛仔裤上街都无情地扒拉了出来,而他自己的事却一点儿也不透露。这鸟人真可恶!严丽萍瞪大好奇地双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劲儿地问我,“这都是真的吗?”
桃子也跟着瞎搀和,这让我发现女孩子的一个通病,同时也揭开了一个迷惑:为什么这么一个女大学生,有着美好的前程,不好好在学校念书,却跑出来跟猴头这么不三不四的东西交往呢?答案是好奇。
我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时太小不懂事。两个女孩就嘻嘻地笑,桃子笑地趴在我怀里大喘气,宛如一个患肺气肿晚期的病人,严丽萍捂住嘴唇,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猴头得意地给我眼色看,我回瞪他。
如果严丽萍这小妞的好奇心仅仅局限在我的身上,是晚的气氛应该是愉快的,偏偏她转向了桃子。我相信她这是嫉妒心使然,女孩嘛,也怪桃子太张扬,她那光洁滑润的皮肤即使在夜市的昏暗灯光下也能咄咄生辉,刺人眼目,不像严丽萍那阴云般暗无天日的脸。
“你在哪里上班?”严丽萍突然问桃子。
桃子没有回答,她在桌子底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我看到她的牙齿抿住了嘴唇,正要说话,听见猴头若无其事地说:“他们俩是同事!”
他的回答使桃子的指甲深深陷进了我的皮肉里。严丽萍“哦”了一声,好像很失望,她从桃子的身上收回视线,端起杯子喝酒。
美好的气氛秋风扫落叶般荡然无存。
“回吧。”我提议。
猴头点了点头,招呼结账。
“干嘛这么早就走啊?再坐会儿嘛!”起身的时候,严丽萍遗憾地叫道。
我拉着桃子的手,头也不回。
桃子一上车就哭了,无声无息地流泪,这眼泪浸湿了我的后背。我没有劝她,我不知道该如何劝,只管风一般让宝贝跑起来。宝贝呜咽着,仿佛呼应着桃子的眼泪。
到了宾馆,我没有开灯,关上门就将桃子放倒在床上,我知道她需要我紧紧地拥抱,她一定需要。我就只管紧紧地抱着她,无须言它。桃子在我温暖的怀里渐渐地安静下来。她扳转我的肩膀,温柔地看着我的脸,目不转睛,默默地,痴痴地,看了足足有十分钟。她的脸如残花带露,我轻轻给她抹去泪痕。
“我是不是一个坏女孩?”她这样幽幽地问,又像是自言自语,使我心痛不已。
我暗暗嘱咐自己不要在乎,不要在乎感情,不要在乎任何女人的眼泪,我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对感情认真的人,我不需要任何女人的爱,假的,统统都是假的,不需要,全都不需要。我没有回答,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发现两种答案都是不能说出来的,如果说肯定那会带给她伤害,如果我否定那只会让她以为不过是良心上的安慰。
我不能回答。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的。”她叹气,眼泪再一次如潮水涌出来。
我立刻慌了,人们无疑会将沉默看作是一种肯定的回答。此刻,我宁愿我是个众所周知的哑巴。我拉她如怀,深深地吻她的眼泪,她的眼泪苦涩潮湿,我不停地吻着,那一刻,肝肠寸断,刻骨铭心。我在她耳边轻诉,“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你的眼泪是海,我会跳进去将海水吸干!”
桃子听了控制不住地吻我,眼泪竟还要丰富,如同七月的暴风雨。我知道她是开心,她是激动地难以自制。我们疯狂地接吻,将衣服一件件扯掉扔在地上。我感觉那激情燃烧如森林之火,火在烧,在爆炸,将一切的一切予以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