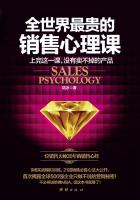叶冬又说:“老刘刚才说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在西宁购买的攀岩绳,肯定是样子货,不带钢芯的,承重力要打很大的折扣。没有办法,咱们只能两股拧成一股来用,这样一来,长度就会不够用,我们又没有岩钉和岩锤,像刚才看到的上野狐洞那里的崖壁,都是负角的峭壁,肯定不好下去。所以,我们先要搜索榆林窟里的河谷两岸,从下往上寻找——东、西两侧崖壁上的特殊标记。如果我们的运气足够好,也许不必要冒这个险。”
老刘不解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好运气?喝凉水都塞牙,叶冬,你别盲目乐观了!”
叶冬淡淡一笑,解释道:“我们是查找我父亲藏匿物品的地点,或者留下警示的地点,我父亲来的时候是逃亡,身上没有携带任何装备,他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也能,而且原则上讲,徒手就能,所以,用安全绳在崖壁上寻找,这是最后一条路,我觉得我们用不上。”
经他这么一解释,老刘即刻被点醒,点头称是。
叶冬又接着说:“我最担心的是梁若兮那边,自从上次和她通话以后,到现在已经四天过去了,他们没有任何音讯,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罗烈愕然,反问道:“咱们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的状态,现在又全部换了SIM卡,咱们又没有和她主动联系过,她当然不知道咱们的行踪,这有什么问题吗?”
老刘嘿嘿一笑,声音中有几分嘶哑,回答道:“罗老师,你太小瞧梁若兮了,他们神通广大,有多少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咱们的身边,你都忘了吗?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就在咱们的附近,我已经闻到脚趾身上的古龙香水的气味了。倒是胡维明他们,自从张掖一别,到现在销声匿迹,这才是最大的变数,除非是咱们错怪了他们,否则,他们早应该赶上来了。”
叶冬沉吟不语,心里暗想,是啊,此时危机四伏,事情已然发展到如此地步,如果原地徘徊,只会让自己这一伙人陷入更大的被动之中,只能快刀斩乱麻,先干了再说。想到此,他抬眼看了看烈山,只见烈山蜷缩成一团,睡态酣然。
老刘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嘴里嘀咕道:“他还真睡得着,烈山,烈山?”
何烈山没有任何反应,却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咱们现在就像是农民一样,得靠天吃饭,你们难道没有想过气候的因素吗?万一出现异常的灾害,是不是还要按计划进行?”
叶冬一惊,对啊,这一路走来,乌云遮日,风雨不断,颇感流年不利,自己怎么能如此疏忽,漏算了这一点。
老刘笑着说:“敢情师弟也睡不踏实,气候是个大麻烦,咱们左右不了。我想,只要不下刀子,咱们就按计划行动,恶劣的天气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坏事,可是对咱们却是最好的掩护,这难道不是上天的眷顾吗,念弥陀佛去吧!”
叶冬摇头,心中惴惴不安,支吾道:“见机行事吧。”
老刘转身吩咐全安,“全儿,你去前面跟老板娘说,说我想吃炖腔骨,让她给炖上一锅,多放酱油和盐,味道一定要重,就说我口重,淡了没味。再去让陈土搞上几瓶好酒,这顿晚饭就算是咱们哥几个的断头饭,吃了这顿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吃下顿呢!”
全安下炕穿鞋,一边嘴里答应着,一边问陈土是谁,却不行动,只望向叶冬等人。
叶冬故作轻松地笑道:“老刘,你说点吉利的,咱们就是去找些线索,既不是去赴汤蹈火,更不会肝脑涂地,用得着这么悲壮吗?”
老刘神色黯然,嘀咕几句,好像是说,自从遇到了叶冬,就开始祸不单行,但凡有最坏的打算,都被一一言中,此次当然也不会例外,并劝叶冬自此之后应改名叫哈雷,也算实至名归。
叶冬等人都哈哈大笑,全安这才出门去吩咐老板娘。
几个人又闲聊了几句,实在睡不着,但是都知道晚上还要忙一宿,当下也不再说话,纷纷躺倒,闭目养神。因为天气阴沉,所以夜晚来临的特别早,七点刚过,天色就暗淡下来。这里已是西北的腹地,实际时间和北京差了一个时区,此时只相当于内地时间的五点。
几个人起床,洗漱完毕,便到前面饭馆吃饭。陈土炖了一大锅腔骨,肉香扑鼻,因为没有别的游客,这家饭馆成了他们的私人餐厅。老板娘坐在一边,一边搓着面鱼儿,一边看他们吃。陈土特意给众人准备了一瓶好酒。
叶冬又烧了起来,浑身乏力,无精打采,只吃了几口菜,就没了胃口,可是,他一想到这一夜苦熬还等着他,只得逼着自己又吃了几大碗疙瘩汤。不承想,这几碗热汤下肚,头上微微见汗,他倒觉得这病好了许多。
烈山、罗烈闷头吃饭,滴酒未沾。老刘则吱喽一口酒,吭哧一口肉,吃得很香。全安没有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几个人吃了半天,才见他拎着一大袋子水果跑了回来。
老刘问:“全儿,不吃饭你跑哪去了?”
全安把那个大袋子放在脚边,也不洗手,坐下一边吃一边回答:“二叔,听说瓜州的蜜瓜好吃,又甜又解渴,我去买了几个。”说着,嘿嘿地傻笑不停。
老刘点了点头,这孩子是个有心人,不多说不少道,眼里全是活儿,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
几个人又吃了半个小时,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老刘这才站起身,拎着酒瓶,喊道:“陈土,酒我给你剩了一半,你喝吧,我请客!肉我吃得很香,你这手艺,真没得说。”
陈土裹着油脂麻花的围裙,从后厨跑了出来,笑着说:“老板,酒我给你存着,等你回来再喝。要我说,你们今天晚上还是别走了,要不明天早上再走吧。”
老刘笑着回答:“不行啊,约好了的,下刀子都得去!一会儿,我侄子送送我们,就回来,你帮我照顾好他呀!”
陈土大声应承着:“昂。”
两口子把众人送出小饭馆,看着车拐出这条巷道,才转身回去。全安开车,顺着双石公路,向着榆林窟万佛峡的方向驶去,这条路白天已经走过一个来回了,轻车熟路,哪儿有个沟沟坎坎都记得清楚。在临近蘑菇台的时候,全安不待吩咐,就关掉了车灯,摸着黑向前开。
因为黑暗,车速也降了下来,老刘吩咐道:“全儿,停车吧,我们就从这下车!再往前不到两公里,就应该是榆林窟了。你调头,慢点开,往回一公里左右,你就可以打开大灯了。一定要注意安全,记住,两天后,你来送吃的。”
全安点头答应,想嘱托几句,又怕二叔嫌他罗唣,眼圈有点发红。
几个人下车,把装满东西的登山包背上,又拎着蜜瓜,顺着双石公路朝榆林窟的方向走去。
四个人不敢走大路,就在路基的下面,靠近玉米地的边缘向东南方向疾行。周围生息全无,没有一点亮光,风吹庄稼地,似波涛拍岸。他们脚下踩倒庄稼、杂草,也发出沙沙的声音。
老刘抱怨道:“我靠,这么黑,当心踩一脚屎。”
叶冬低声笑道:“放心,没屎,谁敢来这拉屎,吓死他~~~”
“嘘——”
走在最前面的何烈山突然发出噤声的警示,几个人都停下了脚步,他们侧耳细听,就听到,在节奏分明的涛声中,藏着一种奇怪的响动——是庄稼被碰倒发出的哗哗声,还有啃咬东西的声音。
几个人都觉得头皮发炸,老刘一把抽出腰间的弯刀,蹑足潜踪,靠近烈山。两个人的脸几乎贴到一起,才看清楚烈山的表情,只见他把手指放在唇边,眼睛瞪得大大的,又用手指了指庄稼地深处。老刘会意,抬手挥了挥******,示意他有武器,由他来打头阵。何烈山和老刘卸下肩膀上的背包,轻手轻脚地向着声音发出的地点靠近。叶冬示意罗烈留下,自己也跟了过去。
虽然他们的脚步很轻,还是发出了很大的响声。不过因为风声更大,如果不仔细辨别的话,也听不出来。叶冬的手心里全是汗,紧紧握住拳头,紧跟在老刘他们的身后。
距离那声音越来越近,而那声音还在响起,烈山突然拉住老刘,扬了扬手里的手电筒,示意他做好准备。老刘点头,身体前弓,像一支即将离弦的利箭一样紧绷。
烈山突然拧亮了手电筒,一束明亮的光柱透过玉米杆照射过去,叶冬看见了,是一头驴,正在偷吃刚结了棒子的玉米。
那头驴被光柱吓了一跳,呆愣在原地,随即反应过来,把目光愤怒地射向了打扰它进餐的异类。按照它的犟脾气,它本应该奋蹄直冲过来,掀翻这几个不速之客,但是它借助着手电筒的光亮,清晰地看到了老刘手里明晃晃的钢刀。它立刻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那头驴驴头一转,奋力狂奔,瞬间,伴随着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哗哗声,逃向玉米地深处。
烈山关闭手电筒,老刘嘿嘿一笑,拉着叶冬往回就走。嘴里嘀咕着,“野驴,挺好玩的,虚惊一场。”
烈山和叶冬也不搭理他,低头朝回疾走。他们走到,刚才和罗烈分手的地点附近,几个人都怕吓着他,老刘特意咳嗽了几声。可是,当他们回到原地的时候,立刻发现,罗烈不见了,只有三个沉甸甸的登山包立在原地。
叶冬大惊,轻声地呼叫:“罗烈,罗烈!”
只有风的呜咽声,没有人答应。
叶冬不敢放开声音大喊大叫,可是心中着急,急得团团乱战。
老刘不甘心,压低嗓子又叫了几声:“罗烈,罗老师!”
还是没有人回答。
老刘疑惑地说:“这个书呆子去哪了,瞎跑什么呀!”
叶冬稍一冷静,随即说道:“他肯定没有进庄稼地,这里没有他的背包,一定是上公路了,快走,他也许还没走远,咱们还能追上。”
三个人背好背包,拎着袋子,再也不顾暴露行藏,顺着双石公路,朝前跑去。
跑出去还没有三百米,就能够看到前面的公路上有一条人影,听到他们的声音,那条人影立刻跳到公路的一侧,隐身在几丛乱草之后。
叶冬跑在最前面,低声叫着:“罗烈,是我们。”
那条人影这才站起身,走上了公路。果然是罗烈。
老刘埋怨道:“罗老师,你怎么擅自行动啊,这多危险,万一走丢了,可怎么找你啊?”
罗烈解释道:“我一直跟着你们走呢,你们怎么在我后面?”
老刘一惊,问:“怎么回事?你快说说。”
罗烈讲道:“刚才你们三个人都去找那个声音,没过多久,就有人回来了。他离我很远,朝我招手,我就跟着他走。我还以为是你们呢,可能是发现了什么情况,让我去看看。我跟着那条黑影上了公路,我还叫了他几声,他也没有回答。之后他就跑向另一侧的荒野,我正要追过去,就听到身后有声音,于是藏了起来,谁知道是你们。”
“什么?还有别的人在这里!”老刘惊讶得嘴都合不拢。
烈山猛地俯身,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倾听。
叶冬问罗烈:“那个人是什么样的身材?”
“和烈山差不多高,身体消瘦,别的就看不清楚了。”
老刘疑惑地喃喃自语:“会不会是老叶!”
叶冬心里明知不是,但是猛听老刘如此一说,竟盼着果真如此。他全身的血一下子冲到头上,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也不和众人商量,便不顾一切地起身追去。
三个人跟在他的身后,也向着公路另一侧的荒原之中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