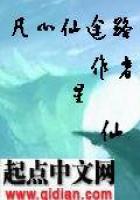老刘一边抽烟,一边思考,憋了半天,还想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发问:“罗老师,我又没听明白,这万佛峡的地望不是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突然冒出了藏传佛教的显、密二宗,还什么意义重大,怎么就重大了,你给我解释解释?”
罗烈笑了笑,在黑暗中露出一嘴的白牙,他托了托眼镜架,讲道:“三代以前的事多不可考,能够流传下来的几乎全被记录在神话传说里。但是对于西北地区,一直有着很多美好的猜想。王大有先生曾经对上古时期的神话史做过梳理,他提出祁连山一带才是华夏文明的发源之地,而且从燧人弇兹氏立天表,确立天北极,结绳记历,开创‘九星悬朗时代’开始,直至炎黄时代,他们一直以祁连山地区为祖地。炎帝连山氏,应该就是指在祁连山一带生活的炎帝一部。在更加古老的时代,燧人氏的祖先也生活于距此不远的藏地羌塘地区,还有始终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古昆仑也有可能就在这里。对于华夏文明来说,西北这片土地是神奇的,透着灵气的。这话讲远了。孔子删书断史,将神话人物历史化,变成了活在古籍中的历史人物,使许多被各族尊崇的祖神被迫人格化,几乎被阉割掉了一切神性。由此,关于上古三代以前的事被赋予后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被描述成了另外一个样子,虽然完整,却不可信,更无从考证。宗教产生于文化,即所谓教化之道,在宗教信仰中保留了很多最古老的传承,对于人类起源之初的历史是一种很好的继承。比如,《苗族古歌》,就是一种用歌唱的方式,延续下来的神话传说,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比较真实的历史原貌。道教亦然如此,佛教虽是舶来品,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和华夏文明融合,也是如此。”
罗烈看到老刘一脸的不耐烦,知道自己把话题扯的太远了,忙直入主题,“噢,这些神话听听也就罢了,还是说回到现实。西晋道士王浮撰写的《老子化胡经》里讲,老子西出函谷关,跑到流沙一带,后来和尹喜去了北天竺,化身佛陀,立浮屠教,也就是佛教,从时间上来看,老子的隐匿和佛教的产生勉强可以联系到一起。有一种说法,释迦摩尼生于公元前565年,灭度于公元前486年;这和公元前505年,王子朝之乱进入尾声,老子无奈之下西出函谷关的时间还算吻合。不管是出于佛教为了在中原地区传教布道的需要,还是道教人士为了证明道教的正统地位的需要,《老子化胡经》的出现都无可辩驳的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就好像孔子当年删书断史一样,可以弘扬天下的就记录下来,不能讲的就藏起来,或者毁掉,让时间去改变一切。一旦这种现象产生,就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是伏藏。而且这种藏东西的美德很久以前就有,从黄帝伊始,上古有之。不准(音‘否彪’)发现的汲冢书如此,孔子壁中书如此。提到敦煌石窟群,更是如此。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古籍却可以在敦煌的卷子中找到原本,而万佛峡榆林窟就属于敦煌石窟群中的文化遗迹。说回到佛教,佛教分为大、小乘和大乘金刚乘,也就是密宗。从密、显二宗的佛法教义来看,密宗参禅证果更快,而且法门众多,很有点像《西游记》里菩提老祖对孙悟空说的那样,‘道字门中三百六十傍门,傍门皆有正果’,菩提祖师还提到术、流、静、动的修炼法门,但是乖巧的孙猴子都没有学,最后却学了‘显密圆通真妙诀’。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万法归一,佛、道殊途同归的道理。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试着这样解释,道教的尸解之道,和佛教的虹化大法、藏教中的中阴闻教得度大法,都应该是殊途同归的。从表面上看去,道家有道家的妙法,佛家有佛家的精义,其实并不矛盾,都是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描述而已。由此抽丝剥茧来看,无论是洪保的铁索悬棺,还是现在我们将要面对的圆城寺的藏传佛教,都应该是具有同样的核心事实。”
老刘妈呀一声叫了出来,“俺的个娘哎,罗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都不是正常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将要进入妖魔鬼怪的世界了!”
罗烈摇头,更正老刘的话,“我没有这么说,我只是说秘密的指向是这些,而且你们在洪保的墓中遇到的幻境,和那些魔鬼虫,单纯用‘越州鳗井’的典故是无法解释得通的,都说明事情非同寻常,我只是提醒大家要小心。”
老刘吐了吐舌头,不再争辩。
叶冬看了烈山一眼,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表情索然无趣,就好像刚才大家说的事和他无关。叶冬不想逼他说话,看了看表,时间已经不早,招呼几个人打车回酒店。
进入酒店大堂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提醒他们,访客要在十一点之前离开,客房不能留宿。
老刘没好气地正告服务员,“我们要打牌,你没看见吗?我们连行李都没有,又没有女客,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那个小伙子没有再说话,躲到一边。老刘一进客房,就抱怨道:“我不是舍不得花钱,实在是没有必要,咱们的话都没有讲完,开了房也回不去,干脆今晚挤挤,抵足夜谈吧!”
叶冬挤出了一丝难得的微笑,只说昨夜烈山和罗烈便没有睡,众人都不是神仙,还是先睡饱了再说。烈山让罗烈帮忙,把自己的床垫抬了下来,放在两张床的中间,形成了一张大通铺,虽然中间落差很大,但是让人感觉到一种温馨。老刘又吩咐前台再送来两套洗漱用具,之后,众人依次洗漱,各自安歇。
四个人都累极了,特别是叶冬,从北京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现在更跑到了太原,受尽奔波之苦。中间盗了一次墓,打了两回架,又被任桓折腾了一整天,另加上牵挂父亲,此刻已然是心力交瘁,洗了澡之后,他便一头躺倒在床上,只挂在床铺的一角,沉沉地睡去。罗烈心疼老刘身体胖大,把地铺让给了他,自己躺在叶冬的旁边。烈山把被子当成褥子铺好,也把头一转,便不再说话。
只有老刘,穿着三角小裤衩,光着膀子,看着电视,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我靠,连个***片都没有,这让人怎么睡啊!”
老刘斜眼看了看罗烈,见他充耳不闻,随即自己无趣地嘿嘿一笑,主动凑过去搭话,“罗老师,我承认你对事情看得比我们透彻,但是我觉得你的猜测也过于写意了。先不说那些妖魔鬼怪的玄事,你能告诉我洪保墓、圆城寺地宫和金印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吗?”
“我怎么会知道!直觉告诉我,金印必和圆城寺地宫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秘钥来讲,它有一个特别之处,让人不好仿造。这就是它的重量,那么小的体积,重量将近十斤,即便有人能够仿造出来,其重量也达不到原件的标准,这就是我对于金印的解读。至于洪保墓,虽然隋老和黎大爷都做过分析,但显然还没有达到正确解读的地步。这一方面取决于他们故有的成见,另一方面也和你们下墓时的观察有关。而你们稍有疏漏,便会令分析者不能正确解读。其实,早在你们要去南京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一些资料,可惜你们谁都没有看过!”
老刘忙问:“什么资料,你说说看!”
“我所有的资料都是基于《明史》而言的,徐元文、张廷玉等人编修的《明史》实为一部比较详尽的断代史,可以作为依据。其中记录:
‘洪武四年七月壬戌,京师风雨地震。
八年七月戊辰,十二月戊子,京师地震。
建文元年三月甲午,京师地震。
永乐七年五月壬戌,十一年八月甲子,十三年九月壬戌,十四年九月癸卯,二十二年六月壬申,南京复震。
洪熙元年二月戊午,南京地震,凡四十有二。
宣德元年七月,南京地震者九;二年春,复震者十;三年,复屡震;四年,两京地震;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
这些记录直到正统年间,才逐渐停止下来。而郑和船队出航的时间,几乎与这些时间先后衔接,特别是从永乐十年开始的第三次航行后,几乎每次都是先有地震,后有出航。而洪武年间,宗泐出使西域搜求遗经,侯显在永乐元年首次出使乌斯藏,迎请得银协巴,也和这些记录丝丝相扣。而我们都知道,南京并不座落在任何一条地震带上,这些频繁的地震活动,事出诡异,定有缘故。另据《明史》中记录:
‘宣德元年七月甲午,地生毛,长尺余。
正统八年,浙江地生白毛。
成化十三年四月,甘肃地裂,生白毛。十五年五月,常州地生白毛。十七年四月,南京地生白毛。
弘治元年五月丙寅,泸州长宁县雨毛。
正德十二年四月,金华地生黑白毛,长尺余。’
这一现象,直到正德十二年,即1517年以后,便再没有发生过,而成化年间的频发,正和妖狐夜出,李子龙潜入大内的时间吻合。这会不会就是指你们遇到的那些魔鬼虫呢?”
老刘被吓得浑身一抖,不由自主地频频点头,又问:“罗老师,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巧合,都是神鬼妖魔在作祟!”
罗烈淡淡一笑,摇头道:“还不能这么说!人类很可笑,不懂的就都归结于神鬼之道。我们可以试着走下去,答案慢慢就会清晰起来。”
老刘点头,问:“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罗烈略一沉吟,说道:“应该去定西,去找梁小姐,直截了当地当面质问脚趾,逼他说出实情。”
老刘不待他讲完,连连摇头,“可惜任桓跑了,脚趾不承认咱们也没有办法,即便任桓还在咱们手里,我估计他也不敢和脚趾当面对质。万一和梁若兮他们撕破了脸皮,下面可怎么办?这个办法不稳妥,咱们不能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罗烈承认老刘的反对意见是中肯的,但是自己确实没有想好,又被问急了,才脱口而出。
老刘被好奇心折磨得手足无措,他推了推烈山的肩膀,轻声地问:“睡了吗?师弟。你醒醒,咱们商量商量啊!”
何烈山不胜其扰,转过身,瞪着他,没好气地回答:“有什么好商量的,皇帝不急太监急!咱们唯叶冬马首是瞻,何苦自寻烦恼。你要是担心,就担心担心你的刀怎么办吧,没事老带着它干什么,去哪都不自由。”
对于师弟的冷嘲热讽,老刘一笑了之,他这个人最善于从平淡中升华,其他的皂苷零碎一概不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厚颜无耻,另一方面不得不夸奖他很睿智。老刘梗着脖子寻思半天,终于品出烈山的话中之意,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从地铺上蹿了起来,挤到叶冬和罗烈的床上,猛推叶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