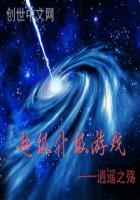终于有些忍不住,杨荣踉踉跄跄地裹着寒风进到朱棣帐中,叩拜后直截禀奏道:“陛下,我军万里赶来,现在却战不能战,长期驻扎,粮草衣物又接济不上,眼看兵将怨气日重,陛下,还是先班师回朝,待准备充分了,先让骑哨打探清楚敌情再作征讨。”
杨荣觉得自己说的倶是实情,皇上当然会痛快地应允。朱棣端坐在帅椅上,周身拥着厚厚的衣被,但仍然面色铁青,嘴唇似乎不住地打哆嗦。“杨荣。”僵硬的嘴唇终于翕动着说出话来,一团白气从口中腾出,话语冰冷,“当初竭力劝朕出征讨伐瓦刺的是你,现在头一个说要班师回朝的还是你,你是何意,莫非拿朕当小儿戏耍!”
杨荣浑身一震,他听出了话中的意思,皇上现在其实正处于两难地步,若一直向荒漠深处走下去,瓦刺踪影不见,简直是自找死路,若就此班师,无功而返,难免会给人留下劳民伤财的话柄,要知道,当初正是因为出征,夏原吉被下到诏狱中,至今生死不明,若就这样回去,岂不承认错的是皇上?可皇上怎么会错?
“臣……臣当时并未料想到漠北深处会如此险恶,臣……”杨荣有心想揽过些罪责,来替皇上开脱,但他也清楚这个罪责的重大,弄不好会丢掉老本,他犹豫着不敢不承认自己的错处,也不敢全担待起来。
朱棣却仿佛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鼻?里“哼”出一声,仍然面无表情地说:“杨荣,朕知道你是忠心为国,但便忠心,也有失误的时候,失误不比奸侯,但造成的祸患却同样严重,朕向来体谅臣子的苦心,也不会为难于你,只不过叫其余人等好生思虑周到罢了。”
听皇上这样说’杨荣放心一些’但心里仍没底’刚要再说话,朱棣已经招招手,侍立在营帐一侧的卫士蹿上来,将杨荣按倒在地,三把两把地捆住了。杨荣忽然忘了本来想说的话,就这样一声未吭地被带了下去。
第二日一大早,军中上下传出令兵士们振奋不已的诏令,全军拔寨南归,待粮食衣物准备齐全了,瓦剌消息打探确实后,再另行征讨。“知道么,这回匆忙北征,听说全是杨荣出的主意,圣上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还治了罪,这家伙,害得多少弟兄白白将骨头扔在狼也不来的地方,治罪活该,杀了他的头才解恨!”因为即将解脱苦难的高兴,众人的话也就格外多,你一言我一语,将杨荣骂了个狗血头。
大军匆匆而去,又仓皇而回,没遇到敌军一兵一卒,却平空折损三成兵士,出征时北京城中囤积的粮食全部运走,而今人人空腹而归,更有些已经几天没吃上饭,摇摇晃晃的,没等进到城中,便晕倒在地。
回城当天天气阴沉沉的,乌云低垂,天际不时传来阵阵雷声。雷声忽远忽近,渐渐滚落到头顶上。朱棣一改往日骑马行军的习惯,他坐了辇车轰隆隆地驶进永定门,那里聚集着群臣等待迎驾,但辇车丝毫没停顿,直接从他们跟前碾了过去,随从太监一迭声解释道:“皇上身子不适,百官免见。”大家也就默默地叩了个头,各自散开。
车辇的影子隐没在甬道上,众人就要散开之际,雷声突然尖利起来,条条火龙在乌云中上下飞舞,闪现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好像随时都要落下来。“快些走散吧,怕立刻就要落雨了!”有人这样说,大家得了提醒,脚步更加迈得快了。
可是没走几步,霹雳炸响,道道火柱在火龙间交错,尖利的声音叫人茫然。恰在这时,一声吆喝陡然响起:“快看哪,紫禁城那边着火了!”惊恐中众人驻足朝正南方向望去,可不是,远远的,火光已经映红了低垂的乌云,火柱和火龙在火光正上方舞动得更欢,不用说,是它们击中了某座大殿,引发了大火。
“糟了,紫禁城正殿全是干透的巨木构建而成,这火一着起来,恐怕大灾降临了!”每个人都恐惧地这样想到。
朱棣在辇车中也听到了随从的惊呼,吵嚷声越来越大,雷鸣风吼里听起来格外令人心惊。朱棣不耐烦地掀开眼前的帐幕,没等他呵斥,南边天空一抹红彤彤的跳动先让他瞠目结舌。他立刻知道,着火的地方必定是皇宫无疑,别的庄户人家,即便遭了火灾,也弄不出这么大动静来。
“快,你们看不出来么?!一群不中用的废物,快传朕的旨意,令城中兵卒全数调过去,赶紧救火!”朱棣见随从们只是嘁嘁喳喳地叫嚷,却满脸麻木,仿佛被惊呆了,又好像有意要看热闹,禁不住怒骂起来。一股凉风趁机冲进喉咙,他伏在车栏上猛烈地咳嗽,脸上神色在阴云笼罩下颇有几分浄狞。
等众人簇拥着车辇接近皇城寸,灼热的气息愈加浓烈,夹杂着油漆味的烟雾弥漫过来,呛得朱棣喘不过气。但他强忍住了,他将这场大火当作了在漠北没能追寻到的敌人,他站在辇车上,指手画脚,大声叫喊着要太监护卫们跑东跑西,忙得不亦乐乎,他甚至还冲进皇城,站在大火附近,亲自看他们是如何救火。
大火毕毕剥录地冲天燃烧,头顶的黑云已经被烤成暗红色,前廷后宫也乱了界线,宫女们纷纷跑出来,尖声叫喊着想要远远躲开,又不忍心错过这么难得的热闹场面,不远不近地驻足,观看兵卒们抬水救火。
大火映衬下,天色愈暗,有几个宫女正巧站在朱棣的辇车旁,但她们只顾盯住面前的大火,没注意到皇上就虎视眈眈地杵在身边。
“姐姐,这么大的火,我可还是头一回瞧见,真好看,太壮观啦!”一个宫女兴地着叫。
“唉,可惜这是百姓的血汗哪,辛辛苦苦多少年,就这么一把火给烧了,实在太可惜哟!”另一个年龄略大些,话语更沉闷。
站在旁边正看得人迷的宫女听她们说话,冷不丁地插过话头:“可惜什么,百姓的血汗倒不假,不过即便不烧,百姓别说住,就是看上一眼也不能够,叫我说,烧了活该,总之是干活的人累死累活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反倒不如大家者住不上了心静!”
听她们说得这么热火,又有宫女凑过来,眼光不离大火,嘴唇上下翻动着快人快语地说:“哎,知道么,我听老年人讲,被雷打死或叫点着了房屋,那是这个人做了造孽的事,老天爷要惩罚他呢!前阵子权妃一死,吕妃不知怎么的也被杀了,杀了吕妃不算,还将大大小小的宫女杀那么多,这样的皇上,和说书人讲的隋炀帝差不多,怪不得上天要警告他一下,宫城皇城都烧光了才叫绝呢,咱们没了地方住,正好回家,我早就在这鬼地方住够了!哪里是皇宫,分明是牢狱!”
其余几个听了连连拍手:“姐姐到底是读过些书的,说出话来果然比我们强!皇上不光在后宫滥杀无辜,听说这回好端端的硬要什么北征,结果胡人的影子没见到一个,自家倒白白累死了一大半,这不是造孽是什么,老天爷没长眼哪!”
说着话有人哽咽起来:“临叫选了来宫里时,我哥哥就被征发人伍了,这回出征也不知有没有他,若他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爹娘可就没了指望了!”
听她这么悲戚,众人也动了心事,沉默片刻,先前那个讲话最多的宫女打破沉闷,压低了声音说:“哎,听说过么,现在皇上六十多的人了,那东西早不中用啦,既然不中用了,还霸占人家这么多女孩子家干什么,宫殿全烧光了,大家散伙的好!”
有人梧住嘴窃笑:“人家那东西不中用,你怎么知道的,好像你见识过似的!”
那宫女也笑了:“后宫嫔妃好几千,我想见识也没那福分,多少比咱姿色强的人蚊子似的叮在那皮包骨头的身上,多少年啦,血早给榨干了,临幸过的姐妹都这么说。唉,也就是这会儿乱糟糟的能说几句痛快话,平素谁敢这么议论!有道是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好了,快看,火头小些了!”
朱棣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忘了指手画脚地指挥,他还是头一次听宫女如此讲出心里的实在话,这话是多少代帝王根本听不到的,他也忘记了发怒,平静地听她们说下去。等听她们说自己那东西不中用了时,他浑身一冷,衰老的凄凉倏地涌上心头,年轻时气吞山河的雄风哪儿去了?多少个夜晚,他赤条条地躺在柔软的罗香帐内,面对曾令他评然心动的玉体,却没了任何反应时,他总是这样问自己。但往事斯,一切却再也不会重来了。朱棣清楚这个道理,他只有深陷于无边的悲凉中不能自拔。
但是此刻,这种凄凉感只是一闪而过,他忽然在暗中阴阴一笑:“你们这帮贱人,也配议论朕么,你们不是嫌朕杀人太多么,朕就偏再杀几个叫你们瞧瞧,造孽?哈哈,朕贵为天子,干什么事情都不过分,哪里谈得上造孽?!”
还没想停当,朱棣已经如猛虎一样霍然站起,他挥动衣袖,冲不远处的几个锦衣卫大喝道:“快,将这几个没王法的东西拉下去,狠狠地折磨,将她们的骨头磨碎!”
声嘶力竭的喊叫盖过了火焰和呼呼作响的风声,紧接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朱棣摇晃两下,差点站立不住,好在忙乱中并没人看清。站在旁边的宫女们此刻才注意到身边的车辇,她们立刻惊呆了,僵立着说不上一句话,直到锦衣卫们冲上来,将她们拖拉走,她们也没呼喊出一声,似乎在梦境中还没清醒过来。
大火断断续续地一连几日才卜灭下去,青烟袅袅中,工部和户部大臣勘察了火情,随目写成奏折禀报上来,其日寸户部尚书夏原吉还在诏狱中面壁思过,奏折由户部侍郎代写了呈上。
仅仅几天,朱棣骤然苍老了许多,他斜靠在软榻上,哆嗦着手略微看了看,零星房屋不算,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在大火中全部化为了灰烬。朱棣心中有什么东西猛地扎一下,尖锐的刺痛,他又想起夏原吉说的,为了盖大殿,百姓辛劳十余年,像支撑奉天殿的七十二根巨木,都是上百年树龄的金丝楠木,从深山老林中砍伐运送下来,通常是民夫进山一千,出山时只剩了五百,不仅有汗,更多是血呀!朱棣又想起了那天救火时宫女们尖锐的议论,虽然她们此刻在诏狱中正为她们的随口胡言欲活不得,欲死不能,但仔细想来,未尝不是这个理啊!上天既然借了大火来惩戒自己,莫肖真的造了孽?!
朱棣默默地想着,他忽然有些眩晕,手指一松,奏折飘落在地上,蒙昽中,他听见有太监惊恐地呼喊:“皇爷,皇爷怎么啦?”
依照祖制,皇城宫城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皇上应当下所谓“罪己诏”来反省,还要让大臣上书直言,指出政令的过失。朱棣勉强撑起软绵绵的身子,在偏殿中召见群臣,他只是想做个样子,他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多的精力来听他们直陈过失。
但是令朱棣没想到的是!大臣们似乎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他们不知由谁打开了话头,你一言我一语地唠叨开来。一些人提出当初就不该迁都,南京乃金陵帝王之乡,盲目迁都到天寒地冻的北京,祖宗神灵不适应这里气候,怎么会有不怪罪之理?
对此朱棣并不特别在意,当初议论迁都时,反对的人就络绎不绝,此刻他们旧话重提也在预料之中。于是他强忍住浑身的不适,慢条斯理地说:“众位爱卿,当初迁都时,朕曾与卿等商议三个月之久,可见并肖草率从事,况且迁都之事,自古并不少见,只要宜国宜民,祖宗自然不会怪罪,这些就不必重提了。”
皇上一句话打住,这个话题自然就此结束。但随即而来的,是令朱棣颇觉难堪的北征。大学士杨士奇率先指出,若说迁都北京,大举修筑宫殿,虽然劳民伤财,但毕竟还有东西摆放在那里,足以流传后人。而北征却是将百姓的银子和性命丢进深潭中,丝毫没有半点必要,百姓怨望乃至上天告诫,也在情理之中。
大学士的话向来耿介,朱棣早领教过多次,看皇上不开口,似乎没发怒的意思,其余众臣大胆起来,附和着七嘴舌地说,北征确实有些鲁莽,未察清敌情便贸然出击,犯了兵法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