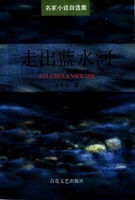朱棣脸腾地红了,呼吸急促起来,他明白众人遮遮掩掩的意思,他们里一定想,你不是坚持北征么,那战果呢,连敌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分明是叫阿鲁台戏耍了一通,还有什么面目指指画画?但朱棣无法反驳,他知道他们说的都是实情,明摆着的劳民伤财,任你再分辩也是徒然。但他不甘心就此成为他们议论的目标,若堂堂帝王任由臣子们指责,那君威何在?!
无名怒火汹涌奔流,朱棣终于遏制不住,他忽然拍案而起:“你们……朕这把年纪,尚且不避劳苦,深人大漠几千里,敌军遇没遇到暂且不论,你等这般目无君父,指指点点,成何体统?!左右,给朕将杨士奇拿下,他的兄弟杨荣还在诏狱中,让他去做个伴!”
偏殿大堂上顿时混乱起来,杨士奇大声辩解着什么,但朱棣奇怪自己却一点也听不见,到后来,满殿的臣子也开始身影模糊,他听到什么东西砰地闷响了一下,感觉软绵绵地躺在什么地方,异常舒,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皇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双腿发软,几乎站不起来,看他苍老的面容,已经彻底消逝了当年在战马上翻飞的豪迈。据太医讲,皇上肝火颇旺,心力急躁,力口之在漠北遭受忽寒忽热,风餐露宿,得了风湿之症。
群臣知道太医的话甚有道理,若不是肝火旺盛,心力急燥,皇上何以在大病之中,还要再次御驾亲征?不过这些风里浪里过来的大臣,都能揣摩出皇上的心思。上次在偏殿中直陈过失时,你们不是嫌我劳而无功么?我这回就偏要再次出师,拿回战功来叫你们瞧瞧!他们太了解皇上的脾性了,这种既让他自己尝不到甜头也让百姓和大臣吃了不少苦头的禀性,众人都知道,谁也没办法改变。
出于这种原因,朱棣要往驾亲征再次出兵漠北的诏旨颁出后,意外地没一个大臣站出来反对,大家商议好了似的三缄其口。这一次北征,朱棣将心中的火气发到本已臣服的阿鲁台身上,既然有人觉得是他戏弄了朕,朕就将他捉回来,叫你们看看,戏弄朕的人是何等的下场!
向来跨马驰骋疆场的朱棣,头一次坐上了车辇出征,他心中很不舒爿,但像他这样站在地上都有些头晕目眩的境况,怎么能坐稳马背抓住马缰?他不甘」已、,却也无可奈何。大军这次做好了远征的充分准备,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之后,追随着比大军更长的辎重队伍。出动了大约有三十五万匹骡马,近二十万辆粮车,还有二十多万民夫往来奔忙着运送军粮。但即便这样雄壮的队伍,进人到沙漠中时,却突然显得单薄,天地之间,再多的血肉躯干也是如此渺小。
大军走得相当缓慢,当行进到阿鲁台驻地附近时,前锋传来消息,俘获了几个阿鲁台的音属,他们声称阿鲁台得知大军前来兴师问罪,自知不是对手,已经匆忙向北迁徙,具体迁移到了什么地方,大漠茫茫,谁也说不清楚。
校尉轻声慢语地禀奏着,朱棣感觉浑身冰冷,预期的激战成了泡影,战功自然也就失去了着落。“难道又是上一回的重演么?这样如何回到北京?”朱棣暗自思忖着,表面不露声色,面无表情地挥挥手叫他退下。等校尉走出了营帐,朱棣才似山崩一样地轰然倒下,他眼前闪现出当年靖难之战中,一幕又一幕生死激战的场景,闪现出自己满脸蒙上灰尘,将士们只有听声音才辨认出这是他们首领的场景,还有那插满了箭矢,如同刺猬一样的旌旗,多么令人神往啊!可是这一切都成了隔岸的风景,成了明日的黄花。朱棣感觉现实与梦幻相交错,他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
滞留在茫茫大漠间仓皇迷惑日寸,终于有个叫人心动的消息传来,鞑靼王子也先土率领自己的部从,前来归附大明。消息传到中军,朱棣长出口气,他有种溺水后抓住根木棍的感觉。他立即命令也先土赶来觐见。结果令朱棣格外惊喜,也先土不像阿鲁台那般胡人气息十足,他更有几分文弱的神情,谈吐十分文雅而且谦卑,相比之下,朱棣贝出奇地热诚,特意赏赐给也先土旌旗旌表,并摆出一桌丰盛的往宴犒劳这位王子,虽然自己不能亲自奉陪了,但筵席的隆重,仍让也先土感动不已。
带着这样一个战果,朱棣开始漫长的返回路途。但不知怎么回事,心中没了那揪人心弦的争斗,朱棣再也挺不下去地躺倒了。摇摇晃晃的车辇在沙漠草甸中艰难跋涉,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尽头。而朱棣却已经意识不到这些,他混沌的头脑里翻检着生命当中的一件又一件大小往事,一个又一个鲜活人物。他的世界已经开始缩小到脑海深处。
昏睡了两三天之后,朱棣终于目争开眼目青,看看侍立在身旁的内侍,张开嘴微弱地叫道郑和,郑和,你从西洋回来了么?”
那内侍闻言一惊,但立刻明白过来,忙凑近了轻声说:“陛下,奴婢是黄升,郑公公此刻或许正在西洋的某个地方为陛下播扬我大明国威呢!”
“哦,”朱棣轻嗤一口气,仔细再看看,终于辨认清楚了,眼前这个确实是黄升,黄们的干兄弟,两人身材相似,话音也差不多,“黄升,现今大军到了何地?”
“禀皇爷,刚到翠微岗。”
“你估摸着什么时候可到北京?”
黄升眼珠转动两下,弯腰说道:“皇爷,从来时的情形看,奴婢估摸着到北京恐怕得八月过半了吧?”
朱棣沉默片刻,忽然提高了声音:“速传朕的旨意,叫夏原吉来见朕。”
“这……”黄升一愣,旋即明白过来,爬在床榻旁嗫嗫着说,“皇爷,夏尚书此刻正在北京诏狱中呢,皇爷……”
朱棣摇摇头苦笑了:“那就召杨荣来见朕好了。”
黄升这次伶俐了许多,忙接口说:“皇爷,杨学士他,他也在北京……”
朱棣却再笑不出来,他痴痴地盯了弯曲女天穹样的帐顶,良久才徐徐说:“朕身边还有谁?”
黄升不知他问的什么意思,但也不能再犹豫,略想一下禀奏道:“皇爷,大学士金幼孜就在帐外附近,皇爷若要召见,奴婢这就去叫。”见朱棣疲惫地点一下头,忙爬起身退出去。
金幼孜匆匆赶来时,朱棣正直眼望着吊了棉帘的帐门,秋风呼啸着从四周旋过,声音如同群狼长嗥,凄厉得动人心魄。看金幼孜来到近前,朱棣努力微笑了一下:“爱卿虽为大学士,倒也经常在地方官府中行走,爱卿看,朕所倡导之永乐盛世,可否还算名副其实?”
金幼孜显然没料到皇上见面会劈头问起这话,但看看他枯黄的面皮和无神的双眼,立刻也就明白了,犹豫片刻才拱腰回话:“陛下圣明,陛下自登大位以来,致力百姓生计,现今国力较洪武年间大为增强,百姓蕃息,人口大增,此等情形,有目共睹,陛下不必生疑,尽可放心息身子。”
朱棣听得很认真,脸上并没什么表情,等他小心翼翼地说完了,沉吟片刻又:“朕的人?”
“陛下文韬武略盖过秦皇汉武,举世公认,自不待说。”金幼孜说过一番话后,逐渐缓过神来,话语流畅许多,“陛下文治武功堪称双绝,编修永乐大典,远播国威于西洋诸国,亲征漠北,南征北战,为巩固北疆,又修葺北京,将国都北迁,臣遍观史书,能做到这些一半的,已是寥寥,堪与陛下比肩的,臣还未看到。”
朱棣忽然露出微笑,摇摆一下枯瘦的手臂:“爱?不必再说下去,朕明白了。”
金幼孜不清楚皇上到底明白了什么,但他赶忙住了口,垂手站在一旁。彼此沉寂片刻,朱棣忽然幽幽长叹口气夏原吉和杨荣、杨士奇都是朕的忠臣,爱卿回去之后,当立即将他们释放,朕之后人,就要靠他们来辅佐,大明江山兴衰全在你们了。”
“陛下何出此言?”金幼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忙翻身跪倒章,“陛下些须微疾,不必思虑这么多,待不日还京后,一切再从容计议不迟。”
朱棣不以为然地摇手笑道:“任你使尽家中财宝,难买无常生路一条,这个道理,朕岂有不晓得的?唉,荣枯在天,生死由命,朕还是能想得开的。不过百姓们讲,瓦罐儿少不得井上破,尿盆儿再刷也是臊,万物皆有本性,朕向来自诩为马上皇帝,能死在这营帐中,也就甚感欣慰了。”
“陛下!”金幼孜从未听皇上如此随和地说过话,心头涌过一阵难以言说的感觉,张张嘴却不知再说什么好。
朱棣面色平静地招手示意他平身:“爱卿,快准备纸笔,朕有几句话要说。”好在营帐旁侧御案上摆放了文房四宝,金幼孜转身捧过来。
“朕一生驰骋,功过在心也在天,任后人评说去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近日将前尘后事思虑再三,深感天下百姓跟随于朕,疲意有加,望后继者体恤民情,以休养生息为治国上策。北京城中被天火烧毁的三大殿,不必修复,漠北再有战事,以守为主,切莫穷追,所有政令,当考虑百姓负荷为先。朕之殡葬,礼仪尽量从简。大位传于皇太子,一应不到之处,皆以太祖祖制为准。”
朱棣一口气说这么多,似乎有些劳累,他合上沉重的眼皮,喘几口粗气,转脸盯住金幼孜,脸上流露出一丝诡秘的笑意,忽然放轻了声音说:“爱卿,朕知你素来忠直,有句话还要交代,朕去之后,地府沉沉,未免寂寥,朕欲让后宫中朕曾召幸过的嫔妃追随陪伴朕一程……这个就不必记下,爱卿传朕口谕也就是了。”
金幼孜闻言一愣,猛地抬头,正与朱棣浑浊却意味深长的眼光相遇,他迟疑一下,抖动嘴唇答应道:“陛下放心,臣……遵旨。”
帐外风更猛了,卷起的股股黄沙漫天飞扬,天地之间一片苍茫,千军万马行走在茫茫荒原上,似乎永无尽头。此刻中原大地上,大江南北百姓正忙于收获辛苦一年的收成,郑和也正航行在西洋尽头的各个角落,卖力地播扬大明国威。天地尽头响起“吾上国永乐皇帝万岁,万万岁”的呼喊时,朱棣已经魂魄随风而散,飘扬在苍茫宇宙洪荒中,所有的一切,都逐渐地成为了过去。
皇上驾崩的消息传至北京后,京城顿时一片混乱。皇太子朱高炽派遣长子朱瞻基远赴开平迎接灵柩,当即释放出夏原吉等人,商议妥当后,率领文武百官在长城内居庸关下哭迎先帝。新皇即位后,将父皇朱棣和母后徐妃合葬于京郊昌平县天寿山的长陵,尊其谥号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当金幼孜将先帝私告自己的口谕禀奏给新登基的皇上后,新皇当然不敢违背。后宫上百妃子在哀哀哭泣中,被赏赐了一顿精美的盛宴,之后有太监过来,每人扶住一个,将她放在张张小木床上,小木床的正上方悬好了一个个的绳套,太监帮着她们将头伸进绳套中,一声吆喝,啪地将床上活动的木板齐齐抽开,看着吊满房屋的宫妃,新皇欣慰地想,这下父皇的在天之灵该不会寂寞了吧。
正如朱棣所担的那样,朱高炽身子不结实,即位没多长时间,便很快步自己后尘而驾崩了。不过,也正如他立皇太子时听从解缙的建议所想到的,他的皇太孙此刻已经成长壮大起来,顺利地接替了皇位,国号宣德,而宣德皇帝英武聪明的劲头,也正应了他的初衷。
向来不安分的朱高煦和朱高燧在这场皇位的接连交替中,觉得大好时机已经到来,便趁朱瞻基年轻并且刚即位,扯起造反大旗,一如父皇当年夺取他侄子建文皇权时的靖难之战,历史仿佛轮回了一周,又开始重新演绎。然而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运气和谋略却远远不及乃父,他们刚刚起事,朱瞻基便听从大臣建议,御驾亲征,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结果两个叔叔很快被生擒活捉。
朱高燧再次表现出过人的机敏和应变,俯首认罪,被贬斥了事。惟有朱高煦抱着自己侄子未必敢拿自己怎么样的念头,倔强地强硬到底,结果让自己侄子罩进一口铜缸中,四周堆上柴草,在熊熊烈火中,桀骜的朱高煦化作了灰烬。
不过,这是永乐朝以后的事情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歇,它总在栉风沐雨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