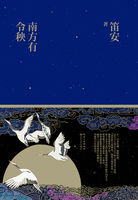正如朱高燧所说的,《永乐大典》编修完成后,道衍便决意离开南京了,临行之际,金忠相送,走出三山门巍蛾的城楼,步出江东桥,一直来到宽阔的长江岸边。江水正碧,水天一色,江风阵阵涌来,吹起道衍过于宽大的僧袍,衣袂招摇,飘飘欲仙。
“师兄真的要走么?”金忠面带几许依依,还有些赧然,“可惜小弟不知为什么,忽然厌倦了漂泊,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朝廷颐养天年,横竖现在天下太平,也不至于再帮着出主意涂炭生灵。师兄年事已高,江湖之苦还是少吃些的好,留下来吧。”
道衍确实更显苍老了,虽然秃着头不见白发,但眉须和面色都透着沧桑,他望金忠笑道:“师弟脸红什么,老僧并未责怪你违背前言,为人最好的结局,无过于能做到,提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撇得下。今看来,你我二人,可以无愧了。师兄要走,是因为该做的已做,师弟不走,是因为该做的还未做,并无对错可分,又何必自责,也不必阻拦。”
金忠见道衍看出了自己0底隐藏的东西,脸色更红,吃吃地说:“师兄此去,要往何方?”
道衍看看似乎从天际而来,又似乎向天际流去的滔滔江水,挥挥风中的衣袖:“事有机缘,不先不后,刚刚凑巧命若蹭蹬,走来走去,步步踏空。万事自有定数,预先思虑,不过徒费精神,师弟就不必过问了。”
“那……”金忠还要再说什么,一叶扁舟飞快地靠近,船夫双手持桨叫道:“是两位师父雇的船么?现在正是顺风,快些走吧!”
道衍若有所思地看金忠一眼,转身向船上走去:“不是两位,是一位,该渡的渡,不该渡的勉强不得。”
金忠似乎听出了话中有点意思,他来不及细想,小船已经悠然荡开,随着波浪忽高忽低,宛如飘摇在浮云中,倏忽间化作一个黑点,渐渐隐没在碧涛里。金忠痴痴地站立良久,激荡如雪的浪花飞溅上岸,打湿了衣襟,他浑然不觉。
自从住进比起王府更加威风森严的东宫后,朱高炽一直就不大安稳,总觉得一颗心高高悬起,总有什么东西让他放不下而提心吊胆。沉静的不眠深夜里,他常常会想到朱高煦孔武骄横的面,也偶尔在眼前闪现出朱高燧嘴角撇出诡秘微笑的神情,他知道自己这个太子位置招惹了两个弟弟’两个性格迥异合起来却廿相得益彰的弟弟,他们联起手来,自己从哪一方面都比不过他们,为此他惴惴不廿安,总预感到他们不可能善罢甘休,意料不到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
可是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他自己根本无法想象,这就更让他窒息般地心悸。好在有金忠这样一个久经风浪的谋士在身边,彼此虽然没明说过眼下的情形,但金忠似乎有意无意地多次提到要本着一颗正,以不变来应万变,大概算!是最好的主意了。
父皇亲征,自己监国,说是监国,其实也没什么事情要做,琐屑小事有各部主持,略微大些的要禀奏父皇行在,由他决断,监国不过挂了个名声而已。不过朱高炽乐得自在,觉得这样反而更好,省得招惹是肖上身。
前两天,郑和带着满身的海腥味赶回南京,得知皇上远在边关,便依照旧例,向监国的太子禀报沿路情形,一个说得绘声绘色,使沉闷的大殿活泼许多,一个听得津津有味,聊以打发心头的郁闷。
郑和率领的巨大船队,在颠簸不平的海面上连续航行了数十个昼夜,终于迎来了一块陆地,上岸打听,原来是占城。占城对于郑和来说并不陌生,也不神秘,早在洪武时候,占城国的国王就派遣使者来到这个中原大国,向洪武爷进贡了大象和狮子以及他们的特产。洪武爷也以礼相待,赏赐了大量绸缎和瓷器,并颁发诏书,封占城为中原属国。
虽然早就听说过,但亲眼看到这个风俗奇异的国度,郑和还是耳目一新。当时的国王叫占巴,他戴一顶出奇高的帽子,帽子上缀满各色鲜花,披件大红披风,双臂上十余个玉镯互目碰撞着叮当作响,半男不女的样子既庄重又可笑。
国王乘坐一头同样花枝招展的大象,走在迎接队伍的最前边,左右簇拥着数百侍卫,个个裸着上身,脸上用油彩描画得五光十色,敲起皮鼓,吹响椰壳笛,分外热闹。跟在后边的大臣装束也相差无几,怪模怪样却神色严肃。
一行人来到宝船前,国王抬手轻轻一拍,大象温顺地屈膝跪倒,让主人轻巧地走下地面。国王占巴率领百官跪地叩首,迎接上国远来的使节。郑和也拱手答礼,让通事用占城方言宣讲了大明天子的殷殷厚意。然后他们在使馆中受到隆重的招待,宴席非常丰盛,满是异国风情的菜肴,占巴还献上三百根象牙和一百根犀牛的角,权且作为供品。
在占城逗留数日,舰队又劈波斩浪,继续向西航行。过了占城后,沿海岸分布的大小岛国渐渐稠密许多,历经有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和阿鲁等国家,最远一直到伸出海岸很远的一个大岛尖端的国家,叫古里,因为距离遥远,郑和从未听说过这个国名。为了表示纪念,郑和特意命人在岸边建造一座凉亭,里面树起一块石碑,刻下铭文说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苦,然笃朴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
虽然国度众多,但风俗习惯却同占城大同小异,岛中民众大多还是破衣烂衫,茹毛饮血,一副不开化的情形,仿佛叫人又回到史书上记载的千年以前。岛上的国王和臣民见郑和他们身穿鲜亮的绸缎绣袍,举止文雅,如同从天而降的仙人一般,羡慕得双眼冒火,当即就有许多国王派遣大臣登上宝船,要来参拜上国的国君,还巴结讨好地献上各种宝石和珊瑚之类的珍奇宝物,至于金银珍珠,就更多得数不清楚。
“公公如此风光,足见我上国的威力,不过既然他们民风荒蛮彪悍,就没遇到什么凶险么?”朱高炽听得人神,暂时忘了烦忧,忍不住插嘴说。
“殿下英明,怎么会没有,常言说出门一里,不如屋里,凶险倒是凶险,只不过有惊无险罢了。”郑和连忙作出夸张的神情,娓娓讲来。
那是在爪哇国附近的旧港,这个地方很是特殊,虽远在大洋,首领却是流亡海中的中原人,叫陈祖义。他纠集一群渔民,占据此地,不去做正经营生,专门拦截海上往来船只,杀人越货,不折不扣的一帮海盗。
郑和听爪哇人讲起这种情形,深感有损中原大国的面子,便答应替当地百姓除去这一大害。
本着先礼后兵,未到旧港时,郑和先行派人乘小船前去,以大明皇帝的名义叱责陈祖义,要其束手缴械,收拾行装跟随舰队返回中原。陈祖义倒也乖巧,见对方来势汹汹,深知不好对付,便听从身边人的建议,来个诈降。并随同使者带上酒肉等精美食物,送到大船上,其实是要暗中探看整个舰队的装备,以便伺机。
听陈祖义纟此识相,郑和颇为满意,正要命令大船靠岸,接受陈祖义投诚时,陈祖义咅下有个叫施进即的同乡,平素在陈祖义面前阳奉阴违,总想找机会取而代之。眼下见郑和大军来到,觉得机会再好不过,于是就悄悄潜人船队中,将陈祖义的阴谋报告给郑和。
郑和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也分不清谁真谁假,但此等关乎性命的大事,他还是宁可信其有,指挥舰队上的兵马,一部分埋伏在岸上,一部分在船上戒备。
当日夜中漆黑一团,加之阴雨时不时地飘洒,阴风阵阵,虽然人多势众,但众人还是提心吊胆,睁大眼目青望着什么也看不见的远处。
半夜时分,果然有点点火把闪烁,悄无声息地向岸边摸来。陈祖义率领手下精兵劲卒约三千余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郑和设下的埋伏圈中。正当他们要登上大船放火烧杀抢掠时,周围号炮接连响起,灯火通明照亮远远近近的海滩,待陈祖义回过神来,才发觉他们已被数万明军团团围住。
郑和铠甲整齐,在灯光下熠熠闪亮,大红斗篷高高招摇,如同天神突降,神情威严地大喝道:“陈祖义,你这中原败类,将大明朝的脸面丢在西洋各国,还不快快投降,否则定将你剁为肉酱!”
话语铿锵,不怒自威,令陈祖义和手下兵众不由不为之折服,再看周围刀林廿枪丛,要闯出去已万万难能,只好纷纷扔掉刀枪,匍匐在地,叩头求饶,乖乖地被:捆绑起来,扔进各船的舱底。
“那,施进卿卖主求荣,自然也非善类,难道就成全了他不成?”朱高炽听着!又忍不住插嘴说!
“殿下英明,他们狗咬狗,按说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郑和施一,赶忙回答!“可惜他们在那里经营许多年,已经根深蒂固,我们远道而来,要彻底清除他们,
也殊肖易事,想来想去,只好就此打住,算是对施进卿恩威并用,叫他从此有所收敛。施进卿感恩戴德,再三表示臣服大明,并叫他的女婿随船队来觐见陛下,奉上贡品。”
直着身子坐了半日,朱高炽挪动一下肥胖的身躯,赞许地看着郑和微笑道:
“郑公公风雨飘摇了这多时日,播扬国威于万里之遥的海外,真是难能,尤为可贵呀!正好金忠要到北京去代本宫遥迎父皇,顺便带上些奇特的贡品,叫父皇提前高兴一番。公公可好生歇息几日,待父皇回京后再觐见禀报。”
郑和见朱高炽面色疲倦,额头上明晃晃的竟似乎有些冒汗,赶忙答应着告退下殿。朱高炽长舒口气,他惊喜地想,正不知如何去迎接父皇呢,可巧郑和来了,
多带些宝物,或许自己的位置就会更稳固。想着召过一个小太监:“快去请金忠,
赶赴北京的日子要提前几日才好。”
故地重游,金忠确实别有一番感慨,当初自己孑然一身,千里迢迢到北平来谋求干番事业。似乎就在一晃间,秋月春风转换了几轮,当年的雄心壮志已经随风不知飘散到哪里。而今在众人眼里,自己算是功成名就了,可怎么就找不到当年神往的那种感觉呢,反而空荡荡的叫人觉得如此不踏实。还是师兄道衍看得开呀,怪不得他说,功名事业这事,往往来如风雨,去如微尘,不可不看,又不可看得。
那自己是否应该跟着师兄离开了?金忠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自己,也很多次地这样想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留在了喧嚣的尘世中,他总觉得这里还有些东西让他留恋,功名?官位?抑或飘渺如风的所谓事业?他自己也说不清,但他的确留了下来。
“大人,前边的城墙便是北京了。”有个声音响起,让马铃叮咚中昏昏欲睡的金忠激灵醒来。他从车内探出头,是跟随的侍卫杨胜骑在马上拱手向自己说话。
“嗯。”金忠含糊地答应一声,看看宽阔驿道尽头处的高大城墙,比起南京城来,它越发冷峭,孤零零地耸峙在荒芜四野上。这座饱含威严的城池,当初是自己人生经历的起点,现如今,经过多少人的热血沐浴,它仍无动于衷地静默无语,仿佛全然不知自己的名字已经改作了北京。依了皇上的意思,也许不久,它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京城。几年来北京一直大大小小地建着宫殿,到时候里里外外必然会重新修建,北平或者北京耳目一新日寸,到底是自己还有师兄还有皇上的功德呢,还是罪过?
金忠默默地想了片刻,杨胜和另外几名护卫扬鞭打马,赶在马车前,气势顿时威严许多,朝廷重臣的派头显现出来,稀稀落落的百姓惊慌地四下躲闪。
朱棣的行营仍在昔日燕王府中,斑驳陆离的宫墙被赶抢着粉刷一新,空气中还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早就得到消息的朱棣很是欣慰,战场上重展雄风的喜悦还未退去,郑和从西洋返回,并且还征服了许多海外小国,更让他激动不已。大明朝的国威,在自己手里,已经远远超出父皇洪武帝的影响,这足以说明,自己是帝王的材料,在天下人眼中,应该名正言顺了。
春风得意中,金忠将郑和带来的宝物一一献上,朱棣爱不释手地逐个仔细摩擎,一边漫不经心地问讯着南京的情形,金忠倒不特别紧张,详略得体地奏对过,朱棣满意地连连点头。
“好,太子能将国事料理得如此有条不紊,朕也就放心了,不过这里面爱卿的功劳当属第一呀!”朱棣眼光不离那些珠宝玉器,仿佛根本没费什么心思。
但金忠却敏锐地听出了朱棣心底的声音,看来他对自己反复斟酌才犹犹豫豫立下的太子,仍不十分可意,只不过木已成舟,不便再明说罢了。金忠虽然端测出来,可皇上没直接说,自己就不能捕风捉影。本来他是想在皇上跟前赞美几句太子的,现在赶忙收回,以免叫皇上听出自己的什么弦外之音来。多少年的交往,金忠深知,朱棣自己常常要玩弄些不大不小的聪明,却对别人在自己艮前卖弄心计深恶痛绝,他得小心在意。
见金忠唯唯诺诺,朱棣愈发高兴起来,捧起一个碧玉雕刻成的龙状手镯,在光亮中眯起眼睛仔细看看:“这种玉温润细腻,最能滋润肌肤,让权妃佩上,实在天然一色,美丽绝伦,好,金忠,你一路风尘劳顿,先下去歇息吧,有什么事情明日再商议。”
陪侍的近臣知道朱棣心思,忙知趣地拜辞退下,未等他们走出大殿,朱棣已经风风火火地转到后殿,找权妃去了。
金忠一行的到来,原本也是成为常例的臣子礼节,朝廷上下都没人觉出什么。北京昔日的燕王府现在成了皇上的驻跸行营,以前徐妃曾居住过的隆福宫,此刻主人贝换成了权妃,其余跟随来的嫔妃如吕妃等人贝合住于隆福宫北边的兴圣宫。太液池正是绿水荡漾的时节,波光掩映下,两座宫殿红绿女子进出往来,娴静美妙。
但隆福宫旁侧的偏殿中,使女翠翠却无意流连这些,她内心正掀起阵阵狂澜。就在金忠他们进城的第二日,一个人忽然闯进自己房中,他身穿太监衣衫,却面色沉毅凶猛,两眼闪烁着刀锥般的目光,眼角旁还有不大显眼的一块刀疤。
“你……”翠翠不由得抬高声音,她下意识地觉察出这个从未见过的太监绝5非正经太监,心中扑通直跳。
那人却上前一步,轻嘘着示意她不要声张,晃晃手中玉佩,并紧接着压低嗓袁门说:“翠翠姑娘,切莫惊慌,在下是奉了皇三子之命,特意拜见。”!
听说是奉了皇三子之命,又见到那个熟悉的信物,翠翠果然立刻镇静许多。满脸关切,迫不及待地问:“皇子他,他叫你来做什么,莫非他惹到了什么麻烦!”
那人见状放下心来,不动声色地一笑,机警地看看四周,大正午时分,夏日的太阳雪亮地照着院落,既无人声,更无人影,这才放缓了语气:“姑娘,皇三子眼下正有大难降临,要姑娘从中周旋,或许可以保住性命。”
“啊?”翠翠差点又失声叫出来,俊俏的脸庞有几分扭曲,“皇子他,他贵为皇子,能有什么大难,我,我一个女子,怎么周旋?”她紧张得喘气急促,简直说不上来。
“姑娘不必着急,听在下仔细交代清楚。”那人倾耳听听外边,确无动静,“正因为他是皇子,才大难临身。姑娘自然知道,当今太子既无才能,更无功劳,只因为早出生一两年,结果成了东宫太子。当时二皇子仗着自己曾立过大功,心里不服气,在人前人后说过些不满的话,于是和当今太子结下了冤仇。皇三子当时出于公心,也帮着二皇子说过几句,结果太子便迁怒于他,将他们都看成心腹大患。
现在皇上远在北京,朝廷里由太子监国,他便趁势为所欲为,想将两个弟弟随便安个罪名,胡乱处死……”
“啊?”翠翠又是吃惊地掩口喊叫一声,“那他,他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