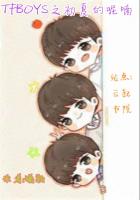“手臂受伤了,在医院缝针。”周日下午陶阿诺冷不丁的收到朱子函的短信,本来打算抱怨他终于想到发短信给自己了,看着短信内容突然像吃了一大口白山芋,咽到了。
“怎么会受伤?”陶阿诺满心的关切,不知从何开始说。
“******,疼死了!我怎么这么倒霉,都快毕业了,工作没找到,手臂又受伤了!下周不回学校了,我向班主任请了一周假,你帮我给班长说一下。”朱子函答非所问。
“好的,你放心吧。真希望能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知道你受苦,好心疼。”陶阿诺觉得这句话说得挺矫情,不过经常跟子函说些矫情的话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又是在这么特殊的时刻,简直是“肆无忌惮”。若不这样说,就想不出别的话好说了,其实阿诺心里更想说的是:“怎么这么不小心;手臂受伤会这怎么会严重到需要缝针;那就好好修养呗,有什么需要说骂人的话;抱怨这么多有什么用,自己受伤的还怪谁??????”这些话,即使是情商不高的陶阿诺也知道不适合现在说出口。既然想说的不适合说,就只剩下编造出来的劣质芝士一般有着塑料口感的关心话了。
到了周一晚上,朱子函打电话过来,陶阿诺才弄清楚受伤的前前后后。
周日下午朱子函约了朋友去打篮球,抢篮板时摔了出去,本打算扑到铁丝围网上,谁知网上生锈翘起来的一根铁丝在手臂上划了一个大口子。之后马上到医院缝了五针,虽说是皮肉伤,毕竟伤口深,又是有铁锈,需要扒开清洗干净,确实让朱子函受了不少罪。
接下来的几天,陶阿诺每天发短信关照子函“伤口怎么样了?还疼吗?”子函每次都认真回答,描述自己伤口的情况,“上午去医院换过药了,平时还好,就是换药的时候疼死了。”对此,陶阿诺又感动又内疚,因为在她看来,伤口总会一天比一天好,毕竟是很简单的伤,又不是什么疑难杂症,所以虽然每天去询问,但都不过是敷衍。不是不关心,也会心疼他痛苦,只是再说多少有什么用呢?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
一周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周日晚上,朱子函让陶阿诺帮他在学校附近订一间快捷酒店,因为他伤口没有好,行动不便,不想住宿舍。
陶阿诺虽然满心埋怨他太娇弱,要知道住酒店一天就是一百多呢,睡觉的地方而已,但也不想做个扫兴的人,周一一大早就去预定了。
陶阿诺再次见到朱子函是周一的课堂上,她特意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在自己边上留了一个位置。
课前,陆晓杰晃悠着着二郎腿,歪着头挑衅的问:“今天陶阿诺同学怎么跟我们这些学渣一起抢后排的位置了?”
反正是开玩笑,不求答案,陶阿诺心知,也就仅已微笑作答。
上课开始十分钟之后,陶阿诺隐约感觉到窗外有个人影在逗留,刚转头看,朱子函已经拿着一本课本走了进来,两步走到陶阿诺边上的座位坐下,又小心翼翼地把手臂放在课桌上。
“讲到这里了。”陶阿诺马上凑过去帮他翻开书本。
朱子函顺从的打开书,没有说话,把头埋得很低,像是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接下来的时间,陶阿诺跟着老师讲课的节奏翻了五页,朱子函随着自己内心的节奏在放心地拿手机玩了五局斗地主。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下课铃还没响,朱子函就提前走出教室了,陶阿诺看了看时间还有五分钟下课,也就跟了出去。
“去吃饭吗?”陶阿诺觉得作为一个称职的女朋友,自己应该在子函伤病的时候承担起他生活起居的琐事。
“回酒店,买点外卖带回去。”
陶阿诺看着穿薄款冲锋衣外套的朱子函,似乎又瘦一圈,原本是纯粹黝黑的皮肤,现在更是黑里透黄,已经瘦到皮包骨头,偏偏人长得又高,大风能吹倒的样子,憔悴的让人不忍心多看。
陶阿诺送朱子函到了酒店房间,陪他买了外带的馄饨和为第二天早餐准备的面包,自己就回学校了,回去应该还赶得上食堂的午饭。
陶阿诺下一次收到朱子函的短信是第二天的中午时间,而上午的课程朱子函意料之中的翘课了,陶阿诺也没有叫他来学校,反正来了也是玩手机,何况还要拖着一条受伤的手臂。
“我准备下午去医院换药,你有时间吗?”陶阿诺收到短信时正拿着一瓶酸奶在图书馆看书。
“有啊,我陪你去吧。到学校告诉我一下。”朱子函住的酒店离学校很近,况且公交车站就在学校门口。
当然,后来他们打车去了第一人民医院。
到了医院,朱子函摸索着找挂号,找交费处,找换药室。陶阿诺只跟在后面一会儿慢走几步,一会儿屁颠儿屁颠儿小跑一阵。她自己从来没有独自来过医院这种地方,偶尔的几次到医院都是家人帮忙搞定,自己只要配合医生听诊检查就好,况且,即使这么大人了还是改不了闻到消毒水的味道就怕的习惯,所以对就医的程序一窍不通。
跟着朱子函顺利到了换药室,陶阿诺不由的心生敬佩,不管是多么强悍的女孩子总是乐意看到自己男朋友比自己更强大的。
换药室的中年女医生烫卷了的短发夹在护士帽和口罩之间,显得挺和蔼,朱子函看着镇定而礼貌,陶阿诺反倒是有点局促不安,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医生边上还是站到门口等着。
阿诺正犹豫着想退后几步到门口去等,听到医生说:“来帮你朋友拿着外套。”这才看到朱子函已经脱下了外套,一只手伸出来正平举着。
好不容易有体现自己这个陪同价值的时候,还差点掉链子,陶阿诺自责着,一个大跨步向前,接过外套,果然被朱子函瞪了一眼。
医生一圈圈取下朱子函伤口上的纱布,慢慢的露出沾有血水的地方,朱子函颤抖一下,显然不安起来,另一只没受伤的手握起了拳头。陶阿诺怕会看到鲜血淋漓的伤口,就站到医生背后两步的距离,这样阿诺,医生,伤口三点一线,就能确保看不到伤口了。
随着医生放下剪刀拿起镊子的几声金属碰撞的清脆响声,朱子函终于还是从胸腔里发出一阵闷响。陶阿诺虽然想象不出那是多疼,但也双手紧握搓出汗来。
“好了,伤口恢复不是特别好,明天再来换药,如果还是这样,最好去打三天吊水。”医生利落的收拾着换药的托盘。
朱子函站起来整理衣服,已经完全恢复平静的神色,只有额头上一层薄薄的汗水还微微反光。
从医院出来,朱子函皱着眉头把自己手里装病历本的小包塞到陶阿诺手里。她虽感到不太开心,但想到毕竟朱子函是个“伤员”,也怪自己没有想到帮他拿东西。
他们沿着人行道走,到了最近的公交站,陶阿诺不甘心地反复看着公交站牌。医院离学校不远,走路也就半小时以内,偏偏就是没有直达的公交。
“打车回去?”陶阿诺心里想,回头看子函一言不发地只是跟着自己走,转念又想“说不定再走一站,前面的公交站就有车直达学校了。”
走了一段,快到交叉路口的地方,朱子函停了下来,全身骨头都垮掉一样,向右边耷拉着头,眼神愤怒、疑惑又无奈。
“怎么了?前面就是车站了,说不定有车可以回学校。”陶阿诺看出子函托着手臂步行走得委屈,又不知如何是好,明明已经可以看到前方的公交站了。
“要走你自己走,我现在身上还有伤口呢,我走不动。”朱子函说完眼睛一翻,转身开始关注后方开来的出租车是不是空的。
“哦,你没说嘛。”陶阿诺对朱子函的态度很不满,只是不想吵架,便忍着,跟他一起等出租车经过。
第二天三点还没有收到朱子函的任何信息,陶阿诺坐在自习教室里开始两分钟看一次手机,但每一次看都会增加自己对子函的埋怨与愤怒。到了五点钟,陶阿诺还是决定主动打电话过去。
“子函,你去换药了吗?”电话接通的一瞬间,陶阿诺突然决定强压愤怒,努力温柔地说。
“换过了啊。”朱子函漫不经心的语气,听起来心情不错。
“你在哪里啊?”
“怎么了?”朱子函戏谑地轻笑着。
“你在什么地方?怎么听起来环境很吵?”朱子函的态度让陶阿诺实在摸不着头脑。
“呵呵,你有什么事吗?”朱子函更加肆意的笑。
“听说一家石锅拌饭不错,我们去吃好吗?”陶阿诺中午在宿舍听到几个女生叽里呱啦地齐声赞叹了学校后面巷子里的一家小餐厅,听说价格实惠,分量足,当时就想着和朱子函一起去试试。
“??????想请我吃饭?”朱子函略带吃惊的问。
陶阿诺只是听说一家好吃的小店,距离又近,很方便,至于谁请谁倒是没想,被子函这么一问有点别扭,还是一口答应了。
“在哪里?”朱子函终于收起了玩世不恭,认真地和声问。
“就在学校附近。”
“可是我过去不方便??????我也不太想折腾??????”朱子函声音飘忽。
“离你住的酒店很近啊!”陶阿诺一头雾水,不知道朱子函在含糊其辞些什么。
“我不住在那里了。”朱子函含糊半天终于说了一句让陶阿诺能清晰听到的完整句子。
“不住这边了?那你住哪里?为什么要换房间?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陶阿诺怎么也没想到朱子函竟然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一般独来独往,一连串的发问几乎没想听回答。
“我现在住在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每天换药就不需要折腾了。”朱子函确定陶阿诺问完了,安静了两秒才轻松的回答。
“如果我不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陶阿诺已经愤怒到冷静的毫无人性。
朱子函轻笑几声,算是回答了。
陶阿诺紧握着手机,咬着牙,说不出一句话。
“我在网吧打游戏,没事的话,我就挂了哦。”朱子函打破了沉默,然后又迎来新的沉默,大概过了一分钟,两个人都没说话,朱子函先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