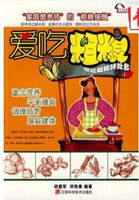月白也不是蠢钝之人,见容子奕此状便知无谓再瞒,唯有将头伏得再低些,请罪道:“公子慧眼,奴婢确是欺瞒了公子,求公子降罪。”
容子奕弯下身,虚扶一把,道:“姑姑还请起来说话,我知你身不由己,并无怪罪之意。”
月白的心怯怯起了身,福一礼道:“谢公子不责之恩。”
容子奕踱开几步,拣一张椅坐下,又示意月白也坐。月白自是不肯,容子奕便起身亲请一趟,二人方才对坐下了。
吃一口茶,容子奕拈着杯,缓缓开口道:“自姑姑来后,便为小生做了许多分外事,比如方才借更衣提点我要去向院中先来的公子请安,又提点教导我克服男女之别以免我在王爷面前失仪。这些姑姑本可以放任不管,可姑姑却处处巧心提点,可见姑姑待容某有赤心。容某实欲与姑姑坦诚相待,唯有揭了姑姑身份,唐突之处还望姑姑见谅。”
月白垂首道:“不敢,不敢。公子既是看的通透,奴婢也不敢再有所虚言。奴婢本是在殿下书房伺候的掌事,在殿下身边多年。因公子从外间来与别不同,殿下恐他人照顾公子不周,又因公子无名无分至多也只可指派末等近侍侍奉,便给我另造了身份混入末等近侍中指给公子。没想到才几日,便瞒不住公子了。”顿一顿,月白抬目望向容子奕,问道:“公子可否告知奴婢是何处做的不尽,叫公子察觉了?”
容子奕含笑道:“姑姑心思细腻,处处缜密,若我没断错,霞红他们几个也并不晓得姑姑身份。”
月白微微颔首,道:“是,他们几个都是半年前殿下额外新选的,殿下当时便将我混入他们之中送去礼仪司学规矩,回府后直接去了公子的南四房,所以他们尚不知情。”
半年前,正是容子奕被掳来此处的时候,如此看来,月白所言确有几分可信。容子奕于是接着道:“殿下的筹谋本当是天衣无缝,可惜,姑姑却错了一处。”
月白眼观鼻鼻观心,诚惶诚恐道:“还请公子指教。”
容子奕答道:“姑姑错便错在自请求药这一步。一个小小末等近侍,还是个指入偏院的,怎么会与雨霁姑姑能说上话?即便是沾亲带故能与雨霁姑姑说上话的,以你的身份要出入那小院亦是困难,更罔提去求如此珍贵之药。纵是我近来得了王爷青眼的,你也不该如此笃定能求药才是。”
月白心头一悸,道:“竟是如此大错,我却还未察觉,实在蠢钝。”
“姑姑你并非蠢钝,而是善良。”容子奕站起身,走近月白,“若是姑姑心中无善,此刻恐怕浩然已是一尸两命也未可知。这高门深院里,善良本是最无用处的东西,而于我而言,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根本。”说着,他向月白拘一礼,道:“容某愿今后之路,能与姑姑同行,不知姑姑可愿意?”
月白闻言心中颇有感慨,未作一丝犹疑便起身回福一礼道:“能侍奉公子,是我的福分。”
容子奕微微一笑,道:“前些日子委屈姑姑了,如今姑姑当可回复真身,不至该如何称呼姑姑?”
月白福一礼,道:“奴婢旧名锦绣,”她抬起头,一双眸子望住容子奕,眼神坚定而从容,“从此以后,便是月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