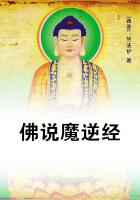宁王这些天来忙于训练虬龙部的士卒,对近在咫尺的威武军没有太多的了解。
当宁王与林少霖进入其营地之中,却发现兵士操练颇有章法,士卒的互相搏击也绝非敷衍了事,可见此军有过人之处。
“此军都尉乃是原淮中军的吴壹言,此人曾多次剿灭山贼,我听闻在其前来阴山路上便与桃花林的悍匪金泰有过一战,大破金泰!”林少霖早已探查清楚,便向宁王介绍道。
“也算颇有才干啊!”宁王感叹道。
“宁王,我们虽有斗智之心,然此时正在操演,不妨耐心等待,观察一二。”林少霖说道。
宁王微微颔首道:“卿言甚善。”
两人便耐下性子,细细观察练兵,吴壹言虽无超人之才,也颇得军心,对士卒宽严有度,众人训练也颇为刻苦。
林少霖暗暗赞叹:“此人可用!若是边关开战,决计为一员良将。”
军士操练已罢,众皆疲惫,王云啸与唐子明,秦延川齐齐坐下歇息,却见得不远处,宁王与林少霖走来。
三人亦知尊卑,便立起,向那二人行礼。
“切莫行礼,我等是布衣之交,何必如此?”宁王倒是洒脱,连忙止了三人行礼。
唐子明与王云啸生性不好拘束,闻言便放下手来。
秦延川则不然,此人生性重人伦道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宁王就算身为都尉,也是上官,他自然要做足礼仪。
“秦兄可免礼了。”宁王见秦延川并无反应,不得不再说了一遍。
唐子明都在轻轻说道:“便听了宁王的罢。”
“如今非操练之时,席都尉又非威武军都尉,何须如此大礼?”林少霖却是看出了秦延川的为人,便如此说道。
果不其然,林少霖言毕,秦延川便放下手来,直直地看着宁王道:“席都尉乃虬龙部都尉,为何来威武军中?”
甚为难缠!
宁王心中叫苦道,秦延川让他想起了在京中的侍中边昭,两人的个性相类,皆是骨鲠之臣。
秦延川此时已经没有了初来乍到的病态,其脸色不再是青灰色的,也非在淮中之时的白皙,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肤色显出了健康的光泽,与他身上保留的书生气息一经融合,倒也别有一番气质。
耿介乃是此人一辈子的个性,虽说之后的他发生了颇大的改变,但是世人都认为,世间最敢犯言直谏的勇士莫过于秦延川。
是则是,非则非,黑白分明是此时的秦延川心中为人的准则。
纵使宁王对他颇有好意,然而他认为宁王的行为有悖世间情理,便敢于直言。
这样的人,简直像都御史周冰。
林少霖的认识比起宁王更为透彻,宁王认为边昭和秦延川都是骨鲠之人固然不错,然而边昭的骨鲠乃是老臣风骨,是为君思量。
而周冰和秦延川则是为民思量,他们的宗旨在于利于民则为善。
虽然两人的认识可能会有偏差,但其用心确实是极其无私的。
君子朋而不党,这样的人便堪称君子,他们绝不会党同伐异,所作所为但求光明正大。
林少霖是个智者,他也了解如何应对君子。
“席都尉此来,乃为私事,然军机要务已经交由徐队主,之后必将向总兵请罪!万望见谅!”林少霖诚恳地拱手道。
秦延川点了点头,脸色缓和了一些,便退到一边,不再说话。
林少霖知晓,如此年轻气盛而又尊崇道德者,不可以暴力制之,当以理晓之,方可从其心意。
林少霖言毕,笑曰:“王兄近日声名卓著,引得林某前来,望王兄指教一二。”
王云啸何其敏锐之人,能以情势度事态,此时林少霖如此明显的话语,他自然知道其心意。
欲斗智否?
王云啸露出了笑容:“不敢不敢,林大人天下名士,在下若能得阁下指教,必然受益匪浅。”
秦延川见两人有一较短长之意,心下虽然觉得有些胡闹,却也起了几分好奇之心,毕竟年轻气盛,最喜争斗,纵是淡泊明志之人,也逃不过一个“气”字。
林少霖虽有智者之名,到底是二十一岁少年人。王云啸更是十八岁,尚有几分稚嫩,两人堪称少年俊杰,正因如此,更希望一比高低。
更为重要的是此二人乃边关将士,正当跃马北疆,杀敌立功,岂是轻易服输之辈?
有诗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陲。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正所谓英雄自古出少年,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两位少年豪杰可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却是自视极高之人,遇上旗鼓相当的对手,自是要比试一番。
这两位都是当世少有的明智之人,正是一个半斤对八两,石将军遇铁将军。
林少霖职位高,又是成名已久,便首先问道:“敢问天下大势。”
“何谓天下?”王云啸立即回道。
“人所在处,是为天下!”林少霖笑道。
“人之所在,亦有我所不知者,不敢妄论。”王云啸也是微微一笑。
“便论马基维利大陆之事。”林少霖见双方互不相让,便单刀直入道。
“斗胆先言,今大陆列国纷争,极北之维尼亚素来不预外事,然其主阿骨打借通商之便,若扩军备,则不为人所知也,众皆以为维尼亚如温驯之牛,在下以为其如凶险如鳄。”
“极有见地!北地多豪杰之士,维尼亚人蛰伏多年,一出必迅如猛虎,不可不防。”林少霖点头赞叹道。
“不才敢问林大人,西南之地如何?”
“十六国联盟各怀鬼胎,如今楚国内乱,此乃先兆,待十六国纷争之时,若有一势力兼并各国,足以争霸于大陆之上,本国素来轻视十六国,只怕未能知晓其中凶险。”
“如林大人言,本国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啊。北地之密密尔,乃多年宿敌,兵多将广,人马剽悍,以疾风般骑兵闻名,可能胜之?”
“密密尔者,所依仗者,乃是精骑,其疾如风,不可捉摸,若以阵法相敌,敌不能破也。然欲直捣王庭,必当以骑兵破之,方能一举成就万世之功!”
“大人所言甚善!以骑兵破骑兵,以敌之长破敌之长,可毕其功于一役。”
“王兄谬赞,不知诺曼帝国形式如何?”林少霖并未沾沾自喜,而是淡然问道。
“此国不久矣,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两国互为仇敌,如今不分上下,故俱引外援,在下断言若密密尔大胜我,则南国亡于北。若我大胜密密尔,则北国亡于南。”
“若怀一统之志,则当如何?”林少霖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起来。
王云啸顿时感觉一种危险的气息,此时南诺曼与丝之国尚为兄弟友邦,若自己回答不慎,容易授以话柄。
王云啸终究是看了林少霖一眼,说道:“假途灭虢。”
林少霖的脸色变得阴沉,众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却听得林少霖突然拊掌大笑道:“京都腐朽之辈,绝无此等见识,但会粉饰太平耳!”
王云啸只是淡淡道:“乡野村夫之见,何足挂齿?”
“非也非也,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自古英雄出自布衣,足下可称布衣之雄!”林少霖由衷道。
宁王听着他们的对话,若有所思。
而秦延川听得最是入神,直到王云啸提出假途灭虢四字,他终是一惊,接着便如前一般,缄默不语。
唐子明却是眼神澄明,似是深有所得。
“王兄大才,深知天下大势,既然如此,在下便出一微末小题,可否?”
“单凭指教。”王云啸不卑不亢,平凡的圆脸上没有半点兴奋的神色。
“我国中北疆,时有地震,一旦难起,死者枕藉。北边有牧场,牛羊千头,有十人奉皇命看守,多日地震,一震死牛羊百头,人一名。三震过后,余牛羊几何,人数多少?”
王云啸不语,似是沉思之状。
唐子明见此题颇为有趣,便笑道:“我家中本为商人,筹算之技,亦有所知。三震则牛羊死三百,人死三人。”
说罢,唐子明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并非如此简单,既然地震,岂能坐以待毙?则牛羊散,人亦走!”
“所言有理!”宁王听得分明,觉得合情合理。
王云啸也不禁点头。
“并非如此,牛羊无知,人受命而为,岂能背离职守?牛羊易散而人不去也。”秦延川突然抬起头朗言道:“此人之信义也,若无信义,何以存世?”
他这番话掷地有声,林少霖深知他是在讽刺之前假途灭虢之策,却笑道:“秦兄所言非虚,若是相同故事,于西南楚国发生,如何?”
秦延川毫不犹豫道:“自然一样。人有分天南地北,男女老幼,然其受命而为,岂能不守其责?”
“非也。”王云啸却摇了摇头:“在下受教了,之前此题,在下也未曾考虑周详,然而此题,在下已有决断!”
“何种决断?”林少霖笑容可掬道。
“西南楚国,奉行民主,然对奴隶酷虐。若以奴隶看守,则奴隶不得善待,失羊必死,必然远走!若以民众看守,则民众受佣,若危害性命,必不能守其位,此其民主之弊端!”王云啸话语清晰,说得头头是道。
“王兄得矣!”林少霖大叹。
“大人指教,在下难忘。在下虽能观大局,却不能深知人心,今日受教,所获匪浅!”王云啸由衷地拱手行礼。
“天下制度,各有利弊,能得人心者胜!”林少霖也端正神色,如是说道。
“在下有过,请大人恕罪!”突然,秦延川行了叩拜大礼。
众人大惊,却听得他一席话,令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