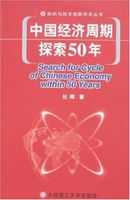女孩欢快的声音就像风铃一样悦耳。
白泽的手心迅速溢出了些汗,只觉得这一辈子的幸运似乎都被用光了。
别苑设在一处安静的地方,许是累极了,到达时身前的姑娘已然沉沉睡去了。
白泽小心将她抱下马,那只豹子一只紧紧跟随在身后。
这让白泽多少有些不舒服,甚至心里发虚。
以至于上竹楼时,差点脚下不稳摔下来。
这处别苑,是白泽费了许多心思,熬了多个夜晚设计的。
雅致的小竹楼,美观的石桌,井井有条的花海。
每一样都透着设计者精巧的心思。
平日里虽然不常来,也都定期差人来打理。
安顿好麋妮后,白泽悠闲的坐到石桌前,颇是得意的打量着自己的得意作品。
是夜,天上挂满繁星,麋妮捂着依旧有些微疼的头,从楼上缓缓走下来。
彼时,白泽正在石凳前,品着新到的春茶。
听见身后有声音,不禁回头看去。
满天的星辉似乎都落在女孩单薄的身上,她一直手扶着栏杆,皱着眉盯着他。
僵持了一会,她才清浅的一笑,说:“谢谢你!”
白泽手里的茶不觉洒了些,他带些诱惑的说:“姑娘,我这花圃里满是鲜花,可惜不是季节……”
顿了顿,他又说:“想来姑娘是爱花之人,不若在此地休养,顺带可以看到来年花开?”
听着白泽的提议,麋妮有些犹豫。
她一边走近白泽,一边思索。
最终,站到白泽面前,犹豫的说:“只怕叨扰公子。”
见她斯文起来,白泽忽然有些失望。
不知怎的,他还是喜欢她灵动欢乐的模样,像极了山间可爱的小鹿。
敛了神情,白泽盯着麋妮,嘴角微扬:“无妨,不过多些吃食……”
“再说,你也可帮我打理花圃!”
一番说辞,麋妮才勉强点头,转身走入屋子。
白泽立在庭院中,看着姑娘消失背影,站了许久。
此后每日,白泽都会带些吃食来看麋妮,还有那只贪吃的豹子。
他发现,这个姑娘平素里,都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偶尔,才会透出些本来的性子。
一日,麋妮正给花圃浇水,忽然抬头问了白泽一句。
“若你花圃的花都开了,该是怎样一番美景?”
白泽正在看书,听她这样一说。
四周打量了一番说:“该是极美的!”
许是混熟的缘故,麋妮自然的将头靠到白泽手上,笑道:“若是能看见花海,此生足矣……”
说着,她的眼睛迷离起来。
痴痴的看着对面的花圃,向往的说:“我从未见过花海,你说像海一样多的花,该多美?”
白泽不由心里一动,问道:“你为何这样喜欢花?”
麋妮笑着说:“因为,花是颜色,是我最向往的东西!”
她越说,白泽心里愈发纠结。
末了,他才认真的说:“有朝一日,我会带你去看花海,看这世间最美的色彩!”
本以为她会很高兴,没想到麋妮忽然愣住了。
好半天,才郑重的点点头道:“好!”
这样好的时光没过多久,帝都的形式忽然紧张起来。
几乎是一夕之间的事,白家上下都显得人心惶惶。
白泽再也无法隔三差五去探望麋妮和她的豹子了。
那天,阳光很好。
春天的气息近了,白泽提着精致的糕点,来到小院。
麋妮正趴在石桌上休息,见是白泽。
她懒懒的抬起头,冲他笑了笑,说:“你来了?”
她脚边的豹子也似乎懒了许多,闷哼了一声算是回应白泽。
白泽将精致的饭菜一一摆好,伸手拂过她的鬓角,柔声唤道:“起来吃饭了!”
麋妮忽然将眼睛瞪得大大的,微微抬头,带些期许的问:“几许花开?”
白泽脸色有过瞬间不自然,他长长的叹了口气,才说:“快了!”
见麋妮依旧懒懒爬在桌上,白泽只好耐着性子哄她:“你乖乖的吃完饭!”
麋妮转头看着地上的豹子,声音很轻:“宝儿,你走吧!”
又拉过白泽的手,视线却始终在豹子身上,她说:“回到山上去!乖!”
麋妮像哄孩子一样,耐心的同地上的豹子交流。
一丝不好的预感瞬间爬上白泽心尖,他紧了紧握着麋妮的手。
麋妮同豹子沟通了好久,豹子才勉强从地上起来,缓缓往外走。
又一步三回头的看着麋妮。
麋妮的精神状况似乎好了很多,她欢快的站起来,冲着豹子使劲挥挥手告别。
直到豹子消失后,她才如被抽空所有力气一样,瞬间瘫软下来,跌在白泽怀里。
“白泽……”她轻轻的唤,竭力展出一抹微笑,有些期许的问:“你说,花是不是要开了?”
白泽还没来得及回答,雅致的小院已经被一群官兵团团围住。
他们穿着绣黄布的盔甲,白泽一眼认出,是帝君贴身护卫。
“何事?”白泽问。
领头士兵二话不说,将泛着寒光的剑低在白泽脖子上。
冷笑一声说:“白府反了,三少不知?”
“砰!”白泽狠狠拍打身旁的石桌,厉声喝道:“胡说!我白家三代贤臣,何来反了?”
“是不是,三少随我走一趟就知道了!”
白泽只好小心的把麋妮抱到一旁的桌子上,轻轻抚摸她满头青丝,温柔的说:“等我,很快就回来了。”
“把这女的也带走!”领头的士兵瞥了麋妮一眼,冷冷的说。
“慢着!”白泽只身挡在麋妮面前,皱着眉说:“她与我白家无关,不能将她牵扯进来!”
“有没有关系,不是三少说了算!”说着,领头士兵一把推开白泽,拉起麋妮的手,准备往外拖。
“你敢!”白泽咬着牙说,一把短剑自袖中而出。
死死低着领头士兵的脖子,隐约可见士兵脖子处有血痕。
“刷刷……”几乎一瞬间,院里的数十把刀剑同时出鞘。
气氛一时紧张到极点。
“白泽!”麋妮柔声的唤了句,她扯扯白泽的衣角,摇摇头说:“我愿意同他们走,你不必这样!”
白泽看了麋妮一眼,始终没有将剑移开。
麋妮轻笑一声,复杂的看着白泽,道:“想想你的家人!”
白泽手中的剑缓缓松动,像麋妮眼里的光,一点点消失殆尽。
袖剑本是一股气所化,气散了,剑也就没了。
挣扎一番,白泽和麋妮最终还是被带离小院。
临走前,麋妮万分留恋的回头看着自己照顾了许久的花,惨白的嘴角微微上扬。
最终,他俩都被关入天牢。
看着麋妮半死不活的模样,狱卒好心的将两人关在一起。
麋妮的身体越发虚弱了,她懒懒的依偎在白泽的怀里,语气凉薄的问:“有没有一个瞬间,你后悔过!”
白泽周身忽然颤抖的厉害,末了,才摸着麋妮的额头,笑着说:“可是害怕了!”
麋妮摇摇头,说:“不,死终归是早晚的事!”
“只是”,她又淡淡的补了句:“我后悔了!”
白泽忽然很生气,他极不喜欢麋妮的语气,却无法对她发火,只说:
“没事,我会保护好你的!”
“呵!”麋妮冷笑一声,转过身沉沉睡去。
夜半,狱卒闹腾的将白泽带离牢房。
在离麋妮不远的地方,疯狂的折磨他。
麋妮半睁着眼睛,看着他们将烧红的烙铁,往白泽身上招呼。
麋妮的鼻子酸得不行,她还是咬咬牙忍住了。
紧紧的抓住四周的稻草,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师傅的话还在她耳畔萦绕:
“眼泪是你最后一道保命符,切不可轻易流泪!”
眼角最终还是润湿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流失。
次日清晨,阳光微暖。
麋妮头昏得厉害,四周不是那个脏兮兮的牢房。
她躺在一块干净草地,身上披着白泽最喜欢是那件大衣。
蓝天,白云。
美的就像梦里,麋妮嘴角微扬。
白泽自远处走来,他的表情有些复杂。
麋妮了然的笑了笑,眼睛明亮得就像夜空的星星。
“你是来杀我的?”她问,见白泽沉默,又自顾自的说起来。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会有这样一天。”
“就像猫和老鼠,最终只有一个生存下去,不是猫饿死,就是老鼠被吃!”
说着,她抬起头看着白泽,缓缓的笑开了:“如今,你还等什么?”
她微微仰起头,看着他笑道:“你来了!”笑容就像三月的桃花,映着阳光,明媚而娇艳。
“嗯!”他极不自然的偏过头去,不敢在看她的眼……
“可是白泽,我要死了!”她有些忧伤的说:“还没来得及和你一起看花海呢!”
他心中一颤,手里的刀也跟着紧了几分。
良久,无奈的别过脸去,颤声答她:“来生!来生我定陪你去看盛夏的花海!”
袖子里的刀,最终狠狠没入麋妮的心脏。
白泽不敢回头看,凭借感觉摸索寻找,刚刚化出的麋貎心。
那颗发着红光的小珠子,烫得异常。
白泽忽然有些恍惚,脑海里不断回荡着麋妮的音容笑貌。
他告诫自己:“她只是动物,异类而已!”
越是这样,心里却更加空得厉害。
五月,百花齐放。
白泽成了长安城新的统治者,他本不姓白,而是一个被帝君的五皇子。
当年,白家的一个巫女在帝王家族种下血蛊。
所以,帝王一直受制于白家。
为寻解药,帝君将刚出生的小皇子同白家新出生的孩子秘密调换了身份,被换的皇子便是白泽。
帝君多疑,除了自己骨肉,其他的谁都不信。
白泽就这样蛰伏白家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神兽麋貎是唯一能治疗血蛊都神药。
这些年,白家一直用麋貎肉压制帝王家的血蛊。
可若想将血蛊测底消灭,唯有服下麋貎化身的灵石。
麋貎身边时常有异兽,其泪剧毒。
且若要化灵石,需日日服用东山的五根水,出去体内混浊之气。
又因为,麋貎生性狡猾。
所以,几乎没有人得到过麋貎化身的灵石。
遇见麋妮的第一天,白泽就认出她是神兽麋貎。
他的预感一向很准。
制造偶遇,对白泽来说并不困难。
诱她吃下无根水,也不是什么难事。
最难的是,将她的眼泪逼出来,他还是做到了。
可是,白泽曾以为,得到灵石会很快乐。
如今,只有怎么都补不好的心里满满的失落。
帝都的一切都是他的了。
他从前以为,日子久些,身边漂亮的姑娘多了,就会忘记那个相貌算不上拔尖的女孩。
可但越是这样,麋妮的脸在他脑海里越发清晰。
他想到她在花圃里浇水,忽然回过头冲自己盈盈一笑的模样。
又想到,她给受伤的小兔医腿的一幕。
还想到,她恶作剧的把一盆水到在自己身上时,笑得满脸得意的模样。
白泽烦恼的抓头发,拼命摇晃脑袋,怎么都无法将她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