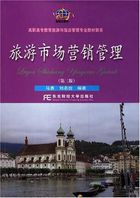“拦着城门作甚!好不放行!”
正当郭阳内心挣扎之际,城门内传出一声粗狂的大喝,这一声喝,使得城门处的众人耳朵嗡嗡响,众人抬头,之间一个身着红甲,满脸络腮胡的武将稳坐在一匹枣红马上,手上提着一杆大枪,瞪着眼睛,冷冷的盯着他们。浑身气势磅礴,在他身后还跟着一队红甲卫士,手执长槊,面色铁血。
郭阳神色复杂的看了来人一眼,抱抱拳,走到来马前:“淳于兄。请借一步说话。”
来将不屑的扫了一眼郭阳,不过怎么说两人都是平级,既然人家给足了他的面子。
“汝等将弟兄们换下,让这些弟兄自去潇洒,本校尉与郭校尉有事商量。”来将板着一张脸对着身后的卫士命令道。当下下马,跟着郭阳走到一边,估计郭阳就是跟来将说此事。
'诺!“
卫士有秩序的将站了半天的弟兄们换下,当起了值。
陶虎没有看到这些卫士的训练有素,而是愣愣的看着那个跟郭阳走到一边的将领。强行压住脸上的惊惧。难怪陶公吩咐,来到洛阳要尽可能的低调,免得惹是生非。如今看来,陶公果然有先见之明,这洛阳果然是一国之都,卧虎藏龙,单单一个城门校尉就有如此气势,观此人气势,便知道此人的身手当是不凡,让他想到了幽州时的那一幕,那个人,白马白甲,长槊,一骑当千,杀得乌桓人不敢侵犯边关。
陶虎不自觉的将两人对比,觉得此人身手或许比那位他眼中的猛将还要强,因为那压迫人的气势!
在陶虎还在震惊时,郭阳与淳于校尉已经过来了,走到他身前,陶虎方才回过神来,愣愣抱了抱拳,张嘴问道:“敢问这位将军,可否放我家大人进城?”语气略带着恭敬。
“本校尉只是一介校尉,当不得将军这一称呼。”这个被郭阳称为淳于校尉的将领听闻陶虎叫他将军,心中欢喜,试问,哪个穿了兵甲的人不想当将军?
不过却连连摆手,顿了顿,淳于校尉又说道:“方才郭校尉已经与吾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上面也的确有着这样的批文,并不是郭校尉有意为难你家刺史大人,还望你家刺史大人不要放在心上。”
“这......”陶虎听后一脸为难,感情这是真的,看来这个乞儿是真的进不去了,只好向陶公禀明,请陶公定夺了。
还没转身,身后就响起了陶公中气十足的声音:“来人可是淳于琼贤侄?”
说着,陶公已经越过陶虎,走到两校尉身前,不过陶公只是扫了一眼郭阳,便将注意力放在满脸络腮胡的校尉身上。
“正是,您是?”淳于校尉疑惑的看着来人。在他印象中并没有这个人。
“老夫陶谦,当年与你父乃是至交好友,当年你学艺在外,老夫见你面向奇异,便记得你。”陶公撸着三寸长须面色温和的说道。原来陶公,便是陶谦,现就任幽州刺史一职,一个月前朝廷命他回京述职。
“原来是家父的好友,恕仲简眼拙,竟未认出陶伯父,还望陶伯父莫要见怪。”听闻陶谦是他父亲朋友,他便不奇怪了。
淳于琼,字仲简,是豫州颍川人。
淳于琼的父亲乃是一介酒徒。每日都要把自己喝醉,不醉不休。其父经常对别人说,酒,乃是神物,心里有千般事,只要饮了酒,任何事物都将是过眼云烟,酒让人快乐得跟神仙似的。
他家的喝酒其实是有渊源的。淳于琼的祖父亦是个酒徒,天天不离酒。家里其他物件可以没有,不能没有酒。淳于琼的父亲受了传染,小时候就爱喝酒,家里来了客人,还能上来抵挡一阵。客人都说,这娃儿好酒量!淳于琼的父亲受了鼓励,越发能喝。常常客人没走,自己就倒下了。淳于琼的爷爷不仅不责备,反觉很有面子。客人表面上都赞不绝口,回过头来却暗笑,这个家不是家,是酒缸了。
到了淳于琼这辈,却都不爱喝酒。淳于琼兄弟五人,其他四人都有点痴呆唯有淳于琼生得一表人材,英姿伟岸。淳于琼又不喝酒。倒不是不喝,而是不能喝。沾着酒脸就红。有一次,家里来客人,父亲知道淳于琼不能喝,就命他过来斟酒。一场酒斟下来,淳于琼倒了。被酒气薰倒了。你瞧这没出息呀。淳于琼的父亲叹息不止:这孩子算完了,白生一付好皮囊,男人不吃酒,白在世上走啊!
淳于琼不吃酒,但很吃书,很吃枪棒。从小就喜欢读书,文读四书五经,武读兵书战策。并且爱习武艺。到了一十八岁,已经是文武全才。
而陶谦便是他父亲的酒友,当年的陶谦可不是现在这般有大成就,一州之刺史,当年的陶谦用放浪形骸也不为过,认识他父亲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淳于琼不知道陶谦年轻时的事迹,不过也没有过深的去问,只要知道,现在人家乃是一州之刺史,现在却亲自走下马车与他攀亲,让他受宠若惊。人家现在是朝廷重臣,而他的父亲,如今却......
当下,便躬身行礼:“淳于琼见过陶刺史。”神形恭敬,全然没有方才的张狂。
一旁的郭阳已经傻了眼了,这还是那个脾气暴躁的淳于琼吗?不过他到底是有见识的,见到往日高他一等的淳于琼都行礼,那他跟惹不起,也跟着行礼。想到刚才的事,他心里透着一阵阵的后悔。
陶谦笑眯眯的搀起淳于琼,说道:“老夫与你父相识,因为好友,贤侄若是不嫌弃,便唤老夫一声伯父,如何?”接着转头看了眼郭阳:“郭校尉也不必行礼了,此乃尔等的职事,应当如此。”
“诺。”郭阳抱拳应诺,见陶谦没有待见他的意思,他便没有自讨没趣的在这里,而是告辞离去。
陶谦笑眯眯的看着郭阳离去,没有说话,反而淳于琼啐了一口:“仗着祖辈余荫,当了个校尉,这等三脚猫功夫,狐假虎威。”显然十分看不起郭阳。接着看到陶谦笑眯眯的,带脸色一红,尴尬道:“伯父勿怪,仲简便是这等心直口快。”
陶谦呵呵笑道:“贤侄乃是真性情,与老夫当年相似。老夫怎会责怪?不过贤侄方才的言语切莫再说了,出的你口,入得我耳。”
“诺,仲简省的!”
“贤侄,老夫现如今能否进城?”陶谦笑呵呵的指了指车辕上的萧冷。
淳于琼迟疑了一会儿,终是点了一下头:“既然是伯父领的人,仲简怎会再次阻拦,伯父自便就是。仲简自担得!“
“如此老夫便谢过贤侄了。”陶谦面带感激的笑道,虽然他是淳于琼父亲的朋友,但人家并不认识他,人家既然帮他,表面上还是要做足的:“老夫或许会在洛阳呆一段时间,贤侄若是不嫌弃老夫家中僻陋,不妨来老夫家中坐坐。”
“伯父有请,仲简怎敢不去,待得仲简闲时,定来叨扰伯父,到时还望伯父嫌弃仲简麻烦才是。”
“哈哈哈,好,老夫静候贤侄,贤侄有职务在身,老夫便不再打搅,老夫告辞。”
“伯父慢走。”
......
淳于琼目视着陶谦的马车缓缓进城,目光闪动,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驾~驾~驾”
谁也没看到,一双眼睛一直注视着这一切,眼睛的主人默默的记下了这些人,这些事。
“淳于琼,陶谦。我记住你们了。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正是萧冷!早在陶虎遵从陶谦的吩咐给他喝了一点水的时候他就迷迷糊糊的有点意识,方才发生的事他都看在心里。
“不过,这两个人的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萧冷迷迷糊糊中又睡了过去。至少,他心安了,至少,他或许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