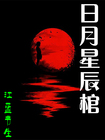阿旭被葬在河对面的菜地里。下葬的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内心悲痛的母亲就伏在坟头痛哭,河的这面都可以看的很清楚。
我也看的很清楚,但是我心里很茫然。
一条生命,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经常跟在身后玩耍的小跟屁虫,就这么一下子走了,一下子就没了。
我知道他在对面菜地下的小小棺材里躺着,可是他知不知道我就在河对面站着?
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晚上没有做噩梦但就是睡不着。
我知道这是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在谴责我,我知道这是一种叫做愧疚的东西在鞭挞我。
有时候我实在是睡不着了,就会去河边那个滩头上,坐在石阶上呆呆的望着河对面。
我希望这个世界真的有鬼魂的存在,因为我迫切的想和他交流。可是除了缓缓流动的河水以及呜呜作响的夜风,我什么都见不到。
我的反常终于让父母有所察觉了,无论他们怎么盘问,我什么都不肯说,只是依然过着比较沉默的日子。
这种内心带着折磨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很快就到了阿旭的五七之日。
人死之后都要过五七。除了头七之外,五七是最隆重的一次。四七二八朝,五七第一朝。五七就是前面四个七之后第五个七的第一天。就是人死以后的第二十九天。
用道家的说法,人在死亡之后三魂七魄不会立刻消散,而是游荡在天地间,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如果在五七过后还无法得到超度,那么就会成为孤魂野鬼。到了那时,即便是法力再高深的术士都无法超度其进入天国,只能渡黄泉,跨奈何,重新投胎。
五七的斋醮就是召唤魂灵速速归来,然后安心升入极乐天国。
那天我鬼使神差的没有去上学,在我的内心里,总是隐隐渴望着能再见到阿旭一面。哪怕明知道这一幕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哪怕这都是我自己不切实际的臆想。
斋醮是由叔公来主持的。他头戴南华巾,身披八卦法衣,足踩白底黑面圆口鞋,左手持帝钟,右手挥拂尘,口中不时诵念道经。
叔公的脚下有规律的走动着,这大概是按照某种图形依循而走,而且方位会不时的变动。有些灰蒙蒙的天并没有阻止许多看热闹的村民乡亲,他们都抱着轻松的心情在低声的交流。
有几个自认为稍懂一些的还在那里卖弄,说老叔公走的是天罡八卦步,正在沟通天地神灵,求祷四方天帝。
我不知道叔公走的是什么步,但是看着他神情肃穆,道袍飘飘,心里便感觉无比安宁。闭上眼,细细感受,叔公嘴里发出的诵经声逐渐由单一变成多重。仿佛那不是一个人发出的,仿佛四周有无数人都在附和,仿佛天地间真的有神灵。
而且,在这无数的声音里,我分明听出了其中有我熟悉的,那是阿旭的声音,那是他稚嫩的感谢声,那是让我放下一切包袱的宽慰声。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愧疚都随着泪水肆意奔淌而出。
重新睁开眼,我走进叔公那画着白线的圆圈之内,恭敬的跟在叔公的身后,随着他一起走起了那种奇怪的步伐。
所有人都看的呆在那里,我却不在乎他们的目光,我需要用我的方式来祭奠这个早早就离开人世的小生命。这或许是我唯一能做的。
秋风已经略显萧瑟,不时扬起焚烧纸钱过后的灰烬,而那时,我的心灵已经得到了解脱。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说服父母,表示自己此生只想做道士。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接受了入门的戒礼,拜叔公为师。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的人生历经了一次重大改变,但我无怨无悔。
叔公老伴早就去世了,是一人独居。
自从我跟他学道以后每天把作业一做完就去他那里,从学篆文开始,画符,学咒,并学习所有的道家仪式。
渐渐的同学们都知道了,一个个的来取笑我,我看的出他们眼神中的那种鄙视。
在现代,农村道士是一门卑贱的职业,被人认为是在死人家里骗吃骗喝的神棍。
但是我根本不在意。就好像突然间我成熟了许多,所以境界变得不同。
叔公说我有灵性。在古代的道术传承中,学道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心性跟灵性,而悟性反而是其次的。
我只是默默的按老叔公的教导去做,至于将来,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会一步一步走,就做一个与死人打交道的做法道士。
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就是辛单淳。
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他都会来叔公这里小住些时日,我是他唯一的玩伴。
捉鬼降妖太过离奇,在现代唯物主义的人看来那都是蒙人的,是封建迷信,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但是那份通过为死者虔诚祷告而获得的内心安宁与平静是真实的,这是我当时的真实体会。
叔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气色却很好。为了照顾他,我干脆就搬到他那里跟他一起住,只要有空,我就会为他做各类易消化的小吃,自认为道术没啥长进,厨艺却日臻娴熟。
道术艰涩难懂,枯燥无比。李家的道术以咒语见长,尤其是祖传下来的天授八咒,因为原来的典籍已失,叔公只是靠他的记忆教授于我。
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腹语的练习。
普通的腹语只是一种发声技巧术,在唇齿不动的情况下将气息在腹内调和,然后再打在发声部位,这样会形成一种振动,经过长时间有技巧的训练后就能在腹部清晰的发出声音。
而道术中的腹语跟普通的腹语不一样。
首先要经过道家的筑基,在丹田内形成一股气,这就是道家法力,然后用意念控制这股气打出一个一个的音节。
据传法力高深的天师,无需任何动作,腹部轻轻发出一个叱字,传出来的音波就能让亡魂邪灵化为虚无。不过那种高深的境界只在传说中,叔公也做不到。
他能做的只是嘴里诵经的时候腹部同样会有延缓的诵经声传出,就好比是一前一后两个人同时在诵经一样。
这种奇术也让我大开眼界,顾不得打坐吐纳的枯燥乏味,一心想要学会。
叔公有些遗憾,可能是根骨的原因,他的腹语只能到现在这种境界。更进一步的话必须要打通神阙穴,那时用丹田打出的道藏古音能与天地共鸣。
神阙穴就是人身上的肚脐眼。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肚脐眼,也不明白如何才算打通肚脐眼,难不成是去钻个口子,每次想到这个我都会笑出声。
道术腹语在修炼时讲究的是一种呼吸吐纳之法,三呼一吸,五吐一纳,三吸一呼,五纳一吐,如此不断循环往复。
我在五年之后才算有所小成。五年里,叔公尽心尽力的教导我,同时也给我讲了道家的各种奇闻异事,让我眼界大开。
第七年,我考取了县城的高中。
当时觉得很犹豫,犹豫要不要去三十里外的高中就读。如果去的话,来回不大方便。直觉告诉我,叔公已经有瓜熟蒂落的预兆了,说不定何时就会驾鹤而去。我怕见不到他最后一面。
叔公知道后,让他大孙子李文忠帮忙把我的行李铺盖直接拿到了县城高中,还说我不用牵挂,叫我安心的在县城读书。
上了高中后我跟叔公的见面就少了很多,只能在周末回来陪陪他。他倒是很看的开,对他来说,李家的道术已经有了传承者,以后去见了祖宗也能有了交代了。
在我读高中的第二年,某一天,李文忠火急火燎的来学校找我。我一见他的面就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跟叔公有关。
果然,他带着惶急之色告诉我,叔公快要不行了,叫我去见他最后一面。李文忠是自己开汽车来的,回去的时候开的飞快,心中的焦急可想而知。
到了叔公家门口,李家的族人都已经赶来了。他的两个女儿及儿媳妇都已经在哭哭啼啼了。众人见我到来,都闪身让开,仿佛在这一刻,我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我半跪在叔公的床头,轻声的呼唤他。叔公有了反应,一只手想举起来,但是已经举不动了。只是眼神盯着自己的手腕处。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从他手腕处将一副他时时把玩的玄环摘下来,他示意我戴在手上。这是一副藤制的连环圈,是道家重要的修持用品,有驱邪缚魅,定心宁神,祈祥降福的作用。叔公时时拿在手里转动把玩。
物品不是很珍贵,但对我们李家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我郑重的将玄环戴在手腕,叔公带着微笑,双眼缓缓的闭上。
我双眼噙着泪,口里诵出了升度亡魂登道咒,声音不光从我口中传出,在我的腹部甚至全身都洋溢而出,一时间,满屋都是肃穆低沉的念咒声。
农村里的丧事比较繁琐,从走报送讣开始,到热摸,点灯,取水,升仙,大殓发丧,一般要三至五天。李家对这个不是陌生,一切事虽然繁杂但是有序的进行着。
到了叔公做五七那天,我戴起了南华巾,披上了法衣,为叔公超度亡灵。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坛设醮。
从此以后,我成了一个道士,一个不会降妖除魔,只为死者超度亡灵的法事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