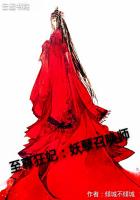听姨娘讲,我三年前原是被人掳走的,我实实在在被这个回答给吓了一跳。
“掳……”我的声音一下比一下大,姨娘用手帕捂了我的嘴,我只好又压低声音,“掳走?”
“你别那么大声,听我说,这还是我亲眼看见的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从你房间里出来,拎着你就跳上了墙,骇死我了。我当场被吓得腿软,马上叫了人来,可是等大家出去找的时候,你和那人已经没影了。后来你父亲四处打探,一直都没有消息。正在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要不要将这事体禀告官府的时候,你就被送了回来。”
姨娘指了指我的床,“当时你就躺在你自己的床上,人好好地睡在这,自然而然地醒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是那双鞋破了。后来大家见你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好似忘了这般,也就不再问了。你爹娘将此事视为家族的耻辱,不许任何人提起,所以之后也就没人敢告诉你了。”
“原是如此”,可我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地方,“可是为什么当初爹娘不肯告官找我呢?如果告官,我可能早就被找到了。”
姨娘瞪了我一眼,一脸你是笨蛋的神情,我则无辜又不解地再问了一遍,姨娘这才说道,“一个清白女孩子被强人掳走了十几天,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何况,你是和皇太孙有婚约的,怎么好张扬,回头损了皇家的面子,别说你,我们一家都不保了!”
家人的立场我能理解,于是又问我更为关心的问题,“那,三姨娘,除了这些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关于三年前的事情,我想知道得更详细。”
“都已经过去了,你又何必再追究,还好你回来时还是好好的,不然皇家不发落我们,我们也得愁死,这事情已经过去,莫要再提了。”
说完,姨娘一掀帷帐走了出去,随后其它人也都离开了。
空荡荡的房间里,独留我一个人迷惑不解,沉浸在一片未知的迷茫中。
先前讲了,人间四月芳菲时,京城的桃花开得正艳,我原本是要去看的,可到现在为止,经历了一大番波折,将事情搅黄了。先时是那鱼面鬼捣乱,接着又是那面可恶的铜镜,害得我根本出不了门。
经历了那么多的险事,那六个丫环跟我跟得是越来越紧了。以前没这遭的时候,我三天两头翻墙出去玩,现在一连几日被闷在房里,根本脱不了身。只要一想到以后都得闷在这里,直到出嫁,我就急得抓耳挠腮。苦的是没什么办法。
今天我又为此想主意间,一个小丫环不知赶着什么事,从我眼前撞过来。本来凭她那样的速度,我是能躲过的,可我记上心头,偏是要让她撞上我。
没成想,她到我跟前时就一刹步子,停下了。我眼见大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上前一步主动撞上了她。她摇头摆手,连声说不是我不是我,我哪里肯放过她,拽着她那水袖子就要去爹娘那处评理。
她被吓得不行,瑟瑟发抖,我也有些不忍了,就不合这演戏,直接进入正题——将她拽进我的房间。
我说了理由是教训她,把那六人拦在门外。关上了房门,立刻演起戏来。
我小声威胁那丫环,让她叫疼,实际是我拿右手手心打着左手手背,打得噼啪作响,叫仍是那丫环叫。我龇牙咧嘴间,那丫环捂了嘴偷笑,我抽了手假装要打她,她这才停了不良念头,专心叫喊起来。
之后我与她换了衣裳,让她跟我床上睡了。我穿着她的衣裳,脸上蒙了面轻纱,又梳了丫环的双头髻,在那六人众目睽睽之下,从容走了出去。那六人在我走后,马上一股脑儿地涌进了房间。
我看着里头关上了门,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是成了。
我跑到樟树下,从树洞里拿出了我先前藏在这的小包裹。里头是一套男装,并一个男子固发用的网巾。
我到角落里,轻车熟路地将行头换上。环顾了四周一圈确定无人看见,这才手脚灵活地攀上了大樟树。我找树枝的落脚处,一跳一挪,三两下的功夫就到了院墙的高度。
我院子里的这棵大樟树正靠着院墙,墙的外边就是一个破旧的胡同口,从胡同口走出几十步就是大街。
我当初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死活要和婶娘换院子,说是吉利,可真实目的就是现在这般。
因我被选为皇太孙妃的旨意里,说我是个端庄娴雅的女子,所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的性情。连我母娘也常常和街坊四邻说道她教女有方,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于是周围所有人家的母娘,全都效法我母娘的做法,霎时整个城西方圆好几里,街道上竟没有一个女儿家。
我听我身边的丫环议论这些的时候,脸上一派平静,心里则暗自偷笑。
现下我已走到城西一处闹市。
四周商贩叫卖吆喝声不绝于耳,一派繁荣景象。街上的人们安居乐业,人人有衣可穿,有事可做,好像就我这个人无所事事。
也对,养在深闺里的未来皇后嘛,我心里苦笑,百姓家家勤劳做活,无论是哪一家,都是不劳动者不得食,男耕女织各为其事。只有我,一个未来皇后,整天在家里读写什么《女训》之类的文章,不但没有用处,还让人十分地厌恶,倒真是不如寻常女子忙活手头的活计,乐得自在。
我有这样的念头似乎很合理,其实十分欠打。虽然如今永乐大帝治世,处处繁荣,可也总有人忍饥挨饿,我不用耕作不用织补,就有了高人一等的衣食,高人一等的地位,换了别人,感天谢地还来不及,居然还在这发牢骚。这样想来,我胡三疑真是可恶。
罢了,罢了。今儿个出来,不是为发这般牢骚的,是为了城郊漫山遍野的桃花的。
出来时往身上揣了银两,现在只要到酒楼里稍事休息,换了食物水酒,就可以启程了。
这时间酒楼里几乎客满。
酒楼请了说书的先生,以此招揽宾客,这说书先生的功力很好,我也喜欢听他这口儿。此间说得正精彩,无数人暴声叫好,我初来乍到,没听着什么。不过我看着热闹,也从众叫了声好,旁边领我落座的小二低了头偷笑。
我寻了一张桌子坐了,是与人拼桌。
我看那人清清秀秀、斯斯文文,是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一个少年小道士。
既是修道之人,那必不是个坏人,想着和他同坐应是无碍。于是握了扇子,躬腰作揖,问了他一声,“酒楼客满,并无空座,能否同坐?”
他没看我,不以为意地扇了扇袖子。这意思我明了,不做声,在他身旁坐下了。
原来我以为他是听台上说书听得入迷,所以不理我,我就坐下与他一道儿听了。谁知越听越觉着他不太对劲,怎么听人家说书,听得直着脖子往上腾,我看他这样子觉得累的慌,心里好奇他在看什么,与他一齐直了脖子,往二楼雅间方向看去。
这不看还好,一看就挪不开眼睛了。
真是想不到,那雅间里头,正坐着一个风姿出尘的男子。那张脸真是不同凡俗,难怪我身边这兄弟如此痴迷,简直要将脖子抻断。
只是想不到,这原是一番断袖情谊。
我十分尊重这厢,也十分理解这厢,于是打定了主意不去打扰他们。
我刚想扭头回来,却发现雅间上边有了新的动向。那雅间里出尘绝世的男子起身了,正准备下楼。
我身边那位的脑袋,也随着楼上那位的行动一齐动了,这下更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暗暗钦佩着身边这位,他为了****不避及世俗的眼光,真是精神无畏。一边我也悄悄祈祷着,上边的那位还是不要与他这一般的好,不然我今天的心情一定会很糟糕。
那美男扇着折扇,缓缓下楼的间隙,我脑海里窜进了一副这样的画面:上边那位美男子缓缓走了下来,冲我身边这位小道士抬了抬手,接着小道士欣喜若狂,一下依偎在美男子胸前,两人怀抱着一齐远去,远看竟是天造的一对、地设的一双。
我正胡思乱想间,那白衣美男子已经下了楼来,我这张桌靠门很近,那白衣美男出去时,恰好从我身边走过,临走时还撇了我一眼,许是我目光太过热烈,而且我如今一身男装,用那样的眼光看人家,难怪人家好奇。
眼下被如此出尘绝世的美男子撇了,我颇没出息地红了脸,回想着他撇我那双眼,那是极冷淡的眸子。
等等。
极冷淡的眸子?这样的眸子我好似在哪里看见过,在哪里呢?在……
脑海中浮现起了昏迷时的情状,我身处的那片极冷的水中,有个男子将气息渡给了我,他也有那么一双冷淡的眸子,只是当时我未能看清他的脸,只记得他的眸子了。
难不成,这美男子真是水下救我的那位?
不行,我要去看个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