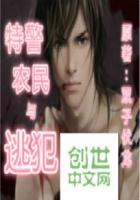过了片刻,似有轻微的脚步声音传出。跟着有人将房门慢慢打开,陶泰出现在房门之内,问道:“琴姑娘,你找我什么事?”陶泰整个人已经没了神采,全身上下再也看不到丝毫青年才俊的影子。
琴韵一怔,没想到这里就是陶泰留宿的房间。琴韵道:“陶大哥,我有话想和你说。”陶泰向旁边让了一步,允许琴韵走入房中。
初时,二人杵在房中,相互无言。半晌,琴韵才率先开口道:“多谢陶大哥救了我爹。”陶泰道:“义不容辞,非我本意,何须谢我。”琴韵道:“还要谢谢陶大哥,帮我寻找我夫君的尸体。”陶泰道:“我没找到,有负重托。”二人又是一阵相互无言。
沉默良久,陶泰道:“琴姑娘,天色太晚了。你若没有别的话说,请回去歇息吧。”琴韵想:陶泰武功奇高,自己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小女子,面对着面,如何能够伤到他?遂道:“我想给陶大哥看样东西,不过,拿给你看之前,请陶大哥转身,闭上眼睛。”
陶泰眼睛微微闪出一抹光亮,毫不犹豫的转过了身,然后缓缓闭上眼睛。琴韵伸手轻轻拔下头上的发簪。发簪本是古人用来固定和装饰头发的主要首饰,也就是古人用来插定发髻或连冠于发的一种长针,后来逐渐演变,多专指妇女插髻的一种首饰。琴韵手中的发簪,针尖长逾半尺,非常锋利。
琴韵手中握紧发簪,轻轻移动莲步,走到陶泰身后,缓缓将手抬起。琴韵心中暗念:“陶大哥,我也对不住你了。”她自幼随父亲读书习琴,与医术也颇有研习,对人体经络穴位十分熟悉。当下,把牙一咬,认准陶泰背上死穴,发簪用力刺落。
陶泰似有所觉,兀自静静闭目站着。忽道:“琴姑娘,我对你并无非分之想。但是我一念之差,没有奋死一搏,疏忽了你的名节,铸成大错。望你不要永远怪我。”
琴韵打算刺杀陶泰同归于尽,眼见大事即成,突然闻听此言,心神一颤。刺落的发簪针尖及衣,却戛然而止。琴韵心思电转:“当时形势所迫,刻不容缓,急切之间是我有求于他。陶泰是因为我的哀求,才极力克制忍耐,答应同我拜堂成亲的。我刚刚渡过大难,便这样回对与他,怎么可以这样?我在做什么?”琴韵手上一松,发簪脱手落地,发出清脆的响声。
琴韵行刺不成,哀声道:“陶大哥,对不起。”蹲下身,双手抱着头,放声而哭,泣不成声。陶泰转回身,呆呆看着她,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房门外有人高声叫骂:“不仁不义的狗贼!乘人之危,夺人妻子,你枉披人皮!还不出来受死。”嗓音尖锐。其时,天色已晚,四空静寂,这一声传出好远,余音绕梁回荡。
陶泰内心烦苦,正在为眼前的情形犯难,不知如何以对。忽听了门外一声高叫,倒觉得被人解了眼前的困境一般,立刻脱离琴韵,抽身走出,到了房外。琴韵也听到了这声叫骂,只觉得声音十分熟悉亲近,一时偏又想不起是谁,止住悲泣,紧随出屋。
夜幕之下,院子中站着一个人。虽然光线昏暗,仍然可以看出,此人身高平常,身形很瘦,留着山羊胡子。陶泰和琴韵一眼认出,此人正是和释道儒、琴书医并列齐名同称为朝阳会“三三高手”的水暗轻。
琴韵抢步上前,叫道:“二伯。”水暗轻和琴书医、释道儒交情莫逆,不分彼此,他们三人关系十分亲密,一向以兄弟相称。尤其是排序在二的水暗轻,对琴韵颇具亲情,视如己出。水暗轻叹道:“唉,琴韵啊,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呀。”原来,水暗轻早就到了房外,并看到了琴韵想要行刺陶泰,后又无法下手的整个过程。琴韵哀伤地低下了头。
陶泰抱腕拱手道:“水兄,你来了。”水暗轻道:“陶泰,你还有脸和我说话?你身居左右护法高位,竟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陶泰也是堂堂正正的汉子,自知理屈,垂首不语。
水暗轻大骂道:“陶泰!你乘人之危,横刀夺爱,落井下石,不仁不义!琴韵丫头遭逢不幸,你不肯出头维护正义,那也就罢了,怎么能乘此机会,将别人的新娘占为己有?你心安理得吗?问心无愧?你良心何在?!你就不怕遭到天谴?这是人该干的事吗?猪狗也干不出这种事来。可叹,老会主一向高看你,怎么就没看出你的丑恶本质。陶泰呀,白瞎了你长的这幅摸样,你犹如畜牲,禽兽不如!”
陶泰站在当地静静听着,面对一连串的辱骂一语皆无。他默默承受着本可以不必承受的骂名,心中对自己叫道:“陶泰,你没志气。你本来好好一个男人,怎么就一时糊涂?你自作自受,活该被人骂!”
水暗轻越骂越气,大叫道:“你这种败类,让你活在这世上,实是天公无眼。我今天若不杀了你,天理难容!”不容分说,晃动双掌,直奔陶泰当头拍落。
琴韵吃了一惊,刚想出言制止,却听到释道儒的声音传了过来:“老二,住手!先听我说。”水暗轻手上一缓,撤回双掌。
释道儒和琴书医同时从院子外面匆匆走了进来。他们两人本已准备休息,只是心乱如麻,没有睡意,忽听到陶泰院中传来水暗轻刚才的那声叫骂,立即被惊动,赶来查看情况。水暗轻眼睛斜视了二人一番,说道:“你们两个,还有脸来见我?我却没脸见人,我没法活啦。”
释道儒道:“老二,你刚到,不了解详细情况。”水暗轻怒道:“我呸!我倒是不想了解详细情况,奈何整个徐州城都哄扬动了,到处都在嚷嚷你们的丑事,我想不听都不行啊。你们就不觉得难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