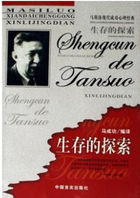政君的二哥王安突然得了急病,叫着肚子痛。李氏请来郎中也看不好,拖了几天就夭折了。
王禁内心抑郁,便在姬妾们的屋内喝酒解愁。
夏姬和任姬两人都有儿子,便借机在他面前哭哭滴滴的诋毁李氏争宠。新人都被卖了,再不趁此机会重新拢住王禁,那就傻了。
夏姬娇滴滴的伸出双手,给王禁续酒,感伤道:“安哥长得粉雕玉琢的,惹人喜爱,可惜这么点大,就……”
“庶子怎么比得上嫡子呢,若是崇哥病了,嫡母不晓得多着急。”任姬帮腔。
“哎,商哥每日从学堂回来,都要问阿父回家没有。”夏姬接着说。“商哥也为安哥难过呢,昨天还哭着说,哥哥还没有长成便夭折了,做弟弟的也很担心难过。”
说完停了停,又瞄了王禁一眼,接着说:“若是小心照料,也不至如此。”
任姬也难过的说:“就是,根哥也是许久没有见到父亲了,那天也为哥哥哭了一场。”
安哥的生母早死,一直放在李氏名下养着。
两人做一幅兔死狐悲状,王禁的脸色越来越黑,只是喝酒。
他本就对李氏有气,卖得那些姬妾里,有两个他正上心着。这火还没撒出来,正在心里拱着,现在姬妾们又都说得这么可怜。
这个女人,真欠收拾,王禁醉醺醺的想。
当晚,王禁进了李氏的院子。但不是她期望的夫妻美满,琴瑟和鸣。
他指着李氏的鼻子骂:“悍妇,你做的什么母亲?我把儿子交给你养,养得连性命都没有了。”
又说:“你当我是怕了你?你这个妒妇,若是能休了你,哼。”
李氏衣不解带的照顾着庶子王安,还得了这么句话,一颗心都凉透了。
这次,她只是哭,也不接话争吵,也不想辩解。
王禁发作够了,便摔门而去。
第二日清晨,政君请安时见阿母的眼圈乌青、眼睛浮肿,心下很是不安。阿父定是又被夏姬挑唆,欺凌阿母了。
姬妾们个个挤眉弄眼,在背后自然是嘲讽的更加厉害。
好强的阿母怎么受得住这个。
哥哥王凤在太学做博士官弟子,课业繁重,沐休日也不回家;弟弟崇哥被阿母保护的一派天真;其他兄弟姐妹有的在旁袖手看热闹,有的趁机掀点小风浪,叫阿父更加不喜阿母。
她听着阿母越来越多的提到了和离,心绪烦乱。如果这时候有人能劝劝母亲多好,自己和崇哥年幼,说话不做数。
得了乳母李婆子的提点,她托大奴王丹随阿父上衙门时,带信叫大哥速速归家,劝劝母亲。
王凤得知事情原委后,劝阿母不要冲动,再怎么还有崇哥和君姐要顾虑。
李氏听了决定先忍忍看。
按大汉律法,后妻生子继承家业优先于前妻生子。王禁这么能生,难保不再添几个嫡子出来。自个做着嫡妻,他尚且对几个孩子不喜。如果再来个后母,不知道孩子们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
政君方松了口气,父亲又做了件叫阿母出离愤怒的事:他没跟阿母招呼一声,便大摇大摆领进来一个妾,说这是蜀郡的郡守以示谢意送的。
这小妾腰肢柔软,甚是水灵,据李婆子说深得父亲喜爱。
父亲的姬妾婢女大都被阿母卖了,留下的都是几个生过孩子的老人。有这个新鲜的,依父亲的性子,他眼里一时不会有别人。
政君冷眼瞧着这小妾独宠之后,便甚是张狂。
父亲总不给阿母好脸,当着众姬妾和庶子庶女们的面就说阿母不贤惠。作为大妇对夫君的爱妾过于苛刻,不给她好吃好穿,也不添几个侍女伺候,一点没有做大妇的度量。
小妾愈加张狂,其他姬妾们只是围在一旁看热闹。
政君已不知该如何安慰好强的母亲了,她恼恨自个年幼,什么法子都没有。
李婆子日日在她耳边絮叨阿母如何不易,父亲如何薄幸。她越来越厌恶父亲,却又觉得阿母若是早早和父亲缓和,何至于被暴怒的父亲踩到脚底。
李氏勃然大怒。
做嫡妻做成这样,还不如给人家做妾呢。忍他忍了这么多年,不想再忍下去了。
她第二日便悄悄回了娘家,将多年的不如意哭诉一遍。
哥嫂方知她平日里只是要脸面,不愿向娘家求援。哥哥李翰卷起袖子要为她讨个公道,却被她拦住。
她不想讨回公道,只想和离。
王禁不过是个低级的廷尉史,便这么张狂。如果他仕途上再升几步,她更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李翰最疼这个妹妹,见妹妹说的如此艰难,堂堂男儿心酸的都落下泪来。夫人赵氏最是个夫唱妇随的,便和李翰一起合计接小姑子归家。
李氏得到哥嫂的支持,将事情商议定了,便择日在正屋里摆了小宴,请王禁过来说话。
王禁以为李氏受不住这阵子的磋磨,要服软了。却万万没想到,李氏一脸平静地提出要与他和离。
他大怒,踢翻了酒樽,如此不贤之妇居然想休了我。
你要走我就不送了,王禁点了头。
政君知道这个消息时,已是晚了。
她忙将哥哥叫回府,几个孩子跪在阿母身旁,哭成一团,阿母只是不松口。
李氏只担心君儿相貌甚佳,尚未许亲,王禁又是个靠不住的,将来不知她会遭继母几多搓磨。凤哥就读太学,考通一经就可以选官立业;崇哥毕竟是嫡子,还有哥哥照看。
她摸着政君的发顶,诉说着:“君儿啊,别怪母亲狠心,实在没法和你父亲过下去了。天天气闷,总有一天会闷死在这个家里。
……你父亲长得仪表堂堂,又许诺我今生不他娶,我才嫁给你父亲。李家的家业被我搬了一半过来,可是你看看你父亲一天到晚都在做些什么?自从做了廷尉史之后,仕途上再也没有进一步。日日应酬找女人,有点颜色的婢妾他都不放过。
当年父亲母亲也恩爱过,我为了他辛苦操持这个家没有一点怨言,可是他是怎么回报我的,连个小妾都不如。
颜色好时,他宠着我,我便以为会这样一辈子,现在姿色尚在,他就已经眼里没有我的位置了。凤哥、崇哥兄弟两个我都不担心,只担心你。
女人陷入情爱之中就会变成瞎子,男人总是朝三暮四。女人对待男人一心一意,男人的心却总是会一变再变。《诗经》里也这样说: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政君听着阿母絮絮念着,泪水糊住了眼眶,喉咙里有股气梗着,呼吸都变得困难。
她长这么大,从未如此凄楚过,活像心被人生生剜了一块去。
阿母就这样丢下她和崇哥了吗?难道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吗?没有阿母的孩子,怎么活得下去。
阿母陷入了自个的絮絮叨叨中。
“你怨我时便读读这首《氓》吧……”
政君喊道:“阿母,我和崇哥还小,离了您可怎么活?”
她不想再听阿母说下去,父亲不喜她和弟弟,阿母不能再这样丢下他们不管!
“阿母,您要走就把我和崇哥都带走。父亲并没有说要与您和离,您为何如此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