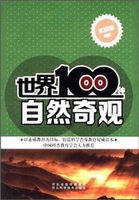苟宾本想跳起来还击,听得李氏一声娇呼,他便晃了晃身子,抱着脸蹲了下去。
李氏紧随着蹲下身去,板着苟宾的脸,急急问道:“苟郎,怎么样?”。
苟宾的二子苟成从车内跳下,疾跑两步,用头对着王禁的肚子顶了上去。
他大声叫道:“你这个坏人,野人,为什么打我阿父。”
王禁见她如此关心苟宾,心中更加怨恨。一使劲,竟将苟成甩了出去,苟成哇哇大哭。
李宅门前吵成一片,惊动了李翰和赵氏出来查看。
李氏扶着苟宾,又担心着苟成。恨声道:“王禁,你这是做什么?连个孩子都不放过。”
王禁看着苟宾捂着脸不放手,气更不打一处来。
这厮明明是欺骗我家亲儿,偏偏这会亲儿这么相信他。
一时也顾不得了,怒喝道:“你还问我,做的什么好事?不守妇道!”
正哄着苟成的李翰,一改以往好脾气,大声质问:“王大人,我妹子怎么不守妇道了?她现在是归家妇,你凭什么来讲这句话?”
王禁愣在那里,闭上了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李氏扶着苟宾便往院内走,她一双妙目,因为生气变得更加明亮。
临进门前,她回过头来,狠狠的瞪了王禁一眼。
王禁想起当年他逗弄李亲,被她也是这么狠狠一瞪迷住了。
大门关上了,他还在回味着那一眼。
那时他多么年轻,是个风度翩翩少年郎。他长得俊俏,又充满了雄心壮志,发誓要做到绣衣御史,重振家声。
在河边见到李亲时,他觉得这个长相明艳、脾气火爆的小娘子,逗弄起来分外有趣。
等惹得她怒目相对时,他却被她那一瞪迷住了。
他愣在那里,刹那间像是有一万匹马从心头踏过。
王禁摸了摸脸上,竟有些水滴。
这么些年他的志向还有他的女人,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
马儿在树下嘶鸣了一声,他回过神来,也不管周围的人指指点点,骑上马绝尘而去。
王禁回想着往日的一幕一幕,他这才发现,李氏也是可以离开他的。
现在,她一定去安慰那狗东西去了吧。她一向心软好哄,只怕现在一颗心都要站在狗东西父子那边了。
王禁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有点混乱,抓不住头绪。
他回到家中,觉得烦闷,想找个小妾说说话,却发现没有人选。
小妾都是用来解闷的,不是解惑的。
政君接到了王丹的消息,知道父亲碰了钉子回来,正一个人在书房里闷坐。
她便煮好一壶茶,用白色的盘碟配上阿母在家时常爱做的青蒿饼,再用木盘托起,端往书房来。
她轻轻的走到廊前,恭声问道:“阿父在吗?”
王禁说:“进来”
政君端着木盘走入,将东西放在案上。又施个礼跪坐在一边,给父亲沏了杯茶,柔声说道:“阿父,女儿才学会煮茶,听得阿父回来,特特端来请阿父喝了消渴。”
王禁的心气略平,他低头看到木盘中配的茶食,竟是青蒿饼。便问:“我记得清明前后方有青蒿可做饼,现在时节已过,你是如何得来?”
政君笑笑说:“阿母闲来无事,命人将青蒿分批种下。外面的青蒿已经长老,她种的青蒿却刚刚好。阿母教我做青蒿饼,我便将青蒿也带了些回来,不知阿父爱不爱吃。”
王禁看着这青蒿饼,百感交集,一时之间竟不知说什么好。
他拿起青蒿饼,大大的咬了一口,对政君说:“茶艺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这青蒿饼已深得你阿母真传之五成。”
“对你来说,已是不易了。”王禁怕女儿不悦,又忙安慰。
王禁吃着这青蒿饼,想着李氏那临别一瞪,不由得一叹。
政君知道父亲这是睹物思人了,她走上前去,轻轻为他捶打肩部。这个举动,她见大姐君侠讨好父亲时做过。
王禁闭上眼睛,过了一会,他问:“君儿,凤哥几时回来?”
“哥哥正在太学苦读,他说要争取今年年末岁考时通过策试选官。许久没有回家,只叫小奴回来带过几次衣物。阿母在舅家也很惦记他,生怕他瘦了,只顾读书,把自己熬病了。阿母常说……”
王禁睁开眼,扭过头看着她。
“阿母常说,商哥聪慧讨得阿父喜欢,凤哥自觉不如,所以常鞭策自己。凤哥还小,正是养身体的时候,不应如此拼命读书。”她的声音越说越小,王禁的心也越发低落。
他换了个话题,对她说:“崇哥可睡下了?”
“还没有呢。我叫他在屋子里先耍会,不要到处走动,免得走了困。”
“好,一起去看看崇哥吧,阿父说好要去看他写的大字。”
她讶异的看了看父亲,没想到他到记得抚慰崇哥的话。父亲还是有些好处,例如言出必行。
崇哥献宝一样,将几张歪歪扭扭的大字捧给父亲看,一脸期待的表情叫王禁忍俊不禁。
他让崇哥跪坐在他胸前,握着崇哥的小手,一笔一划的教他运笔。
崇哥的脑袋晃了又晃,激动不已。父亲走时,还抱着王禁亲了亲,发誓般说:“阿父,崇哥会好好写字,一天写好几张。”
王禁大笑道:“崇哥,好好写字。字是读书人的体面,可别没了脸面。”
走时又摸了摸政君的脑袋,说:“早点睡吧,明早阿父去太学看看凤哥。”
他想,苟宾,你有个儿子帮你。我却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谁在李氏的心里重呢。
政君和崇哥在屋子里欢呼起来。
王禁听了忍不住轻轻一笑,他背过手去,离开了女儿的院子。
这世上只有敌人最是惦记你,苟宾现在被王禁惦记上了。
苟宾可顾不上这么许多,李氏就跪坐在他旁边,刚刚给他父子两个搽过药。
李氏扶着他进李府时,他第一次挨着李氏如此之近,近的能看到她耳边的一颗小痣,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气,像是熏得梅花香。
他并不觉得痛,只希望这条路再长些。
听得二郎苟成在身后抽抽搭搭的哭着,他知道其实那一摔不是太严重。
二郎很喜欢李氏,想多获得些怜爱罢了,这孩子自小便没了母亲。
进到屋内,李氏看着他的脸,倒吸了一口气,嘴唇动了动,终是没有说出什么来。
他知道眼圈定是被王禁打黑了,但这又有什么呢?
李氏拿了药给他搽试,她袖子里发出那醉人的幽香,他早已魂飞九天了。
二郎也凑过来,掀起袖子说:“美人姐姐,也给我搽搽,呼呼会好的快些。”
他们父子得到李氏这么多的关心,十几年来,两人感情上首次贴近了一大步。
这可要好好谢谢王禁。
李翰和赵氏都借故离开,李氏犹豫着说:“苟郎,我这次连累你了,我……”
苟宾顾不上二郎就在身旁,生怕李氏会说出什么更见外的话。
他伸出手去,隔着案几,抓住李氏的手,激动地说:“不连累,一点都不连累。我……,我其实也没有伤的那么重,我只是不想叫你为我和他为难,我只是一点私心,我……。”
他越说越乱,越说越急,最后竟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只是知道千万不要让李氏往下说下去。
苟成在一旁很是焦急,阿父怎么就这么笨呢,哪有人说自己挨打的并不重的。
“可是,我很痛啊。”他终于受不了阿父的笨拙,叫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