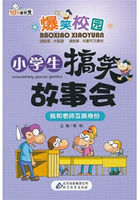“现在已是深秋了吧?”无衣坐在马车的横辕上,听见身后传来霍去病的声音,他撩起竹帘的一角朝外张望,长安城的八街九陌依然繁花似锦,农人、商贾、走卒在宽阔的街道缓慢行走,人们早早换上了厚重的粗布罩衣,只有梳着髫髻的孩童,尚不觉寒意,仍然套着短打的半截裤子,汲双草鞋一路欢笑打闹在路边奔跑,空气中混杂着秋尘和草叶枯萎沤入泥土的腥咸味道。
“差不多是吧。“无衣扭过身子回道,他的脑袋瓜子里这一刻还顾不上关心天气的变化,屁股蛋被马车的横辕颠得生疼,他嘴里念念有词地嘟囔道:“爷,咱们为什么不骑马去呢,这马车慢得要死,一路上颠得屁股又疼,恐怕半个时辰都还到不了呢。”
“就你话多!你以为我不想骑马?可这位韩大人平素迎风弄月,最好风雅,为人又讲究格调排场,嘴巴惯是刻薄不饶人的。前次我骑马过去,被他冷言冷语好一顿排遣,说什么‘扬起的飞尘污了他家门口的台阶’,‘马嘶蹄踏惊了他家的鸟雀’,那些雀儿平时就叽叽喳喳的没有安生的时候,偏偏被我的马的给惊了吗?居然自己提了桶水来泼我,为了息事宁人,我索性依了他的性子坐马车去好些。”
“这样矫情的家伙你去他府上干嘛?”无衣一脸看怪物的表情看着霍去病,“不是自己找虐的吗?”无衣歪着小脑袋瓜,兀自在脑海中想象着这位韩大人的面目,只依稀描绘出巧笑盈盈的眉目,邪魅轻笑的嘴角,俨然就是一只千年成精的狐狸。狐狸!无衣一愣,怎么是狐狸,先前赵破奴被他想象成了一只大尾巴狼,如今又跑出来一只狐狸,最近怎么老跟这些豺狼虎豹反冲哩?莫不是中了什么邪吧。
无衣用力甩了甩脑袋,却被霍去病伸手用力推了一把后背,“发什么愣呢?已经到了,还不下去!”
无衣慌慌张张地跳下马车,落地不稳险些跌了一跤,站定了去霍去病掀起门帘引他下车,却见一衣裳华美的男子领着身后几名婢女仆从,笑眯眯地站在门口,男子身穿一身素白的丝缎深衣,外衣的薄纱清晰可见,一层层裹叠,内里雪白的锦缎裙裾上绣有血色八重菱纹的图案,朦朦胧胧地透出来,精致典雅,而后随时的婢女与仆人也都妆容端庄精致。反观来客,霍去病倒没那么讲究,藏青色棉布直短襟外挂,浅棕色的直衣修饰修长笔直的身段,显得潇洒而飘逸。
“总算是来了,让我好等。”韩嫣迎上前来,眉眼含笑的宛如弯月。“还有你这小鬼。”
“怎么是你?!”无衣毫无形象地当场大叫,引来众人惊异的目光,无衣慌忙捂住嘴巴,这个人不就是当初在未央宫里遇上的那个嘴巴刻毒,含沙射影埋汰侯爷和自己的那个娘娘腔吗?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你、这个狐狸……”无衣指着韩嫣怪叫道,随侍的仆从一听变了脸色,倒是韩嫣并不介意,拍手笑得前俯后仰,突然凑近无衣的鼻尖邪魅一笑,故弄玄虚道:“居然被你了看出来,今晚我定要带你回我的洞府,你可得乖乖地把自己洗干净了候着我。”
狐狸,果然是狐狸!无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眼前的人,他的眼睛仿佛有着无形的魔力,黑色的空洞里闪烁着点点忽明忽暗的星光,魂魄仿佛都要被吸了去般地空掉了,思绪却早已飘到了的九霄云外。
“发什么呆?还不快点进去。”霍去病回过头敲了一下他的头,转身并肩与韩嫣往外走,无衣之好赶紧跟上去,对于这个人他一直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却不知道感觉从何而来。
作为身为帝随侍贴身的近臣,此前无衣也依稀听闻过这位韩王孙的事迹,自帝幼时尚未胶东王时起就已随侍在侧,终日学书友爱、玩耍嬉笑,与帝同卧起,论亲厚友爱竟比皇后妃嫔更甚,帝对他的偏宠连太后都颇有微辞,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从国策朝纲乃至宫闱秘辛,帝似乎从未打算对他有所避讳,而诸多无法摆上台面处置的事情,帝大多经由他的手悄无声息地落定,那些看似手握重权的丞相、御史大夫或是大司马之类的公卿重臣,论起实权竟不如他一个大夫,着实应了那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玄机。无衣知道这位韩大夫在朝堂之上专司为帝执剑,回想当初还被他误以为自己是侯爷的小姓,乃是出入永巷以色侍人的男宠,一想到这,无衣就气得不打一处,对这位韩大人的印象大打折扣,简直连靠近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但韩嫣似乎并未察觉无衣那点小心思,只听见他慢悠悠地说道:“今儿我府上还有一位贵客,你定是要见上一见。”他故作神秘地眨眨眼,瞳孔里透着一丝狡黠的精光,霍去病狐疑地点了点头,也不多问,随着韩嫣的脚步一路走进去。
功臣之后,天子宠臣,韩王孙的府邸自然不同一般王公贵族,只见四足堂门里宽阔敞亮的院墙,被细密砂石与绿植点缀成了枯山水的景致,这番景象尚不足满足他品山乐水的兴致,而后回廊外的院墙后,又另外打造了一处清静幽秘的亭台水榭,高大的珊瑚树被安放在假山绿枞之间,纵使秋日亦有百花繁盛花团锦簇,霍去病听闻他专门从西域请来专长园艺的工匠,不知是用了何等高超的保鲜机巧,硬是将那些只在春夏时节开放的花树延长到了秋日也未凋谢,帝也深以为美,经常携近臣妃子们下榻王孙府邸,游乐赏玩。
无衣好奇地跟在他们身后,他身在冠军侯府,看惯了侯府的冷清肃静,倒不习惯这满目繁花的胜景了,空气里弥漫着甜腻的花香,门廊上精心雕刻着团花与菱红蝴蝶的图纹,径直穿过长长的中门廊,走近前院寝阁的内间门廊前,眼见一道经锦帘幕下端坐着一位年轻女子,
深红色的二重织上衣,衣段表面浸染的菱蒂纹八叶菊拥簇五凤齐飞的图案,瀑布般乌黑的长发油光可鉴,挽成两股高髻,用一支紫金细簪斜插入云鬓,肌肤白若凝脂,细小的美人尖,又细又长睫毛斜斜地仿佛要坠入眼睛里,樱桃小嘴上一点朱红蔻丹,然而这一切尚不足以令旁观者砰然心动,直到目光转移到女子右眼角下哪一点墨色的泪痣,盈盈欲坠的凄美之色,令人顿是心生怜爱,满怀柔情。
“这位夷安公主”韩嫣抬手道,“去病可有印象?”站在一边的无衣听出韩嫣称呼侯爷的名姓语气异常亲昵,就算是李敢在人前也只敢“侯爷”或是“将军”,韩大夫去直呼其名,无衣总觉得哪里怪怪,说不清道不明,索性将目光转移到了那位夷安公主身上,自打娘胎出生,他还是头一次见识到真正的公主究竟是怎样一番模样,在他眼里,这公主无非比寻常人家的女儿穿戴华丽些,会用许多漂亮的首饰脂粉打扮自己,单论相貌,无衣倒觉得自己从前村里的小姐姐,模样倒也不比这位公主逊色。
“记得,上次在宫中行走时还曾遇上过,我记得当时是窦太主的家奴对殿下不敬,所以才……”无衣眼见这位公主含羞露怯的眼神中明显带着几分惊喜,那股爱慕的眼神即使是无衣这般懵懂天真的年纪,也能察觉几分,他只在一旁捂着嘴偷笑。
“妾身见过冠军侯,上次多亏侯爷解围,才令妾身不至在大庭广众之下遭遇难堪。”夷安公主的声音轻悠悠的,很慢,犹如她的相貌,端庄优雅中总含了几分幽怨之气。她端正身姿想要举手齐眉作揖礼,却被韩嫣和霍去病同时拦了下来。”公主千金之躯,怎能行此大礼。”霍去病说话向来干脆,夷安见他坚辞不受,只好微微直起身子,将双手轻轻搭在左腰处,微微屈膝低头道了一个万福礼,如行云流水般轻柔飘逸,绝无半分做作,随时在一旁的无衣这才见识到了何为居颐养气浑然天成的皇家气派。
“罢了,光顾着讲客气,新沏的茶水恐怕也要冷了。”韩嫣吩咐下人铺榻摆案,”我嫌内堂的光线暗,景色不好,索性把案几、茶具和食盒都搬到这堂门前的走道上,诸位都不介意吧?”
说罢,见府中仆人鱼贯而入,茶龛、涤器、茶洗、汤瓶、茶壶、茶盏一应俱全,秋意寒凉,他特意命人在院子空地处升起一盆炭火,将那巧夺天工的姜铸铜的饕餮兽面火炉慢熬其上,又取来紫砂茶壶用砂器茶洗来回暖烫那朱砂茶碗,最稀奇的莫过茶龛边一台摩羯纹蕾纽三足盐台,银质的莲花提手,金色卷荷包边的纯银盖壁上饰有团花与四尾摩羯的图案,无衣听韩嫣府上的仆人解释才知道,这是专门用来放置茶中调味用的盐巴、熟豆、炒米、枣粒之类的容器,支架上有朱雀双飞的雕塑立于其上,栩栩如生,着实令无衣大开眼界。他在侯府专司沏茶,虽也甚至侯爷吃穿用度一应讲究,却未及这位韩大人的十分之一,难怪世人都赞这位韩王孙一派风雅无人匹敌。
韩嫣从金丝楠木的香盒中拣出一撮苍术掷于香炉,一边净手一边道:”今日府上都是贵客,由我亲自为各位沏茶。”一番焖烹洒浇后,他笑盈盈地递上紫砂朱红檀木碗,霍去病皱了皱眉头,看着碗中暗沉幽盈的茶汤。
“我不喝六安茶。”
“美得你,还没到岁末,陈茶老茶尚未积实,想喝也没得喝呢。”韩嫣冷笑道,“你也太低估我的眼力,六安药性太重,怕冲撞你一直服用的汤药药性。这可是赣南新近才上贡的银丝冰芽,专取新茶茶心的嫩芽,用甘泉宫的泉水漂洗,取龙脑冰片生地的异香薰制而成,再用刻有梅花纹路的磨具压制而成,雅称‘踏雪寻梅’,今年多雨,茶资原本就不多,这还是我求了陛下好多回才赐了我这一小罗,你还敢嫌弃?”
无衣一听如此金贵,迫不及待抓过眼前的茶碗,牛饮一海,却又龇牙咧嘴地吐了出来,“呸!好苦哇!”一边吐着舌头哀叫,小脸儿皱成一团,滑稽的模样逗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苦就吃点这个。”韩嫣递过案几上一小瓷盅玫瑰红的蜜饯。“西域新进来的蜜瓜,还有甜瓜,用蜂蜜与玫瑰花汁浸泡过,吃吃看。”无衣一听,赶紧哧溜一下抓过一把果子塞进嘴里,无意中却发现韩嫣右腕沿着袖括往后滑落时,一道粗大狰狞的伤疤突然显露出来,无衣一愣,迟疑地看了对方一眼,却被韩嫣微微一笑,不着痕迹地遮掩了过去。
“甜!真甜!“他咂巴小嘴,一边还用嘴吮吸指尖上鲜红的糖渍。
“先苦后甜,人生亦是如此。”韩嫣笑道,转而对霍去病说道,“如此说来,倒是你那头风寒疾,最近一向可好。若是不好,我再请宫中御医配些丸药你带在身边。”
“无妨,已许久未曾发作,我亦停药了一段时间,想必已经痊愈了。”
”那就好,这样我也安心了,若是上了战场再受风疾所困,恐怕难以招架。”韩嫣说道,“现在这般讲究,看你上了战场能喝什么?别说什么六安老君眉,能喝上雨水和稀泥就得谢谢老天爷了。”
“这倒无妨,我听博望侯说,祁连山中的金泉俯仰天泽,吸取天地万物之灵气,泉水至清至纯毫无杂质,我挺想试试用那泉水烹茶煮酒,是怎样一番滋味。”
“怎的冠军侯会有头寒疾,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一旁的夷安突然问道。
“没什么,只是幼时喜贪寒凉,又无人照管提醒,未及保养,所以每到秋冬寒节就头疼难忍,这还多亏了韩大夫配制的丸药已无大碍,并不是什么大事。”霍去病轻描淡写地回道。
“如此这般才好。”夷安轻轻舒了口气,注意力转移到了无衣的身上,她伸手抚过无衣的额头,好奇地问道:“多伶俐的孩子,多大了?”
“不说我倒还忘了,还不快向公主请安。”霍去病拍了拍他的背,无衣赶紧屈身向夷安行礼,回道:“小人无衣叩见公主殿下,小人年方十四,是侯爷家中新进的仆人。”
“你这么小,就独自出来谋事,家中双亲可曾放心?”夷安惊讶地问道。
“小人家中亲人都被匈奴人杀了,独留我一人逃了出来,本来想来长安投军,侯爷说我年纪太小需要打磨历练,就把我留在身边贴身使唤了。”
“真是可怜见的。”夷安蹙眉低叹,她长年深居幽宫寒院,并不曾亲身体会过寻常百姓的生离死别,所谓战争屠戮的苦痛亦只是宫人女眷茶余饭后的谈资所得,但她亦曾经历过骨肉分离的刻骨铭心,自幼母亲病逝,父皇冷落、兄弟姊妹的轻视、宫人奴婢的趋炎附势,早已习惯了这宫闱之内的世态炎凉,唯独孤独的清冷着实难挨,这一刻无衣能感受这位公主是打心眼真心实意地心疼自己,为自己的遭遇悲伤难过。她轻轻抬起右手的袖括,遮住下半边脸孔,眼睛里水光莹莹,轻叹道:“冠军侯也是惯会替人操劳的心思。”
韩嫣转过头对霍去病说,“你当见过公主不止一面吧?”
“还有一次,”霍去病低下头抿了一口碗中的茶汤,“年初宫中春祭上的《郊祀歌》便是殿下跳的。”眼见夷安的脸上悄然染上些许绯红,韩嫣欠过身追问道:“你觉得如何?”
“甚美。”他原本就不擅长用华丽的言辞取悦女子,更不要说此刻韩嫣别有用意的试探。
“就这样?”韩嫣一愣,虽然知道他秉性冷淡寡言,但不料如此简单明了的两个字,就把自己给打发掉了,让一向喜好八卦舆闻的韩王孙着实觉得无聊又无趣。
“难道不是?”霍去病反将一军,反倒让韩嫣顿时没有言语,眼见他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真心分不清这个榆木脑袋是真不懂,还是扮猪吃老虎地装傻充愣。他无奈地摇摇头道:“公主殿下不仅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瑟,今日我特地请她屈尊前来,就是拜她赐奏一曲,让我等聆听神仙雅乐,一饱耳福。”
“见笑了。”夷安笑意盈盈地侧身取来一张瑟,横摆于膝上,伸出纤纤细指拨弄调音,“此番承蒙侯爷搭救,妾身无以为报,仅以《九歌》一段致谢。”说罢伸出纤纤细指撩拨一弦: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琴音沉涩哀婉,愁肠百转却都化作了根根丝弦绕指柔,银质的火取里苍术焚烧的白雾,从镂空的菊花纹菱里一点点弥散开来,透出秋意萧瑟的凄凉,听者一片静寂,韩嫣开口道:“真不知湘夫人盛装打扮立于江畔,日夜等待湘君前来赴约,却始终未等到良人归来时,是何等失望哀怨的心情。”
霍去病默然不语,低下头盯着手中盛茶的杯盏,来回摇动碗里的茶水,偌大的院墙静得几乎可以听见蝴蝶振翅的微颤,三人对坐在廊檐下的木地板上,看一池花树在风中摆动,只有清风吹卷竹帘发出的“啪”、“啪”的声响。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无衣没头没脑的插话打破了良久的沉寂,气氛顿时从沉闷中跳脱出来,霍去病忍不住松了口气。
“你还小,当然不会明白。”韩嫣眯起眼睛看着一脸茫然的无衣,笑着说道:”等你再长大些,自然会明白何谓长相守、何谓双飞燕,何为一点相思两处愁。”
“额……”无衣一双鹿眼眨巴眨巴,却着实猜不透眼前这几个人到底在故弄玄虚唱得哪出戏,只好闷闷地拿起手中的蜜瓜狠狠咬了一口,果肉碎渣子糊了满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