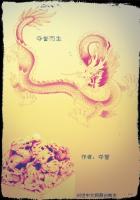下了一夜的雨,丁哨官一行人总算是熬过了这难过的一宿。肖公子本就不想费劲的跑,在他看来这行人本就不必把自己看得这般紧。他肖展是何许人也?柳叶门大当头的大公子。在太原府哪个州县吃不开?江湖上的人自不必说,哪怕是官面上的头头脑脑哪个不买柳叶门的面子?这一路上虽然受了点皮肉之苦,但他自己从不担心自己的性命。要他肖大公子的命,除了当今天子,只怕是还没哪个敢做这般不要命的举动。
一行人在民户家里掏了些粮食,囫囵对付了一顿便要继续上路了。镇上的保长生怕得罪了这帮官差,领着一帮子乡民唯唯诺诺的在白楼下送走了这帮瘟神,这才长舒了一口气,各自回去忙农了。
肖公子在囚车里坐得不爽利,又拿丁哨官打趣:“我说丁头,小爷方才没吃够,好几天没沾荤腥了,咱们到了驿站,叫些酒肉打打牙祭如何?”
丁哨官笑了笑,答道:“那也要看到驿站时是什么时辰,若是还早,这顿酒肖公子不说我也是要请你吃的。”
肖公子答道:“爽快,不过这酒就不需你请了。你身家才几斤几两?小爷还有点盘缠,到了驿站,我请这一路上的所有弟兄吃个饱。”
众人听了这话,交头接耳起来。有的憨直的汉子还和肖公子打趣。有的则窃窃私语。本来这肖展已经是阶下之囚,都已经是关在囚车里的人了,居然还摆这大公子排场。这般不知深浅,只怕是全天下也只此一家了。而有人又悄悄和他争论,大不了又是讲这肖公子的家世如何如何。
总之就是一路嬉闹,到了快晌午,果真到了一处驿站。只是这驿站看也不像是有什么好酒好肉的样子,前后皆是深山,开在这里,若不是为了接待往来的公文官家,哪里还有几个乡民商客经过?
肖公子见这驿站萧条,兴致也少了大半。张狂的抱怨起来:“真是气煞小爷了!这鸟不拉屎的破馆子,小爷还想好好歇息一番呢!丁头!你们领的什么路?!就不能走商道吗?非要捡这一年也用不了几次的官道!”
丁哨官拉了拉缰绳,笑道:“公子说的是哪里话,我们奉命进京,不走官道,一路上的粮草公文和谁交接?还有马匹也要更换,难不成您愿意掏这银子?”
肖公子被说得哑口无言,只能看着这破驿站叹气。
驿站里的驿卒听到外面有车马的声响,赶忙走了出来。见浩浩荡荡一票人,赶忙上前相迎。那驿卒满脸堆笑,对领头的丁哨官说道:“辛苦上官了!小的恭迎。”说罢,驿卒又冲驿站里喊了一声。只见里面又跑出来三个高矮不一的驿卒来。个个都是不敢怠慢,牵马的牵马,接缰绳的接缰绳。
丁哨官倒是没什么摆谱的架势,对那似乎的管事的狱卒说道:“我们奉太原府知府之令,押解人贩进京,途经这驿站,还麻烦老哥周转一番。印了帖子,换两匹好马我们就又要赶路了。”
那驿卒头头笑道:“上官公务繁忙小的知道,不过驿站里的马匹不巧被人领走了。我们县是个穷县,没那么些马匹备着,上官您......”
丁哨官眉头一皱,放慢了要进驿站的步子,问道:“有这么巧?两匹马也换不得吗?”
驿卒为难的答道:“上官赎罪,还真是这般凑巧。昨天才有人拿着公文牵了马匹走了。说是有急件要送到京城。我们哪里敢拦啊?”
丁哨官只得悻悻的又往小楼里走,说道:“也罢,只能凑合着了。那你去取些酒食来,我们赶了两天的路,不好生歇歇只怕是要误事了!”
狱卒点头哈腰,笑道:“酒肉小可倒是不敢怠慢,小可这就去取。各位上官请自便,片刻就上到各位桌上!”
丁哨官挥了挥手,找了个偏大门的位子坐了。囚车被放在门外歇马的草棚边。而里面的肖公子被几个衙役“押”到了丁哨官所坐的这一桌来。
肖公子坐到长凳上也不客气,扯出一张银票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嚷道:“酒肉只管上来,吃不完我们带走!”
驿站里的两个驿卒见这架势有些茫然。还没见过这般大势的囚犯。个个都不知如何搭腔。那为首的狱卒见状,提着一罐子酒笑盈盈的从后厨出来。边走边说:“咱们这里庙小,装不下各位爷爷,小可不敢怠慢各位。自然是把好酒好肉都拿出来给各位上官享用。不过要带走只怕也不够。还请各位海涵。”
丁哨官笑道:“老哥你只管拿出来便是,我们吃饱便是了。”
驿卒头头见丁哨官也不接话茬,也不好再出言打听这嚣张的囚犯是何许人也了。放下酒罐子,点头哈腰的又去后厨招呼了。
不多时,切好的牛肉,洗净的蔬果,还有些粗糙的茶点倒也摆了一桌。其他衙役兵丁面前也都不多不少的摆了些。要吃饱喝足不一定,但比一路上吃的稀粥干粮已经好了万倍。一行人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番,都给吃了个干干净净。驿卒们忙里忙外好一阵折腾,好容易伺候了个遍。等到这帮人吃完,已经是烈日当空了。眼下时节虽也不是酷暑,但昨晚的一场大雨,天上哪里还有整片的云彩。烈日之下,一行人在棚里竟也热得大汗淋漓。
丁哨官见这天色,实在是不适合赶路。只得安排了人手后,决定歇息一两个时辰再说了。只怕是这帮人昨晚都没睡个好觉,坐了一会儿,竟有人扯起鼾来。其他人见状,先都还不敢打盹,但无奈这天气正好合适,不一会儿,倒也睡倒了一片。
丁哨官哪里敢睡过去,强拧着瞪着眼睛,丝毫不敢把目光从肖展身上移开分毫。不过毕竟是血肉之躯,就这帮坐了两刻,眼睛皮也不住的打架了。虽然肖展老老实实的趴在桌子上打盹,丁哨官还是不能放松。哪怕是趴也要趴在肖展身上才放心。
就在丁哨官就要睡着,突的听到有人惊呼。丁哨官瞌睡醒了九分,赶忙抬眼去看。这一看把那剩的一分也吓得没了。三魂都丢了两魂。
只见驿站马棚一边的架子已经散架,被绑住拖囚车的马匹被一头黑乎乎的巨熊按倒在地。旁边的两匹马见状正拼命惊叫。一匹马竟扯断了缰绳往人群这边冲过来。
众人见状赶忙躲闪。不料有不走运的被马蹄踩中,手臂生生的一声脆响,断成了两节。其他人哪里敢去阻拦,都是往惊马的两边闪躲。一转眼,那受惊的马已经跑得没了影。众人这才伸手去搭救方才被踩的两名衙役。
在马棚另一边的一匹马死命的拉动缰绳,竟然一下子把马棚拉倒,棚上的茅草散落一地。那马刚要逃脱,不料按住地上已经断气的马匹的那头黑熊,一爪子便拍到这马身上。想一匹马少说也有两三百斤,这一掌下去,竟然直接被拍出去快一尺远。
众人大惊失色,只敢往驿站角落躲去。哪里敢去与那黑熊搏命?丁哨官见状,拔出腰间的佩刀,大喊道:“这畜生!竟敢白日里行凶!”一挥手,对身边的兵丁衙役喊道:“还不抄起兵器!难不成等着畜生取我们的性命吗?”
其他衙役兵丁这才回过神来,抄起了长枪短刀,纷纷摆开了架势。不过这黑熊实在骇人,方才那一掌都看在眼里,这要是拍到人身上,岂不是肠穿肚烂?
人群中,驿站的驿卒也都面如死灰,那领头的驿卒颤颤巍巍的说道:“这是哪里来的畜生......怎么......”
丁哨官问道:“这不是附近的熊?”
驿卒缩在后面,答道:“小可在这驿站当了十几年的差,从没见到有这么骇人的畜生......”
在丁哨官身后的肖展这时表情却是好不动容,不知是不是已经吓得失了神。
丁哨官发一声喊,大叫道:“小的们!一起上!杀了这畜生!”
众人毕竟不是流氓泼皮,手里拿着兵器胆子也要壮了几分,丁哨官一发喊,十几个人都往黑熊冲将过去。那黑熊也大吼了一声,竟然站了起来。
这一站,又把众人吓退了数步。只见这黑熊站起身之后足有两人多高,像是庙里的金刚罗汉一般。这哪里是寻常人敢去惹的?黑熊往前一扑,前排的几个兵丁没被扑到也都被吓倒在地了。后排的人见状更是吓了个半死。接连后退。
但凡战阵,就是讲一个气势,气势若是没了,哪怕你人数再多也只有溃败的份。而且只要前面有人先退了,人越多越是容易溃逃。将领哪怕有再强的手段,也只有自认倒霉。因此战阵上皆有督战官,但凡见有人溃逃,督战官是要在战阵之后杀人督战的。而这伙人,平日里都是在衙门里养着,没上过战场,更是没见过尸横遍野的场面。前排的人一倒,后面的人都抄着手里的兵器倒着往回跑了。
后面的丁哨官眼见这十几二十来个人都要跑,赶忙踢了一脚冲自己冲过来的一个衙役,骂道:“入娘贼!跑什么?!”那被踹倒在地的压抑,趴起来又被另一个倒着跑的衙役撞翻在地。丁哨官气得七窍生烟,怒道:“卵蛋都给婆娘吃了不成?跟着老子上!”
这丁哨官,虽然只是个小小的哨官,吃着几石的粮饷,但也是跟着上过沙场的。在这般情形下,他知道逃跑也只会让更多人死在敌人的刀下。眼前这个要命的阎罗鬼差只有一起上才有赶跑它的可能。
众人见丁哨官自己也上了,又折回来举着兵器去戳那黑熊。
混乱中,肖展插着手,冷笑的看着这帮人忙前忙后。而在驿站屋后的山崖上,一棵怀抱的大树后面,有个身着黑袍,头戴叶子杂草编成的斗笠的人远远的看着这驿站里的打闹。
这黑袍子汉子用手抄了抄草帽,这才看到一张满是横肉的脸。而不远处的肖展则是冲着这个黑袍子方向笑了笑。好像早已与这黑袍子有了默契一般。
这正是:大公子不畏死原来成竹在胸,小哨官发蛮力搏命拦路鬼差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