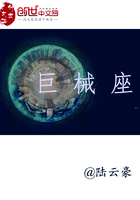子箐掂了掂手里的那包银钱,撇撇嘴叹了口气,走到角落里,寻了个僻处把身上的银钱通通拿出来。
瞅着琢磨了一会,她把那一两银子装到钱袋子里,再用手帕把剩下的那半两银子还有二十来个铜板包起来。
寻思着差不多了,子箐把钱袋子收入怀中,抓着那包银钱便过去了。
老汉将吃食放到一旁,直瞅着身旁的儿子,嘴唇翕动了两下,终是啥也没说出来。
“老伯?”乞丐老汉抬起头来,见到跟前站着个大姑娘,不免有些困惑。
子箐笑了笑,蹲下身来,“老伯,方才听那俩个大娘说了,您老是个识文断墨的,我想请你与我写封家书。”
老汉半睁着双眼打量了子箐一番,迟疑了一会,终是起身,和蔼道,“姑娘,稍等片刻,容老朽讨寻纸墨。”
“有劳老伯了。”子箐应了一声,退开一步让老汉离开。
于此等候之时,子箐顺便看了看那个至始至终没怎么动弹过的男子。
只见他二十上下,双眼缠着脏乱的白布,想来是有眼疾。
鼻梁高而挺,双唇紧抿下颚尖细,若将满脸尘垢洗去,应是个美男子了。
子箐于旁看着,若说她早先对这男子还有异议的话,这会儿得已一见便是没有了。
读书之人皆是自命清高,这样的人沦落至此,难免一蹶不振,她再有啥好抱怨的。
“喏,你就搁这儿写吧,”一个客栈的伙计帮老汉搬了把椅子出来,放到子箐脚边便回去了。
乞丐老汉拿着纸砚道了谢,铺在椅面上,看着子箐,握着毛头笔沾染水墨,“姑娘是要与何人书信?”
方才老汉去借笔墨的时候子箐就想好了,顺口胡诌,只道是给自个儿男人写信,絮絮叨叨的说些有的没的。
言过半篇,老汉提笔一勾,写下最后一个字,上下看了一通,问子箐还有没有要说的。
“没了,谢谢老伯,”子箐笑了下,接过纸张,“呦,老伯,您老这字儿写的不错啊,一横就是一横。”
老汉听了,低低笑了两声,“姑娘见笑了,老朽不过涂鸦之作。”
子箐把纸张摊开,好使墨迹快干,随意一句。
“哪的话,老伯写的我好歹能瞅出三四个,有些写的那字儿,就跟面条掉这纸上似的,一坨一坨……”
“姑娘,认得字?”老汉有些意外,瞧这姑娘打扮,实为村姑一个,怎会识得字。
子箐一愣,要说这字儿,识也识得几个,满大街的招牌匾额都是些繁文的,她仔细瞅还是能叫出来四五个的。
不过这会儿她就是个村姑,肚子都填不饱了,哪有闲钱上私塾认字儿啊。
她眼珠子一转,笑道,“哎,认得认得,十根手指数的过来的数儿我都认得。”
老汉听着,便又是笑了,“不识好啊,女子无才便是德。”
子箐扯扯嘴角,全当没听见,她把书信收起来,心思一转,便与老汉闲唠起来。
“呀,老伯你瞧,我搁这儿倒把你给搅合了,你这还没吃午晌饭吧!”
“不碍事,不碍事……”
“这咋能不碍事儿哩,我爹说了,天大的事儿都没这个打紧,只有吃饱肚子才是真的,多大的坎过不去啊。”
老汉忽的一顿,瞅瞅子箐,见她只是笑着,那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真诚极了。
他回过头瞅瞅自个儿的儿子,“姑娘这话,倒是在理。”
“啥在不在理的,我这叫话糙理不糙,连河里的鲤鱼儿都知道逆流直上,才能过龙门哩,咱填饱了肚子心里有劲儿,想干啥干不成,是吧老伯?”
子箐笑着说完,便把手里的帕子塞给老汉,“老伯,前过张秀才代笔写信要收十五个铜子儿,你且收我十个吧。”
老汉捧着这包铜板,摸着怎么着都不止十来个,他瞅着子箐正欲开口,就听到一个爽利的女声传来。
“箐妹子,箐妹子……哎哟,箐妹子,你咋跑到这儿来了,可是叫我好找啊!”
张氏从小巷口寻过来,急得满头大汗,不住的埋怨了她两句。
又见子箐站在一个老乞丐跟前,张氏顿了顿,在自个儿腰间摸了摸,结果是啥也没摸出来。
“哎,算了算了,下次给啊?”她尴尬的抿了抿嘴,对那老汉说唠了一句便拉着子箐往回走了。
老汉见二人离去,掂了掂手里的这包铜板,笑道,“这小姑娘心真善啊。”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男子口中传出,老汉回过头去,见其唇角微微轻动,确是男子说的无疑。
琢磨着男子的话,老汉又回想了一下子箐最后说的,这不正是告诉他了,可如法炮制与人代写书信谋生么。
他原先只想着这小姑娘是变着法的塞给他钱,没成想竟是这般心思灵透的一个姑娘。
“这小姑娘真是心善……”
老汉笑对着男子,忽然醒过味来,浑浊的老眼一亮,颤声道,“少、少爷……你总算说话了……”
不同于老汉的激动,男子依旧没太大反应,只是垂在地上的手动了动。
老汉喜极而泣,偷偷的抹了一把泪,将手上的那包铜板收到怀里。
他扶着墙面起身,四下里望了望,随后寻朝不远处的那个酒楼挥了挥胳膊。
高楼雅间,一家仆依窗而站,待瞧见这一幕,忙转身与屋内的主子禀报。
“公子,沐府管家他……”
红木桌旁,一男子闲心品茗,黑发白衣俊美逸清。
闻言男子微微一愣,随即启唇一笑,摆摆手,那家仆知会退下。
男子将茶碗放置桌上,把玩着一旁的玉坠,红穗滑落四指依旧妖娆,衬得男子的手越发白皙。
他饶有兴趣地望着窗外,“上来领赏吧。”
在一旁守候多时的两人一喜,忙上前来,她们便是早先给子箐“赏钱”的那个老夫人与丫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