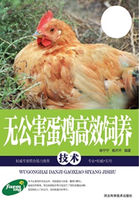开了春,有天,连忠、衍科、三姑、三姑父一起到我家,提前畦好的西瓜苗可以移栽了,帮忙种西瓜,一亩半,运苗、栽培,五个人没用一上午。
连忠和衍科、三姑父又商量着把猪圈里的肥倒腾出来。
父亲说“你们干就干吧,我去买点菜”。
说完,骑上自行车出去,好久才回来。
父亲刚回来,三姑看见脸色不对,关切地问,“四哥,你这脸怎么了”?
“没事”,父亲说话居然漏起了风,大家都过去,父亲上门牙两颗牙齿没了,嘴里还渗着血。
原来,父亲下慈母山的时候,对面来了个自行车的青年,上山比下山骑得还快,父亲躲闪不及,两个人撞到一起,父亲嘴撞到对方的前把上,歪倒沟里,当时就碰掉了一颗牙齿。
青年歪了车,却毫发无伤,吓坏了,父亲看到,摆摆手,让青年走了。
自己伸手试试,还一颗牙摇晃,父亲一气之下拔下来扔掉了。
三姑哭了,说“四哥你这是怎么了,成天这样,也没个人疼”。
一两个月后,父亲到集上,找江湖游医镶了两颗牙,牙总算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
西瓜熟了,村里来了贩子父亲卖点,赶集卖点,还赶上牛车到安丘城卖过。回家的时候捎回来了两个肉火烧,我和妹妹各一个,我和妹妹细细的一小口一小口咬,声怕很快就吃完了,第一次吃那么香的东西,看着我和妹妹那么满足的样子,父亲在一边抽着烟。
那年暑假,父亲卖完西瓜,要喂玉米的时候,车上的耠子突然倾斜,铁片硬生生地划在了小腿的腿骨上,顿时露出了骨头。
妹妹看见了,吓得哭了起来,父亲坐起来,点上颗烟,也没去看医生,忍住疼痛,浇上点白酒消了消毒,磕上点烟灰,就完事了。
然后,叹口气对我和妹妹说“边城,今年玉米得你们俩喂了”。
第二天,我和妹妹正准备到田里去喂玉米,孟凡进、老钟、刘连刚骑着自行车突然出现了,一到我家都憨笑着,见了父亲把自行车停好,叫声叔。
正纳闷呢,刘连刚说,他们家长让来帮着干点活。
平时调皮野性的他们干起活来干净利落,原来我和妹妹打算打持久战的活,一上午就接近尾声了。
要吃午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留他们,回到家父亲非要留他们去吃饭,三个人坚持去水库洗澡,帮忙拾掇完东西,骑上自行车就走掉了。
其实,他们事先并不知道父亲受伤的事。
虽然只是家长的一句话,几个同学之间一点流汗的举动,但对于一个贫困逆行的家庭,回忆起来却是多么温馨和感动啊。
父亲好长一段时间不能干重活,家里的小菜园还在,需要照顾,我力气大了,和妹妹到菜田里浇浇水。父亲用桶打水的工具是一个开放的钩子,把桶挂在钩子上,用井绳把桶放下去,桶底荡在水面上,父亲在井上左右一摇,桶倒水满,而且不脱钩。
看着父亲的样子,试了几次,水满满的,心里很是得意。
屡试不爽,但技术还是不精,最终还是脱钩了,桶掉到了大井里,水面上露个桶屁股。我和妹妹你瞅我我瞅你。
“我们自己捞吧”我说。
“这么深,井又这么宽”妹妹很担心。
“你上面拽着我,没事”我鼓动妹妹。
我把井绳绑在腰上,让妹妹在上面拽着,自己下了井,井很宽,我个子又小,好几次差点从井半空滑到井底,从井底往上看,一种压抑和恐惧,够到桶了,我从腰上解下井绳,倒提桶不进水,再正过来挂在钩子上,让妹妹把桶拔上去,自己一坎一坎爬出了井口。
后来,和我们共用一个井浇地的二爷爷知道了,非常惊奇,说我那口井建好以来,第一个敢下井的人,原来里面有蛇,而且坎已经很难踩,水深得接近两米。
我感叹自己好运,如果掉下去,如果蛇还在,掉到水里,妹妹很难拉我上来的。现在想来,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我成年后性格的起源。